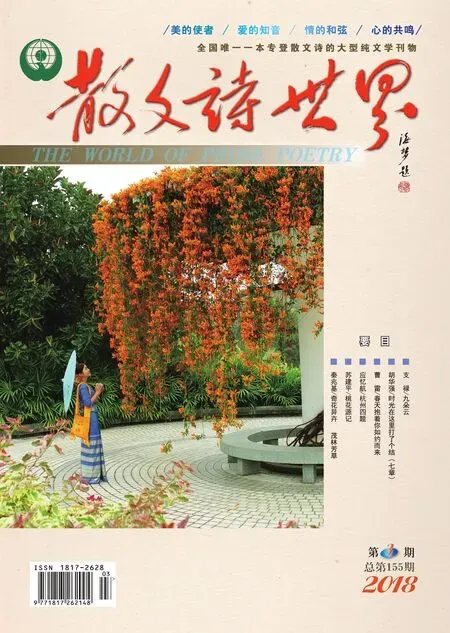一块墓碑(外一章)
2018-11-21 16:21黑龙江张雪松
散文诗世界 2018年3期
黑龙江 张雪松
我读初中的时候,学校距离我的村庄有十多里的路程。
每天上学和放学,我都要独自一人经过一片坟地。有一天,这里突然多了一座新坟,坟前立了一块高大的石碑。远远地望去,所有坟头的青草仿佛都向着这块石碑汹涌。原来,这个刚刚死去的老男人是一位乡上的干部。石碑,让他继续做了这块土地上的领袖。
那段日子,我遇到过送葬的队伍,用琐呐伴奏;也遇到过起坟的人,我看见他们掘开黑土,露出腐烂的棺材,合葬的伴侣(爱,如果没有了血肉和温度,其实就是两副骨架纠缠在一起)。
那段日子,我常听到叹息,却很少看见泪水。像镰的刃口,贫穷的日子也是锋利的,但疼痛仅到伤口为止。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一块墓碑,像骨头一样立在自己的身体里。
一只羊
分田到户那一年,我家从生产队里分到一只羊。
那时,我的年龄比它大不了几岁,在一家人当中,我就自然成了它最要好的伙伴。
我给它喂草,给它饮水,给它搭建过夜的栅栏,我给它我所能给它的一切。
它给我四只蹄子,是坚硬的,用来敲打大地;给我四条腿,是强壮的,用来支撑身体(那其实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重量);给我一声声呼唤,是温暖的,用来寻找妈妈;给我它的眼神,是深邃的,那里面装满了无尽的善良。
那段日子,我们相依为命(今天想来,这或许就是我们在尘世间苦苦找寻的“爱”吧)。
后来,我到了上小学的年龄。这只羊只好送到邻居的羊群里。再后来,我听见过邻居和家人的议论,它身上的毛是最柔软的,它身上的肉肯定也是最腥膻的。
白雪,始终在北风中深化寒冷的主题。一只羊,一直居住在的我身体里。它像另一团白雪在燃烧。
一只羊,眺望在故乡的山坡上,从来不曾熄灭。我知道,吹透它身体的北风,依旧是那么悲凉。
猜你喜欢
文苑(2018年20期)2018-11-15
今古传奇·故事版(2017年11期)2017-07-10
Coco薇(2017年3期)2017-04-25
小学阅读指南·低年级版(2016年10期)2016-09-10
剑南文学(2016年11期)2016-08-22
小朋友·聪明学堂(2015年12期)2016-01-07
小朋友·聪明学堂(2015年12期)2016-01-07
奥秘(2014年5期)2014-05-15
体育博览(2013年9期)2013-10-29
作文周刊·小学三年级版(2009年8期)2009-04-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