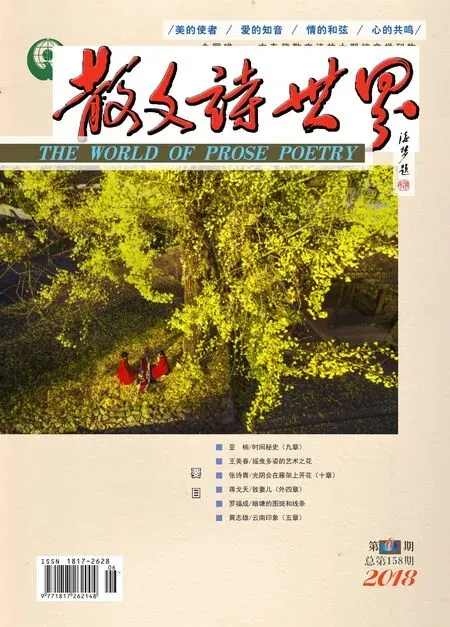新 疆 笔 记 (八章)
四川华蓥市二中 雁 歌
火焰山
一团无名的火,千年盘踞在这里。占山为王。
燃烧的火苗,是猎猎作响的旗帜。
五十度,是气候的方向。逼近或超越,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天空没有鸟影。
焦灼的沙土虽寸草不生,却能让一枚鸡蛋成熟。
这是大地上最震撼的烟火,群山搭起舞台,一粒沙在黄褐色的灰烬中打坐。
谁来欣赏这绝处逢生的热舞?谁来阻止这场旷世熊熊的大火?
掘地三尺,仍捧出一团火焰。离地三尺,每年十几毫米的降水,还没落地,就不见了。
杯水车薪。远远描述不了这火与水之间的差距,让一个古老的成语自然蒙羞。
于是,搬出名著。
牛魔大王的蛮力托起了山,竟无法熄灭山中的怒火。铁扇公主的扇子,早把一座山的名字扇到十万八千里之外。
艾丁湖在一个黄昏被灼干最后一滴泪水,眼眶结满盐霜。
火势还在继续。它要燃尽天空最后一层阴霾,燃尽尘世最后一道屏障,燃尽人们最后一丝欲念。
我看见,一缕火苗正在沿着三千年胡杨的虬根,去舔舐葡萄谷低垂的——那枚晶莹的灵魂。
然后,在大漠秋风中涅槃,开成天山的一朵雪莲。
天山天池
一枚硕大的纽扣,斜挂在西域的腰间。
沙漠,盆地,山脉。切割广袤的版图。
天山,版图上长长的分界线。巨人一样顶天立地,一脚踏在北疆,一脚踏在南疆。浑身如戟,排成一道道栅栏或箭阵,似乎要弹射出千万年前的秘密。
你头枕博格达峰,远看像一幅笔架。
一支笔直指丝路长河卷起的漫天风沙。绘出荒原的落日和孤烟,苍凉的部分放在一粒沙后。
一支笔纵情山水,道法自然。常饱蘸流泉飞瀑,勾勒出一朵干净的白云,或倒影中铁瓦寺隐匿的虔诚。
干涸的唇壤,皲裂的眼神,最终被一线冰雪击中。月牙似的天池紧紧被扣在你腰身一千九百多米的部位。
定海神针,直插湖边,如一根山林的旗杆。摇晃的枝叶,搅翻湖底的传说。
西王母的梳妆台,为何碎落水盆之中?
你以水为镜,为何总是白头?
天空一朵蓝,峰顶一朵白,水中一朵蓝,朵朵都直逼世俗的眼。
塔松,云杉,一律向上,峭立巉岩绝壁之间。青绿的心事,一半交给山风,一半交给湖水。
据说,这是圣山或灵水。
清幽之水,因神谕而通达人性。时而鱼在天上游,时而鸟在水中飞。而那雪白逶迤的群峰,勾勒出一座山思想的底线。
太高,或太蓝。这美,实在叫人迷离,晕眩。
有时,真想把这张版图挪动一下,抖出些砂砾,挤掉些色彩。
然后,把天池放在平地,把雪莲种进菜园。
坎儿井
吐鲁番是一个盆。
博格达峰的雪水流下来。
暗渠隐藏在盆中。空旷的盆面,竖井、明渠、涝坝,如三朵盛开的花,点缀着盆地砂砾和粘土交织的面庞。
一条井渠,早在两千年前,就打通了水与沙的经脉。
五千多公里的历程,并不短。每一步都撑起滴落在西域的月光或风情。比如楼兰姑娘远去的歌舞,比如交河故城湮没的繁华,比如沙漠之上升起的绿洲。
一颗葡萄,是老农的眼睛,映亮雪山。
一个哈密瓜,是雪峰到吐鲁番浓缩的距离。
这片宏阔的场景,跟昔日的大运河相似。
地下的部分,常让人想起万里长城。
长城,本是与烽烟有关。
而坎儿井,总是潜伏在被人遗忘的角落,沿着一条条青绿的藤蔓,窥探沙漠的心事。
每一滴渗出的清泉,都是守望沙漠千年的眼神。
艾丁湖
艾丁湖坐拥盆地,我们在辽阔的疆域坐南朝北。
五万平方公里的水域,在砂砾上铺开一枚荷叶。绿荫下,清脆的日子,花果飘香。
如今,可惜这片叶子已经枯萎。
寻水的野骆驼不见了,疾驰的鸟影不见了。一条鱼的标本,早已把一湖水饮尽。
南北侧烽燧的遗址还在,这海拔最低的烽燧,曾托起高昌国最硕大的一朵白云。
站在这里,似乎还可以想象:一段历史的嘶鸣,或一汪湖水的平静。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地势越低,就一定会有水来朝拜。
在时光通道里,是谁,在颠覆和破坏水往低处流的法则?
蹲在低处,是一种生活的常态。并不妨碍目光,翻过博格达峰的雪岭。
艾丁湖,吐鲁番腹地风化掉的一枚胎记。
唯有月光,静静流淌在一片斑驳的盐碱地里。
艾丁湖,拥有中国陆地最低位置的名称,却高居在显赫的版图上。
只是,在一粒沙的世界里,没有守住半塘的湖水,和月光。
高昌古城
夯土,土坯,风沙,阳光。
两千年的堆积,撑起一座孤城的轮廓与高度。
据说,这里地势高敞,人庶昌盛。但作为一方城池,得源于汉武帝的一次震怒。
木头沟之水,蜿蜒而过。汉武帝的余怒,还挂在葡萄架上。
风沙与阳光反复角逐。
岁月把西域的沧桑反复磨砺,雕琢成每一堵城墙的面庞。比如烽火台,佛塔,宫殿,可汗堡,藏经楼。
刻刀过处,砂砾漫卷。
那些剥蚀的土坯,一片一片地飘落。如黄昏的秋叶,肃穆而静美。
叶子慢慢堆叠成一部黄页。上面依次写满高昌壁,高昌郡,高昌王国,唐代西洲,回鹘高昌,火州。
一千三百多个页码,太厚。加上天气太热,我只能随手翻了几篇。顺便记住了一座城池的变迁。
至于古城昔日的繁华升平,王室贵族,商贾僧侣,风月情场,我们都无从考证。也许,他们应该停留在书页的某一角落,或藏匿在一粒沙中。
大漠戈壁,纵横捭阖。
万里长空,一只鹰扇动的背影已经远去。包括烽火余晖下的那缕孤烟,旷野鏖战最后一匹马仰天的嘶鸣,回鹘女子最后的一滴眼泪。
只留下破败与恢弘。我们穿梭在断壁残垣和城堡街巷之间,一边找寻童年的迷宫,那枚从天山脚下曾经丢失的葡萄。一边与一个王国对话,不需要翻译,风是最好的信使,沙是最好的驿道。
一幢幢墙影掠过,一道道城门敞开。偶尔传来长安城那遥远的呼唤。
阳光下,一粒粒沙子正交出真相,眨着眼睛,向人们致敬。
柏孜克拉克千佛洞
火焰山峡谷。木头沟河西岸。
一千五百年前。黄褐色的绝壁断崖上,传来铿锵的凿石之声。
此起彼伏的是,大漠边关抖落的驼铃与羌笛。
更多的时候,看见一群西出阳关的汉唐使节和商贾旅人。而一路东向长安的鸠摩罗什们,行色匆匆的背影,长长地斜拉在丝路长河的两端。
他们将瓷器与哈密瓜,信仰与文化,铺满阳关大道。然后,牵手长安与高昌,合掌为十。
断崖之上,是亘古绵延的黄土,是八十余座栩栩如生姿态万千的佛窟。即使那些残损的佛像,也掩盖不了圆润有力的线条。
每一根线条,源于脆弱的神经,直抵众生,连接悲悯。
线条与色彩交织出远古的梵音,从胜金口缓缓流出。
中原斗拱与西域土建水乳交融。如一朵朵菩提之花,盛开在高昌古国的绝壁之上。
皇家瑞气与西天佛性点石成金。让一座山开口说话,让闪烁的光芒点亮漆黑的灯盏,和苍茫而昏黄的眼神。
我靠在洞窟边,试图捕捉那些散佚的禅音,以破译高昌石窟群的玄秘。
不见飞鸟走兽,只有游人匆匆的步履。他们一边找寻心灵密码的对应洞窟,一边与一坯黄土对话。
一阵风沙漫过,湮没了所有脚印。
断崖还在。黄土还在。佛窟还在。
那拉提草原
一滴水,从天山流下来,打通一粒沙与一棵树的经脉。
细碎的阳光,如一支神奇的画笔,在巨幅的碧毡上滚动。掀起一浪一浪的色彩和一群一群的牛羊。
玉带缠腰。巩乃斯河从这里蜿蜒而过,荡漾的草海广袤无垠。
从苍凉的戈壁,我踏进绿色的海洋。那辽阔的海岸线,挺立着高昂的白桦和松杉。
一种深不可测的色流,让我顿生窒息,视力退却,几乎不敢与一片草叶对坐。生怕被卷进羊堆马群,卷进洁白的毡房,卷进哈萨克姑娘那澄澈晶莹的波。
我宁愿远离千年雪山万里湛蓝,远离伊犁河谷丰茂的水草,远离最后一抹马蹄或长风,融进草原的夜色。让那无边的黑与九百六十平方公里的宁静,按捺我躁动不已的心灵和惊悸惶恐的眼神。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只蝴蝶的梦中,去想象一只鹰腾空的高度,去揣摩那拉提草原五颜六色的花朵,与成吉思汗西征队伍的命运是怎样的关系。
最好骑上一匹快马,纵横在绿波涡旋的深处。
或者,化作草海含苞的嫩芽,让一只温顺的羊啃食,咀嚼。
喀纳斯湖
第四季冰川太远,一枚遗留的冰块,如一弯月牙,睡卧在阿尔泰山的怀抱。
这是神的最后一滴眼泪,是北冰洋逆流而上的一道蓝。
喀纳斯湖,一半把水还给天空,一半把白云扯满湖底。纯净蔚蓝的湖水,宛如盛满岁月的童话。
揭开这部蓝色的故事,雪岭云杉状如篱笆,分列布阵,编织时光的脉络。那峻峭的细节,如一枚书笺,直捣湖心。
雾霭沉沉,图瓦人驾着毛撬,从童话的开头走来,小木屋藏在白云深处,抚摸一支马头琴的回忆。
要靠近湖边,最好下一场大雪。然后和雪花一起,抖落一身的尘埃。
这样,就可以把红尘的骨肉还给冰雪,把灵魂坠入湖底。
干脆在一道蓝里,做一尾干净的游鱼。在澄澈的天空,腾起鹰的羽翼和草原狼的嗥叫。
而观鱼台,始终是奎屯和友谊峰的眼睛。
它要勾勒,一只哲罗鲑跃出湖面的曲线和浪花。
我不相信水怪,我只相信成吉思汗西征的史诗。
所有的结局,一半在湖底,一半在梦境。
赛里木湖
七千万年前。大西洋上最后一朵云,流落天山。
擦干剩下的一滴泪,一道绝世的蓝,在两千多米的腰身划开一处口子。
传说如风涌出,鼓满鹰翼。无数蓝色眼神,穿越科古尔琴山的垭口,在这里拥挤,延展,漫溢。
依次流淌出来的是“宁静”“平安”,或情侣的浪漫,而哈萨克人的“祝福”,最是记忆犹新。
独坐净海,蓝天如洗,湖水似镜。它让一切杂念无处藏身。
澄澈或空灵,云朵或牧马。牵扯着原始的亢奋,和世俗的神经。
野花的姓氏,拉开水天的缝隙,抒写草原的神性与辽阔。
自由的羊群,正咀嚼一棵草叶的清香。它要吞掉最后一抹夕阳,和最后一片雪花。然后,把自己交给一道深蓝。
一阵风吹过。云杉与白桦挥手致意,天鹅和金雕窃窃私语。
浪纹,一圈圈扩散。似乎在围堵从西域逃离的目光,以及那一缕掠过湖心的鸟影。
蓝,或深蓝。纯,或容纳。
我听不清一丝风吹草动。或许都已沉入湖底,只是不知那头湖怪是否惊醒?
湖安详着,在天山的怀抱。无边的蓝和幽邃的静,让人不寒而栗。
我赶忙交出诚意,退出缺口。
而这道蓝的尽头,一端是丝绸,一端是世界的末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