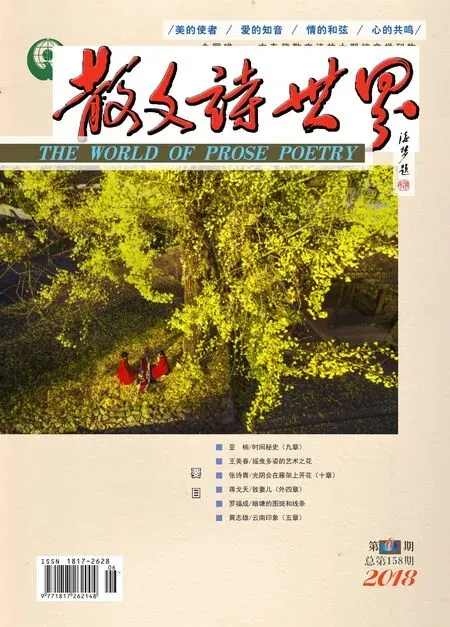光阴会在藤架上开花(十章)
山东 张诗青
张诗青,1987年6月生,山东蒙阴人,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诗刊》《星星》《诗选刊》《诗潮》《散文诗》等多种文学期刊,入选《中国散文诗2016》《2016江苏新诗年选》《2016山东诗歌年鉴》《华语诗歌双年展2015—2016》等选本。曾获徐霞客文学奖佳作奖,华语网络诗歌大赛优胜奖等多个奖项。出版诗集《绿松石》。暂居江苏扬中。
孤独是故乡绵软的柿子酒
里三层是山,外三层是山,故乡打小就是山的样子。
零碎的村落,像穹庐之上的星子般洒在大地;与世间万物,一同生长,也一同老去。
月亮选择固定的山峰升起,羊群傍晚乘着晚霞归圈,睡梦中偶尔会划过几声犬吠。
不论河谷两岸,亦或道道梯田。
春天,它是一片青翠的麦苗;夏天,它是一枚枚甘甜的蜜桃;秋天,它是万亩金黄的玉米;冬天,它则是一层纯净的白雪。
没人知道,白墙红瓦的庭院,曾珍藏过我的孤独。
那时,老屋后面的空地,尚有几株柿子树,每到秋天都会挂满丰硕的果儿,红灯笼般的小脸蛋。
家有多温暖,它就有多温暖。
母亲给羊喂草,父亲晾晒柿饼,祖父捡起地上的树枝……
如今,我与故乡相距千里,里三层外三层的山,早已不见了踪影。
饮下一杯月光般绵软的柿子酒。
三十年如一日。孤独辣辣的,故乡辣辣的。
秋风吹过禾黍之地
半山腰那片凹凸的田地,长着稀稀疏疏的禾黍。
一条许久未踏的山路,尽管多生了些杂草,但并没有使我感到陌生。
眼下,秋风吹过禾黍之地,岁月依旧。
一群斑鸠和麻雀,时常会飞下来啄食;偶然,也遇到一只觅食的老鼠,但它不是田鼠。
几年前,这里还是我魂牵梦绕的家。
那时庭院很大,除了住人的几间红瓦房,还有做饭的平房,有大门过道,有羊圈,有鸡窝,有狗窝。
唯独没有鸭窝,只因它不怕下雨。
南墙边还有两株葡萄树,等不到秋风来,等不到它变紫,往往就被我摘下来塞进了嘴里。
那种酸甜的味道,略微夹杂着几丝苦涩。
在炎热的夏天,有时院子里会堆满劈柴,那是祖父熬丹参药用的。他用泥巴石块支起一口大铁锅,里面盛着水,水里满是丹参、天麻等草药的根茎。
祖父说熬药也是一门学问。要先用大火煮沸,再用小火慢熬,待到汤药收汁后,捞出药草。再添加白红糖、蜂蜜等佐料。最后,将熬好的药汁用陶罐密封起来,以便随饮随取。
而今熬药的秘方,随着祖父的离去,也随之失传了。
长着禾黍的贫瘠之地,日渐荒凉。除了在土壤里,尚能见到零散的瓦砾和砖头。
这片土地更换了新的主人。
光阴会在藤架上开花
我相信光阴会在藤架上开花,也会在风中结出果实。
虽然,村外的老井近乎颓废,周围杂草丛生,清晨已听不到一丝喧闹。
但这又有何妨呢?
每天,它依然对着那太阳,那月亮,那大地深处,泉涌不息。
只是聆听的耳朵,离得太过遥远。
这些年,村里的牛少了,羊少了,猪少了,年轻人少了。
相反,荒地多了,老房子多了,空房子多了,老人多了但又急速少了。
不多不少的,是门前的十万大山,青松翠柏,细水长流。
有时,人难免会背井离乡,但植物不会背叛自己。
躯体生于斯死于斯,灵魂生于斯死于斯;斯地是漂泊者永恒的心痛。
我明白,在雪中刨食,坚守冬天的,是麻雀和斑鸠。
而果实是最后的孤独。
村庄的最低处和最远处
1
自出生之日起,十万大山便已备下。
小时候,它像院落的石头墙,围成的襁褓,呵护着一颗幼小的心灵。
阳光。雨露。
每一种恩赐,都会让大地长出更多的庄稼和粮食。
去养活,大山深处的子民,山坡上啃草的羊群,暮晚归巢的飞鸟。
2
长大后。
它又像一道横亘眼前的天堑。供我攀爬,翻越。
昼夜生长的粮食,吞噬了风和往事。
二十岁那年,我把它背在肩上,小心地包裹好。
那是母亲吃了一辈子的煎饼。
我仅需一张,薄薄的,笨重的翅膀。
3
现实中,或许只有河流才相信命运。
它的一生,都在沿着既定的河谷,穿过那个村庄的最低处和最远处。
对于岁月沉淀的部分,它照收不误。
这种简单,务实。
让我的浮躁,日益相形见绌。
4
十年了。
原本就瘦弱的村庄变得更远了。更小了。
小成一枚星子,被钉在窗外那张漫无边际的黑地图上。
想念的时候,若有微光不经意晃动一下。
我便盯着那个地方,
等那人从庄稼地里回来,等雪白的羊群,从山上下来。
我想让时间在蜗牛贝壳里停留
清晨,慢慢推开闭合的窗页,就像扇贝缓缓张开润滑的嘴唇,带着海风新鲜的气息。
爬山虎伸出翡翠的小手,每一阵微风过后,停留眼眸中的绿波都会涌动许久。
小雨如期而至,滴在江南三月的眉头,滴在这青砖灰瓦之间,滴在骑马而过的游子发梢。
一滴雨它收起翅膀,在风中做出滑翔姿势,稳稳地落在眼前的瓦上。
我坐在窗前,看它从一层瓦转身跳到另一层瓦上,从高处流回低处,最后轮回大地。
流经的瓦片明亮了,有几处蜗牛苏醒了,露出浅浅的触角,萌萌地打量着四周。
我惊喜墙壁上满满的希望,越长越稠密的思绪,犹如你居住江中的绿岛。
长江从何时流到何时未知,黄河何时能奔流复还也未知。
此刻,我想让这弥漫哀愁的雨多下一会儿,我想让时间在蜗牛贝壳里停留。
在闪电深处
乌鸦站在高压线上。
一片背负着黑夜的雪花,尽管轻柔得让人毫无察觉,但终归还是飘落下来。紧接着第二片、第三片……
越来越多的黑夜,堆积在黄昏的构树上。然后,沿着枝丫流回大地。
一切归于沉寂。
酒还是要喝,愁还是要解。
这密不透风的宇宙,如何孕育了众多眼泪?在你需要的时候,它总是第一时间涌现。冲刷掉你的悲伤、绝望、哀戚。
岁月像莲花般,在心间一年又一年收割。
直至,那些好看的影子,全被挡在了疲倦的窗外。
祈祷。仰望。我期待的遭遇。
在闪电深处,一块炸裂的石头腹中,有朵白玫瑰开了花。
沙家港的秋天
八月的沙家港,泊着几艘大船,和一湾白头的芦苇。
夕阳下,几只白鹭翩然飞舞。血色的光泽,点燃了它们轻柔的、洁白的羽毛,也浸透着岸边废弃的塔吊,虽然它早已锈迹斑斑。
芦苇的叶子还很鲜绿,和江水一样鲜绿。
我想定是江水偷取了它们的颜色,就像月亮偷取了太阳的一片赤诚,就像我们彼此爱慕的韶华流年。
悲观者:白色的花穗是苍凉生命的尽头。
乐观者:白色的花穗是一生无悔的总结。
然而,对于我来说,它只是纯洁的花穗,好看的花穗,会结籽粒的花穗,也会脱落的花穗。
我没有看到它的悲伤,却看到了自己落寞的背影;我没有听到它的哭泣,却听到了自己痛彻的心扉。
八月的沙家港,白云悠闲地涂抹着蔚蓝的苍穹。江边那个害怕孤独的人,则用石子用力击打着沉寂的水面。
秋天没有回答的,远处的汽笛已回答。
西津渡口
那一年华灯初上,月光漫过云台阁。
我们牵着彼此的手,沿着青石板的小码头街,拾级而上,蜿蜒而沧桑的路,远远看不见尽头。
偶尔,脚步也会突然慢下来。
这并非感染了春风的思绪,也并非被撩人的夜香蛊惑。
比如,眼前这座喇嘛式的石塔,几百年独坐渡口,不经意间在耳畔,就会奏起古朴的歌谣。
任光阴荏苒,岁月蹉跎。
旁边待渡亭里还坐着待渡的人。
只不过悲伤的事,总是轻易涌上心头,渡口再也不会有船儿到来了。
一层一层的台阶长满了青苔,她读过唐风宋雨的诗词,她打马走过金戈铁马的元明,她身着艳丽的大清旗袍缓缓走来。
从香山书院到小菩提酒吧,从戴春林到绿竹翁,从吴勾酒坊到江南镇江锅盖面。
此刻,我们笑而不语,让风一路疾走。
种白菜
立秋后,蝉鸣凄婉,秋风始凉。
此时,母亲在菜园里,将搀扶豆荚短暂一生的枝条清除。
平整后的土壤,新鲜、松软。
一粒粒球状的白菜籽,像一枚枚受精卵,开始在秋日的大地着床。
子宫的阳光雨露正好,这些旺盛的小生命,慢慢抖落身上的泥土,多么洁净的婴儿。
它不像人类那样,一出生就学会了哭喊;相反,它先天就已懂得了克制自己。
不论贫瘠、饥渴、虫害、雨雪……
这些课程,在生命基因中早已罗列。
只要有阳光,只要有露水,只要有土壤,此生足矣。
入冬了,就抱紧自己。
在拉尕山寨
在拉尕山寨,古老来得恬静。
淳朴而勤劳的藏家儿女,从祖辈的手中接过世代的耕作工具。接过麦子、蚕豆、马铃薯的种子,接过脚下丰腴的土地,也接过那亘古不变的信仰。
也包括语言和风。
山寨远处耸立的白塔,端庄但纤尘不染,它有着雪的圣洁和慈悲。
而五彩的经幡,在蔚蓝的天空里肆意翻卷,如鱼跃浪花,又如格萨尔王战马脖子上吹拂的鬃毛。
只待勇士们一声的召唤。
我相信万物轮回,周而复始。王的十三战神与天马还会归来,而美丽的姑娘们还会为王献茶。
弹落尘埃,脚踩草露,我在暮色中等你。
等你的十万灵魂,等你肉体里流淌着的亿万座雪山,抵过尘世的喧嚣与哀伤。
每往山上走一步,距自己的内心就近一步。
在香巴寺,我愿焚香叩拜,我愿敬献哈达,我愿交出所有的虔诚。
用一颗淳朴感恩的心,贴近神迹,哪怕泪流满面。
拉尕山,它予我一朵禅意,心念便花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