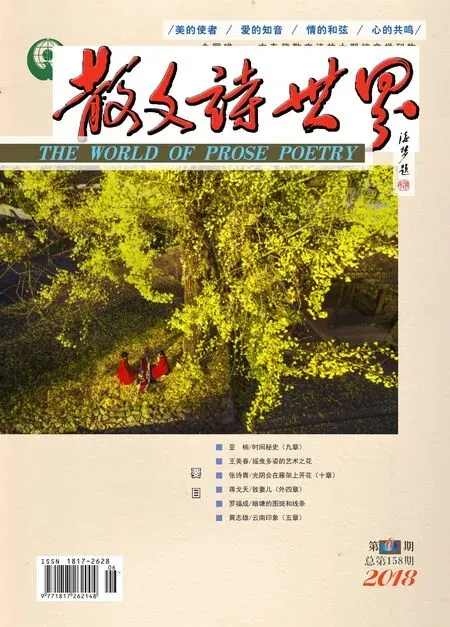老眼看世界(七章)
蔡 旭
上车打卡
公交车会说不同的声音。
小孩子上车时,它说:学生卡。
成年人上车时,“嘀”的一声,它只顾收费。
我上车时,它并没有宣布我的身份。
即使我是外地人,也享受同等待遇。
它说:“您好!”
似乎对老人特别有礼貌。
不直接说出老年卡,让我有点高兴。
它不认为我老。
我也明知故犯地,忽略了——
我的年龄。
路遇陌生人
一个比我还老的老人迎面走来,一招手,改变了我们擦肩而过的轨迹。
让我在街边的绿荫下,停下了匆匆的脚步。
“我好像见过你。今天又见到了。”他说。
好像?我没有印象。当然也不会说出来。
“见到你很高兴。”我点了点头,回报了一朵微笑。
于是就在花圃旁伫立。交换了年龄,讨论了今天的天气。
他并没有向我推销产品,也没有拉我去听什么重要讲座。
没有对我有任何要求。
也许他认错了人,也许,只想有一个陪他说几句话的人。
我有幸被他看中,接受了他的问候。
幸好忘却了我的戒心,递上了我的回赠。
并不是陌生人都需要警惕的。我想。
这时天晴气朗,有清风与花香作伴,我的步子也轻快了起来。
皇宫的生意
珠海有个圆明新园,仿造的。
园里有宫殿,仿造的。
殿里有宝座,仿造的。
座上放着皇帝的龙袍,也是仿造的。
当然皇帝也可以仿造。
这龙袍谁都可以穿,这宝座谁都可以坐。
只花十块钱,就可以拍一张皇上照,做一下皇帝梦。
还可以让皇后陪着,再加十块钱。
似乎生意很清淡。
想当皇帝的人,太少。
许多人同我一样,路过时暂停十秒。
看一看,笑一笑。
路过年轻的老店
一间茶楼,在它的额头上刻着“1990”的字样。
在时空中,刻上它开始飘香的岁月。
哦,又不是百年老店,有什么可炫耀的?
——年已古稀的我,忍不住对这间年纪轻轻的茶馆怼上一句。
身边有人却说:做了28年,它已经不容易了。
一句话把我点醒,不禁放眼张望它相邻的一排店铺。
哦,这些年,那些隔壁邻舍,不知已刷新多少回了。
店面在反复装修,行当在花样翻新,老板在商海浮沉。
“城头变幻大王旗”,谁数过日新月异的招牌,换了几多块?
我忽然觉得不认识身边这个人。
不明白他怎么能看到这间年轻的茶楼远大的志向。
看到从28年到百年老店的胆量与决心。
也许,多少年来,我只是在岸边观潮的人吧。
而身边这个人,是在波峰浪谷中艰难穿行了十多年的——
我的儿子。
在儿童医院
一个写散文诗的退休老头,我到这里并不是为了体验生活。
而是生活,让我不得不到这来体验。
才知道儿童医院里多的不是儿童,而是两三倍的大人。
一倍的父亲或母亲,一倍的爷爷或奶奶,甚至这些人同时都在。
哦,还有不计在内的医生与护士。
半岁的孙女要体检,就由我与她的奶奶带着。
没有两个大人是应付不了的。
挂号、就诊、缴费、打针、化验、拿药,要分头去排不同的队。
更多的时间,都在等待,每一项消费的除了金钱,还有时间。
等待中相同的节目,是家长的交流。
宝宝的性别、年龄、身高、体重,以及育儿的经验与教训……
我家孙女的表现,好得难以令人相信。
四个小时的折腾,竟然没有吵闹。
似乎很懂事,也许是还不懂事。
打针时只有十秒的哭声,瞬间又破涕为笑。
似乎是不怕痛,也许是还不懂得痛。
她并不觉得疲累,只是爷爷奶奶累。
——当然,她也不知道。
在楼群腰间穿过的火车
铁道在城市的天空穿过,在高楼大厦的腰间穿过,在我的头顶穿过。
站在街上的我,看不到铁轨。它当然在,铺在常识里。
火车闪过天空的时候,我往往也没能看到。动字头的列车,子弹头样子的火车头,飞得像子弹一样快。
只有我的上幼儿园小班的孙子,他的眼特别尖,才能看到。
列车一闪而过的时候,几乎没有声音。也不响汽笛,也就没有“呜呜”的呼吸。
“以前的火车轰隆轰隆,声音很响。”孙子说。这是他听我说过的,他并没有听到过。
世界变得很快。从轰隆隆到静悄悄,响声越变越小,越来越不动声色。
光阴也像穿过楼腰的火车,闪得飞快,一眨眼就不见了。
一切都在快,只有我在变慢。步子也慢,眼光也慢,总是跟不上。
列车在楼群的腰间穿过,总在它一闪之后,听到孙子说了,我才知道。
慢慢走过这条小街
城市跑得太快了,人们又想它有时能慢下来。
一条新的小街在老城中诞生了。
高耸间插入低平,繁华中夹进清淡,喧嚷中隔出僻静。
树荫布置了凉爽,青砖铺出了情调,集装箱打扮了生机。
我从小街走过时,花香、果香、茶香与咖啡香就扑面飘来。
更有书香,散发着高雅的格调。
原以为这小街太知道老年人的心意了,其实它更受到年轻人的青睐。
音乐与诗在街上穿行时,点缀其间的总是窃窃私语与甜言蜜语。
这条小街实在太小了,地图上还找不到它的名字。
不过它早就有名有姓了。
只因街边站着一排开花的相思树,而做到了名副其实。
当然是年轻人起的。
不过老人如我,也喜欢它的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