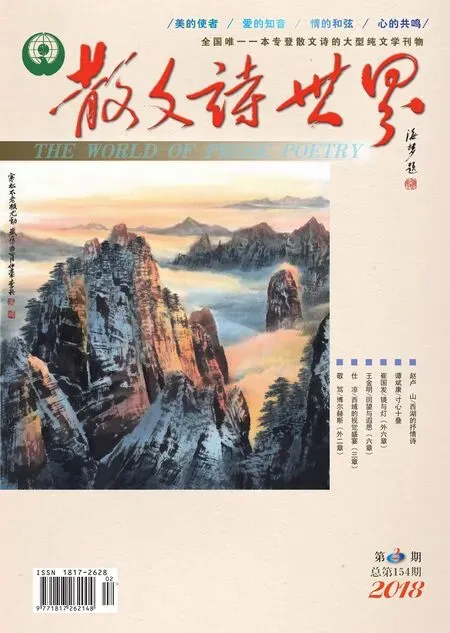羊群,隐没在白云深处(五章)
内蒙古 包玉平
巢 穴
我就是一个巢穴。
一些枯枝败叶,从头顶
一直在,加筑
——这一秋天。
一些虫蚁、蟋蟀、蝼蛄,为躲避秋凉,从渐渐发硬的耳孔
进入,用黑暗里的荒凉,占领头颅。
一行蚂蚁,与黑暗里尖锐的蟋蟀合谋,正在聚集,一口一口咬碎肉身,骨头,搬运——
这粉身碎骨的感觉,让我也初次品味了生命的异样味道。
——我,欲想即刻破壳而出,重试生命轨迹……
此刻,一些虫蚁,在意识的躯干,已搭建许多巢穴,并将秋夜的寒凉
拖入,塞满体内——甲虫,将一生打包,前来;到处都是虫子,在爬动,尖叫,
隐藏,低鸣:
全身,渐渐在失血,发暗,发凉——
仅此,在这毁灭感的缝隙里,我看见了我模糊的前世,
和微妙的余生。
蒙古马
科尔沁草原上的马嘶,撕破了帝国疆域百年沉寂。
飞鸟难于逾越的雪山,被不安的马蹄踏平。欲望的箭矢,转眼间,射中了欧亚版图的靶心。
如今,草原上,西拉木伦河,依然,悠悠流淌着一个英雄民族的豪气与梦想。
草原人,从昔日的马背上,翻身落马:让一匹马,顺着马头琴两根多梦的琴弦,踏着呼麦的沧桑,带着篝火上的火苗,走出,它亘古的梦——
让另一匹马,
回到,孝庄园的马厩里,回到富饶、安逸的科尔沁草原。
不要惊扰那马鞍上,绽放的萨日朗,更不要惊动,马镫上寂静的斑驳;要不——让所有的寂静,回到铁锈里:绊住不安的马蹄,让它静静地,静静地在乌力吉木仁河畔,弹奏一只草原鹰的蓝色梦;让草原的寂静,锁住弓箭、长矛、贪欲、杀机……
冰河上,乌鸦嘶哑鸣叫……
这时,一只乌鸦,在冰河上空,斜飞而来,
一块锈铁,在我心中
滚动,此刻,为何天空随之抖动,倾斜,翻转,
却,突然间保持静止,发蓝,发暗?
在远处,更多的乌鸦,从苍穹的
漏洞中,磨亮身体的墨蓝之光,抽出羽翼,斜身,翩然四处散落,在冰面上,如火焰,跳跃,伸出火舌,争抢食物,此刻,为何
冰面上,蓦然,更加寒冷,悲凄?
陡然,有一只乌鸦,在寒风中,猛然回头,歪脖,一声凄厉的嘶哑鸣叫,天下
为何顿时
黑的更黑,白的更白,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更加空寂,辽远,苍茫?
——乌鸦飞去,乌云,即刻假装合拢翅膀,俯冲,滚动,试图穿越我身体,此刻,天空,为何
陡然撤退,挪动,钟表疼痛,瞬间,停止摆动,荒废?
梦中的羊群
在水与冰之间,我
早已擦觉出
一把刀子的光芒,在暗夜里,依旧没能隐去,暗自发光的,刀锋。
在刀子和水之间,我也没能听见,哪一只羊的尖叫,羊群,却已悄然,隐没在
白云深处。
河流堪比妖孽,用水的魔布,遮掩浪尖上,明亮,滚动而来的尸骨,致使飞鱼的游动,止于
梦幻的——刹那间。
在流水中,在薄冰的洁净里,在生命繁盛的
间隙,我却
更没能察觉到火焰的,汹涌。
当河流,从冰冷的刀刃上,醒来,
堤岸上,聚集着送别的人群,像树木,大雁,依然在向着乡愁的
逃亡途中。
春来,河流大病如初,
眨眼间,花朵
转身,已
离开春草,蝴蝶飞去,蜜蜂潮湿,我们无奈:只能再一次去一枚果核里,寻找
羊群的——踪迹。
暗夜里,一只蟋蟀的生存之道
我敢肯定:这八月的夜晚,孤单得要哭出声来,如果没有那只黑暗中的
蟋蟀,蟋蟀悠长的鸣叫。
我敢肯定:一只蟋蟀,整夜磨亮的刀具,不是想杀人,就是想自杀。
——阴谋家的生存方式,你走近它,它就隐藏自己的体内,销声匿迹,
你离开它,它立刻伸出小手,磨刀——
你看它,浑身长满毒箭,将世界斩尽杀绝为快,尖利的牙齿,咬碎了多少暗藏
墙角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