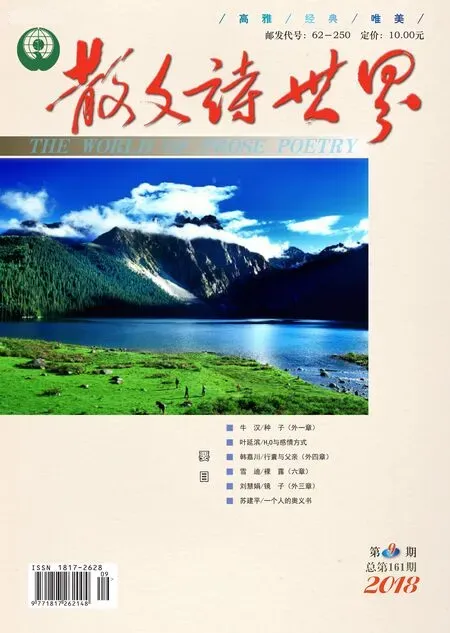山中老宅
福建 陈三河
童年全部的时光都在山中消度。
那座静卧在山中的大厝,收纳着年幼时繁盛而轻浅的快乐。
回望时,那些宛如新草上的露珠那般纯净明亮的快乐,在人为界定的童年世界里空气般蔓延。
构筑老宅的材料都是最简单的土石木。就地取材的石头做地基,用泥土筑起挡风的墙,来自深山的古木笔直而刨光,散发出木质材料淡淡的幽香,置放在屋顶和隔层。屋顶上如鱼鳞般排列泥土烧制的瓦片,遮住了四季不约而至的冷风寒雨。常有不知名字的山鸟或者长途跋涉而来的燕子停歇在那里,梳理光滑的羽毛或调情歌唱,声音流露出干净的金属味。
老宅分隔成三层。最上层较低矮,铺着长方形木梆,经常放些杂物;中层也紧密地平铺着木梆,一般做卧室;底层做客厅和厨房。连接底层和中层是木质楼梯,走在上面总会发出嘣嘣嘣的有节奏的声响。
年幼时,家里成群的孩子特别喜欢在楼梯上跑上跑下,追逐嬉戏。学会写字时,直接用木炭或秃头的毛笔沾满墨水,在墙上歪歪扭扭地涂写着“上下楼梯要小心”之类的警示性文字,大人们从不干涉,可搞笑的是,经常在那里摔得鼻青脸肿却野性不泯,伤疤未好,就忘了痛,越跌越跑。也因此,常有单纯的快乐填满稚嫩的心室。
老宅中间是个硕大无棚的长方形天窗,仰之流云缓慢迁徙;雨天,雨滴无遮飘落;星夜,幽凉星光轻洒。
这给我们幼小的心灵提供足不出户便可以和自然对话的便利。年少时,别无选择,处在其中不懂寓意;年长忆念时,感觉就像一溪朴素幽静的古诗之水,缓缓漫溢过斑驳的心灵,竟也滋生几分不与别人分享的安然。
天窗底下,对应一个长方形池子,平时不蓄水,不养鱼,种几盆空谷幽兰在池边,山野清新脱俗之气,立刻在屋中流荡。
客厅正中央竖起一面屏风,屏风中间有幅彩色的漆画,画中画着仙风道骨的老人、慈祥的妇人抱着幼童。画的两边是一副金粉书就的对联:“礼乐诗书千古业,谦恭孝友百年基”。意在告诉家人,文化的力量和讲究为人的重要性。每每在内心念及,便不敢无视读书,傲慢为人喽。
客厅正对着大门。这是一副厚重的大门,门联上写着:“治家用勤俭两字,接物须和平一生”。把持家待物的理念精髓书写在那,让我们丝毫不敢有奢靡浮华之风,把持和平善念,与万物为友,坦然处世。
这幅厚重的大门虽然挡住了外界的喧嚣,却挡不住我们探视门外山外好奇的目光。在它无数次的开启和关闭中,多少家事在其间生灭,但是,许多梦想却在对门外山外的猜想中诞生。走出家门看世界的欲望,在我年幼的心中一遍遍模糊地升腾。
后来,我们都长大了,姐姐们都嫁人了,兄弟们走上各自的岗位。母亲也接到县城住下了。
我骆驼一般忍辱负重的老父亲也永远离开我们了,离开了老宅。他以土葬的形式,在大门对面的笔架山上入土为安。勤勉一生的他,终于获得了长长的假期。他终于可以与另一世界先他而去的族人永恒地促膝长谈了,谅他不至于孤单了吧。
父亲守在那个艰难而温馨的安静山谷。老宅却渐渐地被我们弃置在山中,只等每年清明回家扫墓才光顾一回。屋中遍布的霉味和荒凉景象,让我们止不住地叹惋。
土瓦房、石头门埕、土楼,这些闽南山区常见的素颜建筑;环绕村庄的蜜柚树、山坡上的竹林、清澈的溪流、长满野树起伏不定的山棱;已逝的亲人、年幼时繁盛轻浅的快乐。
这所有的所有已经深深密植于灵魂里了。
他们,从未消失,只要触及,便在我的记忆里一点点复原。
他们,构成我精神的航船,支撑我不卑不亢穿行于波涛汹涌的江湖而不自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