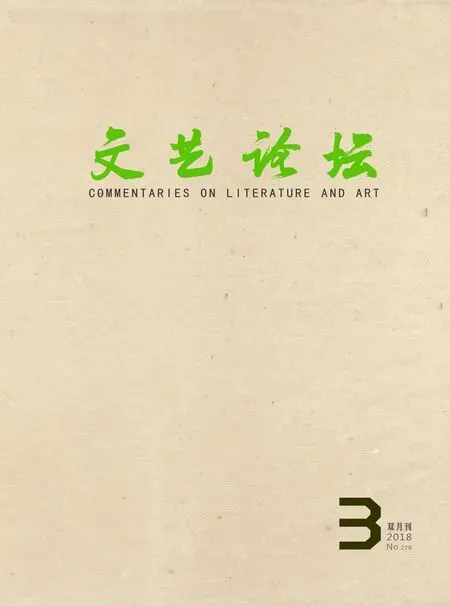规训主体的颠覆与启蒙
——对比《秦腔》与《尘埃落定》的“疯傻视角”
◎石佳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一
《秦腔》以陕南一个村镇为焦点,通过一个疯子的视角,书写了传统农村的巨大变迁与传统文化的失落,流露出作者寄予的深层忧虑与深切同情。作者意在为自己生活过的陕西大地立碑,所立的不是那种歌功颂德的高阁之碑,而是着眼于最逼近真实最赤裸裸血淋淋无滤镜的普通百姓生活的现实与真相之碑。整本书采用了一种“流水账”的方式,但却让人在这些东拼西凑纷繁零落的杂事中分明地感受到了一种浩荡与兴衰,而这,也正是文字大家的功力,是贾平凹的功底展现。这部巨著花费了贾平凹一年多的时间写作,这期间这样大规模的建构写作着实让作者坦诚有些“迷惘”,会担心读者能否认同并接受这样一种展现方式。诚然这样的写作着实能筛选掉不少读者,但只有坚持到最后的读者才能真正被作者带入那一片一气呵成的无人之境。整本书后半段,作者开始在角力与沉浮的大势上发力,每一个情节都不再像前期一样仅仅代表着它本身,而是凝聚在一起,缠绕在一起,仿佛蕴含着命运的密码,让我们看到了一步步的积累、一根根的稻草是如何压垮了夏家,如何侵蚀着清风街的沧海桑田。
“年好过,月好过,日子难过。”这是《秦腔》多次发出的叹息,厚厚600页纸质书页,也不过是故事里的区区几年,那些人的消逝,那些艰辛与坎坷仿佛都是弹指一挥间,但再回顾每一个情节,哪一次悬念不是惊心动魄,哪一次摧残不是无尽的难熬。作者为之立碑的这片土地上养育的世世代代的农民们,都是这样艰难而顽强地跨过一道道艰难与险关,一如作者热爱的中华儿女。
这部作品在贾平凹的所有著作中基本上可以堪称典范了,其原因应该也包括作者的视角与抱负,在一声声“日子难过”中,作者还是希望能够上升到一些民族的整体性层面,而“秦腔”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与仁义礼智信则是作者在琐碎生活背后所希望呈现出的内涵与意义。然而难过的不仅仅是日子,还有作者所钟爱的秦腔与浓郁厚重的陕北文化。在文中我们多次看到作者对于秦腔的衰落和被剥夺而流露出来的愤懑、痛惜、无力与自嘲。当然,衰落的不只有秦腔,还有几个相继逝去的主人公的名字所蕴含的象征意义,仁本就缺场,礼因钱而不在,智慧出现了毛病,义最终只能为自己争的一口气而掩埋,仁义礼智的子孙们纷纷四散零落,最受大家期待的夏风不知所踪,与钟爱秦腔文化的妻子劳燕分飞、背道而驰。
阿来是一位藏族作家,《尘埃落定》写得也是藏族土司家族的故事,展现的是藏族风情,汉字表达也深深烙上了藏族特征。他采取了一种回忆录地方式进行表达,与《阿甘正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是回忆录方式写法,主角同样是被人认为的傻子。相比《阿甘正传》,《尘埃落定》的背景及人物更具民族特色,也更宏大,实话说,读来更觉有深意和韵味。作者后记中显示,阿来有向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致敬之意:“每当想起马尔克斯写完《百年孤独》时的情景,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动。作家走下幽闭的小阁楼,妻子用一种不带问号的口吻问他:克雷地亚上校死了。加西亚·马尔克斯哭了。我想这是一种至美至大的境界。写完这部小说后,我走出家门,把作为这部作品背景的地区重走了一遭,我需要从地理上重新将其感觉一遍。不然,它真要变成小说里那种样子了”。回头思索,阿来确实写了一个历史悠久的土司家族及其兴衰变迁,只不过没有像《百年孤独》里那个家族一样描写了七代人。另外语言中隐隐约约含着冷幽默,居然有米兰·昆德拉语言风格的影子。都说《尘埃落定》是一部藏族史诗,然而我更想探寻作者阿来一直强调和追寻的“普遍性”。异域风情固然引人入胜,然而个中人性与观照视角,我们真的觉得陌生而新鲜吗?我们的文明也何尝不是经历过这样的尘土飞扬,又是怎样归于尘埃落定。
二
关于“疯癫”这个概念,福柯对其有过多次的思考和阐述。人被理解为一个处于历史的、社会的、尤其是权力的关系网络中的存在,是被社会通过知识话语、道德话语等权力话语,以及包括从医院、学校到监狱等各种手段所规训、控制的。在这方面,他为自己提出了问题:“人类主体怎样使自身成为知识之可能的对象,通过哪些合理性形式,通过哪些历史条件,以及最后,付出了什么代价?”而在这个问题的驱使下,福柯展开了对于“疯癫”的思考:是什么导致了理性对疯癫的统治,使得疯癫者只能生活在沉默之中;人们怎样才能说出生病(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或者说,疯癫的主体的真实性何在?
都说《尘埃落定》中的傻子不傻,然而我更想知道,屡屡出奇制胜的、所谓“不傻”的傻子,为何多次被人一口咬定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子,是哪种区别使得他被正常人看做傻子,而这种区别又担负着怎样的意义与使命。为何由“傻”来划出时代与新旧的界限,迎来一段历史的开端。
阿来的普遍性、傻与尘埃落定,或许是这本浩浩汤汤的历史所希望带来的一些冲撞。由傻来翻腾出滚滚红尘,又由傻来让“尘埃”落定。站在时代的交错处,这个傻子拿着他的望远镜,仿佛总能带着一丝神秘意味地看到不远的未来,又犹如神助般看穿历史的趋向。他的目及之处,要么太过遥远,要么完全颠覆,总是与汲汲于眼前、臣服于现实的正常人背道而驰,而这才是他“傻”的精髓所在吧。
由这样的人来完成一个时代的尘埃落定,是再合适不过的了,总要有具备这种“傻劲”的人去结束一段历史并开启一段新生。而芸芸众生的普罗大众,不过是傻子手中翻腾的历史的尘埃,而从另一个角度,没有这样风起云涌的尘埃,也无法覆灭傻子一代人的生命。
傻子最后还是随着自己的家族死去了,虽然不免为他唏嘘,可惜他没有去享受时代变迁后的新生活,然而那也并不属于这样一个时代转折者不是吗?无形中阉割掉了所有土司的繁育能力的傻子,以现代性的方式终结了属于他自己的时代及其延续的可能性,但也并不属于那个新的时代,因此他无处可逃,无形可遁,他的使命早已完成。
而在《秦腔》中,傻子“引生”的命运也颇为相像,同样都是第一视角,同样不被世人理解但是深得周围人的怜悯和同情,也同样有着睿智清晰的头脑和幸免于难的主人公命运。《秦腔》是从引生的角度讲这个故事的,这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有着对生命的博爱和对白雪那纯粹到极致的爱情。引生是一个疯子吗?他孤独地活在这个浑浑噩噩的世界当中,享受着只有自己能享受到的乐趣,忍受着只有自己能忍受的煎熬。最善良,最友爱,最风趣,也最幽默。尤其是他对白雪的那份爱,洁白无瑕。白雪走过的脚印,他会沿着走一遍;白雪流过的泪,他会在地上寻找一遍;……一切跟白雪有关的东西,他都想放在自己身边,他是那么地爱白雪,以至于当不自控侮辱了这份爱时,毅然决然剪掉了自己的阳根……
他反抗一切世俗的污秽,坚定地守护着自己心中的净土——七里沟,他貌似跟谁都合不来,经常做出一些不可理喻的事情,但却有着不容动摇的处事原则和做人标准,他可能没有《尘埃落定》中的傻子那样幸运,能够执掌一方霸业,但他也有属于自己的“小幸运”,幸免于七里沟的坍塌之难,同时保护了心中的挚爱——白雪。
而这样的人为何会被群体设置为“傻子”?他们是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才得以变成了群体眼中的“傻子”?福柯指出,“在所有这些复杂的、重叠着的东西中,您可以看到一种制度的游戏:阶级关系、职业矛盾、知识模式乃至整个历史以及主体和理性都参加了进来”。而福柯把各种各样的自我、性、知识、惩罚、规训等现象,都归结为“权力”运作的产物,把形形色色的社会控制都还原为权力的功能。在理性的历史上,人类对这些论域的合理性的认识与把握是经历了曲折与错误的,这包括错误地对待实际上是心理病人的疯子,在古典时期甚至把他们与罪犯一起监禁,等等。用福柯的话来说,“这个代价是使疯子成为绝对的他者,不光是理论上的代价,而且还是制度上的代价乃至经济上的代价。例如建立精神病学以确定疯子”。
《秦腔》与《尘埃落定》均是两部承载着传统覆灭与新时代来临的小说,波澜壮阔,浩浩荡荡,充满了颠覆与启蒙,其现代性的意味可以说颇为浓厚。在现代性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傻子”这类他者就变得极为显眼而微妙。现代社会是一个以管制和控制为唯一目标的“规训”的社会,通过一系列技术手段,对主体的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和驯服,最终形成现代社会下“规训”的主体,而未进入这种规训的主体则被排斥在规训社会之外,成为他者,成为疯子,最终形成了一个“人死了”的现代社会。“人死了”是福柯继尼采说出“上帝死了”之后的又一惊世骇俗之语。在一次早期访谈中福柯甚至这样说道:“在‘语言说话’的地方,人就不再存在。”这就把“人”归结为受语言规则系统与知识话语所主宰、控制的产物。而两部作品中的傻子,均带着一股沉默的倔强,反抗着传统严格规训的话语体系,显示出一种现代性启蒙的降临与生长。
三
启蒙是现代性绕不过的话题。康德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中这样说道:“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启蒙。”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中对其作出回应,将其解读为一种“否定性”的“精神气质”和“态度”。诚然,这样一种否定性不仅是现代性的标志,也是后现代主义来临的表征。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中在区别“现代性”与“后现代”时写道:“当现代性进而反对这些概念时,它是在追随其最深层的使命,追随其与身俱来的通过断裂与危机来创造的意识。”现代性带着一股冲动,时时刻刻都在否定与颠覆加之自身而上的枷锁。在《秦腔》和《尘埃落定》的最后,都是象征着历史洪流的滚滚红尘的掩埋与覆灭,都是历史遗迹的摧毁与坍塌,它象征着旧制度在新制度下毁灭,纵使旧制度拼命的反抗,一切尘埃落定,它就在新制度建立的万丈光芒中无声的死去,无息的消失。旧制度所代表的“权力”制度的摧毁,为现代性的到来打开了大门,让我们看到“他者”的生存空间似乎有了希望,但两部小说到最后都默契地均未让傻子迎来一个光明的结局和新生活的曙光,这似乎也表明了作者对现代性阶段与程度的彷徨与犹疑,现代性浪潮不断席卷之下,“他者”能有怎样的生存空间和话语权力?规训权力不断瓦解的启蒙疏导下,他者能否迎来真正自由的姿态与生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