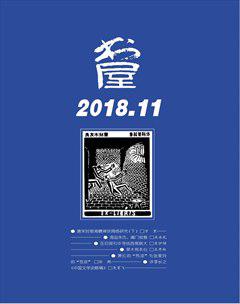萧红的“荒凉”与张爱玲的“苍凉”
徐鲲
一
萧红和张爱玲是两位天才型的女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独特而重要的位置。二人不仅才华出众,而且生命历程和文学作品有不少相似之处,比较二者,能从中发现一些颇有意味的东西。萧红和张爱玲的人生际遇、文学作品及其被接受的过程,至少有四方面相似。
其一,她们各自都生活在一個不和谐的家庭,童年经历可谓不幸,都缺乏父母之爱。萧红出生后就被父亲嫌弃,父女关系冷漠紧张。八岁时丧母,不久父亲再娶,后母对萧红也没什么感情。唯一的亲情之爱来自祖父的关照。张爱玲同样出生在一个不堪的家庭,父母感情不和,经常吵架。父亲是前清遗少,没落贵族,抽鸦片、嫖妓、娶姨太太,生活堕落。张爱玲四岁时,母亲远赴英国游学,父亲不满,幼小的张爱玲成为他的出气筒,经常遭遇虐待。十岁时,父母离异,随后父亲再娶,后母和张爱玲关系紧张,曾因二人闹矛盾,张爱玲被父亲关禁闭达半年之久。
其二,两人都历经沧桑,爱情婚姻遭遇不幸,晚景凄凉。萧红尤甚,萧红短短的一生颠沛流离,爱情婚姻屡遭挫折,先后被几个男人“抛弃”。1942年1月,三十一岁的萧红孤独凄凉地病逝于香港一家医院。张爱玲的人生际遇和爱情婚姻也好不了多少,先是和汉奸文人胡兰成有过短暂的不对等的婚姻(胡是有妇之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移居海外,第二次婚姻也谈不上幸福。晚年幽居,基本断绝与外界往来。1995年9月,七十五岁时在洛杉矶寓所孤独离世,去世一周后才被人发现。
其三,二人都具有文学天赋,在二十五岁前就出版或发表了各自的文学作品,并产生较大影响;而且,作品在精神气质上比较类似,都有一种悲凉氛围或悲剧意识。
其四,二十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国内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书基本未论及二人及其作品,张爱玲更是被屏蔽。到了八十年代,二人如出土文物被重新“发现”,从那时起,萧、张及其作品逐渐为成为现代文学研究的热门课题,成为“显学”,并受到高度评价。
二
如果要从萧、张二人的作品中各自提炼出一个关键词,我认为分别是“荒凉”和“苍凉”,这是一对近义词,在萧、张二人各自的文本中具有提纲挈领的意义。
萧红因为生命历程短暂,所以作品数量并不多,在她为数不多的作品中,《生死场》、《呼兰河传》无疑是代表作。《生死场》是萧红前期的作品,出版于1934年,小说描写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东北一座村庄生与死的故事。那片黑土地灾难深重,村民生活痛苦而麻木,人们像牛马一样生活,“糊糊涂涂地生,乱七八糟地死”。萧红用令人触目惊心的文字,给我们描写了一个令人惊骇的荒凉世界,村民生活的外部环境恶劣,人的精神世界荒芜残缺。《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显示了她的现实主义文学才华。但这篇小说也存在瑕疵,如文本内容的前后“断裂”问题。
《呼兰河传》是萧红后期的作品,是她最成熟的作品之一,更能全面显露她的艺术才华。这本并不算长的长篇小说,我更愿意看作是萧红的童年自传。在这部作品中,萧红开创性地为一个小城——呼兰河作传,她用儿童的视角、自然天成的笔触描画了一幅北方小城荒凉而寂寞的图景。
呼兰河不仅城小而且冷清,只有两条大街,一条南北走向,一条东西走向,构成一个十字型。灰扑扑的马路,车马过后灰尘滚滚,下雨天则是满地泥泞。呼兰河的人们生活在刻板而单调的世界,小城人的日常生活灰暗寂寞,困苦麻木,像北方的大地上的野草自生自灭。贫乏单调的生活滋生了人们的“看客”心理。东二道街有一个大泥坑,正处路中央,不管下雨天晴,它都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吞噬过许多大小动物,车马跌落坑中是常事。而每当有车马跌入坑内,人们都乐于围观,“大家都对它起着无限的关切”,但一次一次的人仰马翻,并没有让谁提出填平泥坑并付诸行动。大泥坑仿佛就是一个戏台,常年上演“喜剧”,大家都乐于在单调贫乏的日子里看戏。填平泥坑等于拆掉了戏台,显得不合时宜。
对于同类的不幸,呼兰河的人们同样乐于围观,并当作生活中的乐子,对老胡家的小团圆媳妇的围观最为典型,小团圆媳妇就是在众人的围观中被滚烫的洗澡水活活烫死的。面对凄惨的情景,面对跳大神的野蛮摧残,围观者包括小团圆媳妇的婆婆都泰然处之。萧红所描写的无意中与鲁迅笔下的“看客”不谋而合,这些看客都愚昧麻木,喜欢围观——不管是悲惨的还是喜庆的场景,不管被围观者是人还是动物。这就是呼兰河,不仅外部世界一片荒凉,而且人心也同样荒凉。
对于萧红自己而言,荒凉感更鲜明,“我”的童年单调寂寞,缺乏父母之爱,唯有祖父给予人间温情,几乎没有同龄玩伴,只能和后花园的蝴蝶蜻蜓、野花野草为伴,“我”家的后花园成为“我”玩乐的天地。《呼兰河传》中作者四次写到“我家是荒凉的”、“我家的院子是很荒凉的”,反复提及荒凉,足见“我”的主观情感之强烈。萧红童年的后花园,让人不禁想起鲁迅童年的百草园,相比而言,多姿多彩的百草园更衬托出萧红童年的孤独寂寞。
从感情和心理上讲,寂寞是萧红童年的关键词。从心理学上分析,童年的成长环境潜移默化地影响一个人的一生。萧红可谓典型,正是童年亲情的缺失和孤独寂寞,使成人后的萧红渴望感情的慰藉,在爱情婚姻中过于依赖男性,以致情感屡屡受挫。她想自立却又无法摆脱对男性的依赖,在这种矛盾心理中纠结而不能自拔,最终在寂寞中孤独离世。1946年,茅盾在为《呼兰河传》所写的序言中,反复运用“寂寞”这个词论述萧红以及呼兰河,多达二十五次。的确,茅盾先生找准了萧红一生的痛点——寂寞。1944年,戴望舒曾拜谒过香港浅水湾旁的萧红墓,并写了一首短诗《萧红墓畔口占》: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长夜漫漫,
你却听海涛闲话。
从深层次探究,萧红的寂寞源自童年生活的荒凉世界,荒凉与寂寞构成了萧红生命历程的因果关系,荒凉是因,寂寞是果。
三
张爱玲作品的核心词毫无疑问是“苍凉”。
《倾城之恋》的结尾有这样一段:“胡琴咿咿呀呀拉着,在万盏灯的夜晚,拉过来又拉过去,说不尽的苍凉的故事——不问也罢!”这一段差不多是张爱玲作品的内容提要或者说情感基调。昏暗、沉闷、冷漠、压抑、孤独、病态等词语构成了她的作品的底色。张爱玲爱用“苍凉”一词,偶尔也会运用“凄凉”和“荒凉”等近义词,表达相近的含义,如《金锁记》的开头:“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我们也许没赶上看见三十年前的月亮……然而,隔着三十年的辛苦路往回看,再好的月亮也不免带点凄凉。”
张爱玲为什么特别偏爱“苍凉”?她在《自己的文章》一文中说出了答案:“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是一种启示。”
张爱玲的作品表现大变动时代都市人的生存景象:人与人之间充满算计,人是伪善狡诈的,人生是荒凉黑暗的,人性是冷漠、自私、卑劣的,世界是病态绝望的。在她的笔下,亲情、爱情、婚姻无不如此。《金锁记》中,主人公曹七巧的人性被金钱和情欲扭曲,行为乖戾变态,不仅破坏了儿子的婚姻,还折磨死了儿媳妇,并葬送了女儿的爱情。曹七巧戴着一副黄金枷锁,扼杀了自己,也扼杀了儿女。《倾城之恋》结局似乎比较圆满,实则苍凉。白流苏和范柳原之间的爱情,更像一场男女之间的“战争”,充满权衡和算计,爱情婚姻基本是男人或女人谋生的手段。白流苏的再嫁和第一次失败的婚姻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将一个男人换成另一个男人,一个家庭变成另一个家庭。张爱玲在年纪轻轻时就洞悉了人世的苍凉悲哀,她显然是一个悲观主义者。
从心理学角度探寻,张爱玲的苍凉和悲剧感同样源自她童年的不幸。暗黑悲惨的童年使张爱玲过早“成熟”,她很早就看透了人世间的苍凉悲哀。聪慧的天赋,加之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在二十多岁初登文坛,就震惊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上海。
萧红的荒凉更多呈现的是外部世界的景象,包括自然环境和人的生存环境,透过这些景象,我们可以感受到作品中人物内心的荒凉。张爱玲的苍凉更多的是指向人生和人性,流露出悲剧意识。张爱玲的小说中外部环境描写没有萧红那样普遍,环境只是人物表现的衬托,张爱玲更关注的是人心、人性。但从根本上讲,荒凉和苍凉并没有本质区别。萧红、张爱玲都描绘了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人的具有悲剧色彩的生存状态,萧红把目光聚焦于乡村和小城镇,张爱玲聚焦的是上海、香港等大都市。
当然,萧红和张爱玲除了相近之处,也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萧红受教育程度较低(高中未毕业),文学才华更多来自天分,所以她的作品更自然质朴,文学技巧不算特别圆熟。张爱玲出生在有文化底蕴的家庭,学历较高,在文学艺术上手法更成熟。如果说萧红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璞,那么张爱玲就是一块闪着冷冷光泽的玉。她们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天空各自闪烁着独特的光芒。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萧红和张爱玲的文学作品均受到文学评论界高度关注。在有些人看来,张爱玲的艺术水平和文学成就在萧红之上。我认为这样的结论不够公允,萧和张的文學风格是属于两种类型的,一个类似乡土民谣,一个类似都市流行曲,虽然都具有悲凉的气质,但二者风格并非同类项,所以不好下谁高谁低的结论。我比较赞同现代文学史家夏志清的说法:“萧红的文学成就一点也不比张爱玲逊色……她是二十世纪中国优秀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将成为此后世世代代都有人阅读的经典之作。”
——一本能够让你对人生有另一种认知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