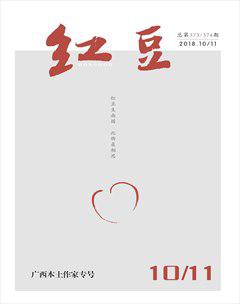母亲,我们送你去远方(散文)
韦毓泉,壮族,副编审,长期供职于文学刊物。
六月,母亲撇下我们,到天堂找父亲团聚去了。
那天,我一大早赶回到老家时,身穿全新寿衣的母亲已经安详地躺在床上。这几年,母亲因患类风湿手脚极度变形,手指弯曲不能握紧,骨节突出僵硬;脚踝骨头变坏,走路时脚掌往里拐,只能拄着拐杖,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挪。而大半辈子承受重担的背和腰也弯成了弓形,每次看见她走路,都感觉是一个瘦小的“7”字在移动。我从没想过闭上眼睛永远睡着的母亲是什么样子,此时见她手脚伸直,背也平平地贴在床上,面容平静,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睡熟了一般,居然一下子没有了亲人永远离去的痛楚。在世时母亲是个残疾人,现在身体已恢复到了常态,在天堂她应该不用领“残疾证”了吧。
我们村地处偏远,土葬还是主要的殡葬方式。而民风,也相对原始和淳朴。老人过世时,村里的乡亲们特别是大家族里的人,不用事主通知,第一个知道的的人,会通知第二个,第二个再通知第三个……到逝者出殡时,村里人应该来的都来了,在附近工作的人知道了也赶回来。他们都要送逝者最后一程,再坐下来一起吃一餐饭。
母亲入殓后,我却担心大家族里没有人来送行,更担心没有人来把棺材抬到墓地去。
五个月前,也就是元旦刚过几天,本家叔叔因为宅基地的事与本家族的人有了激烈的冲突。最后事情和平解决,但我们家与大家族里的其他人心里有了芥蒂。这种芥蒂藏在内心深处,似有似无,看不见,摸不着,说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在合适的时候就有可能发酵,或生根发芽长出枝杈。
母亲的过世,最能检验那场冲突产生的芥蒂是否会发酵。那场冲突母亲和我都不在场,事先、事后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参与,但“爱其人者,兼爱屋上之乌;憎其人者,恶其余胥” 。大家族里的人对本家叔叔有意见,会不会对我和我母亲也有意见?如果他们心存怨恨,这个时候都不来,母亲就这么一个人冷冷清清地走,逝者最后的一点尊严丧失殆尽,创下我们村从来没有过的纪录,母亲如何走得心安?我们脸面何在?而抬棺材的人,一般是大家族外的,他们与大家族里的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不来,彼也不来,辛苦了一辈子的母亲,在村里人缘还算不错的母亲,去世后居然没有人来送行,甚或没有人来抬棺材,这是怎样可怕的一件事!这是怎样让人寒心的一件事!
我们兄妹几个,还有本家叔叔私下里商量,做了最坏的打算。如果真的出现糟糕到极点的情况,我们只能采取另外的殡葬方式。
在忑忐不安中,似乎已陷入困境的我们还是按往时的经验,在大家族的公共大棚里,准备了二十多桌饭菜。赌一赌了,如果真的没有人来吃,我们只好把把这些饭菜倒到鱼塘里喂鱼。
事实证明,我的鸡肠小肚是那么可笑,我的担心是那么多余!大家族里的人,伯,婶,叔,侄,哥,弟,陆陆续续地来了;跟我一个辈分的,比我小很多的小弟小侄,以及他们的媳妇,很多人我都不认识,都来了。他们有的给母亲上香,有的到大棚里去帮忙做饭菜,有的叙说母亲的生平。我们相互打招呼,相互道辛苦,他们都说让我顺变节哀,好像五个月前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一切都按以往的步骤进行。
到了起棺的时候,居然来了二十多人,把摆放棺材的大厅挤得满满的。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悬着的心重重地落了地。原来最担心的这一拨最重要的人终于来了。抬棺什么的一般只需要十个左右,现在居然来了二十多个!
我们子女跟在出殡队伍的后面。走在最前面的人,是负责引幡开路的,紧接着是嘴里一边念叨着一边撒纸錢的,还有一些是不断地放鞭炮的,跟在放鞭炮的人后面的是六个抬棺材的人。从家里到墓地有两公里路,抬棺材的人每走四五百米就要换人。天气不是很热,但是大家走一下,全身都湿透了。
把母亲送进地里后,都回到大棚里吃饭。连外家来的五六十人,大棚里坐得满满的。
作为长子,我是每个桌子都要过去跟大家说一下话的。走到一半,满头斑白的八婶把我拉住,让我坐在她身边,她说:“你母亲走了,我们是要来的,大家都要来。以前不管有什么事,都不如这样的事重要。你母亲辛劳一生,但子女都有了出息,她可以安心地走了。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就是你还有个哥哥,不知道他在哪里,情况怎么样。如果他能来送一下你的母亲,你母亲就没有什么遗憾了。”
八婶的话吓了我一大跳。原来很多人都知道母亲还有个儿子啊。母亲嫁给父亲之前,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母亲起初是嫁到邻近的苏家村的。那年她嫁给了苏家,七八个月后生下了一个男孩。苏家人高兴之余,感觉哪里不对劲,看来看去,男孩的长相都不像他的父亲。又算来算去,发现这小孩生得早了一点。于是他们认为这小孩不是苏家的种,苏家是蒙受了奇耻大辱。大家做出一致决定,把我的母亲赶出苏家。母亲哭肿了眼,但她讷于分辩,只会反复地说小孩子就是苏家的。当时除了小孩出生的时间早一点,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小孩不是苏家的,但没有人相信母亲的话。那个冬天的早上,北风呼呼地吹,还下着小雨,隔壁的大嫂帮她把刚出生几个月的小孩背到背上,一边帮系背袋的绳子一边掉眼泪:“妹子,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但我们女人的命有时就是这么苦。你千万要挺过这一关,再找个好人家,把孩子好好地抚养大。”告别隔壁的大嫂,母亲背着自己的骨肉,在冷风细雨中迈出小脚,一步一步地向娘家的方向走去。
背着不满一岁的小男孩走到腾翔街时,母亲累了,便到街上堂哥的家歇一歇。堂哥知道情况后,让人骑车去通知外公外婆。在他们商议母亲以后的生活时,一对夫妇到母亲堂哥店里买东西。这对夫妇是从柳州到腾翔来打零工的,看到两眼红肿的母亲,关心地问了一下。得知母亲的情况后,他们用征询的口气问:“我们三十多岁了,还没有小孩。这小孩能否送给我们抚养呢?”外公外婆他们商量了很久,最终决定把这小男孩送给这对柳州夫妇。
母亲从来没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我是不久前才从苏家村的一个朋友嘴里得知的。八婶今天提起这事,让我百感交集。从未谋面的亲爱的哥哥,你知道你的亲生母亲是谁吗?你现在在哪里呢?你一切都好吗?母亲忍痛舍弃亲骨肉,离别两茫茫,长思量,怎能忘?只是无缘再相见。相信这是母亲一辈子都埋在心底的苦悲。亲爱的哥哥,今天,我们的母亲走了,你知道吗?
母亲后来是怎么嫁给父亲的,我不知道。但从我记事起,父母经常吵架,甚至打架。有一次刚吵几句,父亲火起,抄起扁担就往母亲的腰抡去。母亲一下子瘫在地上。她哭了大半天,当天就回了外婆家。我常常在心里想着为什么父母老是吵架、打架。父亲高中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又到化工学院学习了几年,算是有点文化的人,是不是他看不起目不识丁的母亲?父亲样子长得不错,从没谈过恋爱,是他嫌弃个矮貌丑且有过婚史被赶出夫家的母亲?这些问题在我的脑子里储存了几十年,父母从来不提,我也不敢让它们蹦出来,就是怕在母亲深深的伤痕里再撒上一把盐。
我回到自己的座位坐下后,一向跟我们家走得最近的三叔、三婶坐到了我的身边。三婶说:“你母亲没有别的手艺,就是靠种点养点,硬是默默地把你们几个小孩抚养成人,还送你上了大学,她吃多少苦呀。要一辈子都记得你母亲啊。”
三婶像在说教,但她的话句句直锥我心扉。父亲母亲送我读书的一些情景,一下子掠过我的脑袋。
父亲、母亲虽然吵吵闹闹,有时还打架,但他们有一个难得的共识就是要尽自己的能力送小孩读书。无论家里怎么穷,他们都咬紧牙关,三个孩子书读到哪里,就送到哪里。
我是到离家十二三公里的一个镇的初中读书的。开学那天天下大雨,父亲从舅舅那里借了一辆自行车,在雨里的泥沙路上小心翼翼地行驶,把我艰难地驮到了学校。当时每个月的伙食费是5元。家里没有任何说得过去的经济收入,也没有自行车,为了解决这5元钱,父亲和母亲常常不亮就从家里出发,每个人肩上挑着四五十斤重的青菜,一步一步地挑到我读书的镇上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斤生菜、春菜也就两三分钱,他们这一趟来回三十多公里的买卖的收入也就三块多钱。这还是比较乐观的收入,如果是下雨天菜不好卖,一趟下来也就一两块钱。分分血汗钱啊!每次我从他们手里接过这浸满血汗的伙食费时,手都禁不住发抖,暗下决心好努力读书,将来好好地报效父母。
我没有让他们失望,以较高的分数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为了方便给我送米送钱,父亲咬咬牙买了一部自行车。高二那年的一天,父母居然都来了,来给我送钱。在校门口,父亲说:“你母亲没上过学,想来看看我们县最高学府是什么样子。”我问他们是否要到校园里去走走。母亲想都没想,连连摆手,说不进了。我内心深处也不希望母亲进去。母亲身高不到一米五,头发黄,颧骨高,眼睛细,大字不认得一个,我担心同学们看到母亲会取笑我,也担心母亲进到如此离她的生活很远很远的高雅的校园会无意中受到伤害,见母亲说不进去,心里暗暗地松了一口气。他们走后半个钟,父亲满头大汗、垂头丧气地推着后轮没了气的自行车到宿舍找我,跟我走到校门口。母亲正站在那里,好像做错了什么,局促不安。父亲用不友好的口气对母亲说:“叫你不来了,你偏要来。车子搭上你,胎子都爆了。离家二十公里,我们怎么回去?”原来是自行车爆胎了。母亲一脸的惶恐,双手紧紧地绞着,额头不停地冒汗。父母已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我,车子坏了他们居然没有钱补胎,只好回来向我“借”。我拿出十块钱,让他们在路上吃点东西什么的。母亲连连说不饿,最后他们只要了一块五钱。
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太累,走的路太多,承受的重量太大,父亲、母亲前几年背就驼了,脚也没劲了,他们两个人都领到了残疾证。
和天下所有的农民一样,哪怕辛苦了一辈子,做父母的到死也不想给子女增添什么麻烦。母亲在县医院住院时,身体检查的结果是:严重的心脏衰竭;高压近200的高血压;便黑,可能是胃穿孔。我私下问医生,医生说六七十斤这么瘦的人血压近200,很少见,最要紧的是心脏衰竭,随时有生命危险,家属最好24小时在身边。
医院用上了最好的救治方案,但母亲的身体没见好转。五月底,母亲老说要出院。也许母亲感觉到了在世的时间已不多,她不愿在医院里离开人世,她要回到生活了五十多年的家里再走。我们兄妹几个商量并征求舅舅和叔叔的意见,决定让母亲出院。医生尊重我们的意见,给母亲打了几支强心剂后让我们办理了出院手续。
住院前,母亲让我们清点了她的现金,要求我们一定要用这些钱支付她的住院费用。“新農合”报销了大部分费用,母亲的钱支付了这些费用后,还有一万多,她要求我们把这些钱都用在她的葬礼上。那二十多桌饭菜,就是用她省吃俭用抠下来的钱置办的。
我们家里的事三婶当然不清楚,她唠唠叨叨地说了母亲的很多辛劳和美德。她和三叔离开后,我转向做“辛苦”的那些人。
我们这里把挖坑、抬棺、埋土的人叫“辛苦”。他们都是清一色的汉子,年龄从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他们都是自愿而来,除了在事主家吃一餐饭外,没有任何报酬。
此时他们正在长桌上吃饭。年长一些的我认识,雪哥,大旭,明哥,大茂,小群,遥弟,基本上是同龄人,我十二岁才到外地去读书,跟他们还是很熟的。大茂是我的小学同学,小学时个子跟我差不多,我们经常打架,互有胜负。小很多的不认识,只好问他们的父亲是谁。
我特别惊讶的是,村里的首富彦哥也来做“辛苦”。彦哥经营石场,身家千万,此时也像其他的“辛苦”一样在长桌边吃饭。其实在送殡的路上,我早就注意到他。在两公里多的路途中,他先跟在后面,过了村里的鱼塘时,他接过其中一个人的木杠,很熟练地把木杠搁在肩膀上。阳光不是很猛,但很快,他那件价值不菲的衣服湿透了。他城里村里都有房子,平时不太在村里住,此时这么热的天,他完全可以坐在城里的空调房里喝茶聊天什么的,可是他也来了。我不知道他是刚好有事回到村里,碰上我母亲出殡,也担当了送殡的一员,还是专程回来的。
此时我只觉得非常愧对这些好兄弟。他们跟我不是同一族的,平时也没有很多的走动。偶尔回老家,有时碰到了只打个招呼,有时在车上明明看到了他们,却连车窗都没有揺下,呼的一声就从他们身边疾驰而去。有一次雪哥打来电话,说村里给上级打了报告申请经费修路,想让我对报告做些润色,我推说太忙,对情况也不熟悉,拒绝了他的请求。小群身体不好,有一次居然打电话问我借钱说要动手术。多年不联系,突然问借钱,虽然他的语气非常诚恳忧伤难为情,我仍然很反感,直接说手头紧张没有闲钱。明哥是热心人,常找同村老乡聚会,也叫了我几次,我都推辞了。没能帮村里的人做些事我也觉得有些内疚,但一想到我是在外面工作的,吃的是外面的米,喝的是外面的水,跟他们八竿子打不到一块,跟他们很少有交集的时候,何必扯上关系徒增烦恼呢?他们家的老人过世,有些我是知道的,但从来没想到这些跟我有什么关系,更没想到要去送一送。单位或系统的人走了,是要去送送的,而村里的老人过世,我至今没送过一个。至于“辛苦”,一向很忌讳,认为是做苦力的地位低下的人做的,自己做“辛苦的”念头,一个小泡都没在脑子里冒过。
今天,这些我认为可能一辈子都没有什么更多关系的人,这些在我的内心没有什么位置的人,这些我无意中伤害过的人,不计较我曾经的冷漠或无礼,来了,都来了。他们不惜用自己的力气和汗水,把一个跟他们没有关系的老人,安安心心地送到泥土的深处。
母亲啊,你走得坦然、走得从容、走得安心,全是因为有了这么多可亲可敬可爱的乡亲。如果你泉下有知,一定会好好地感谢他们的。
责任编辑 宁炳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