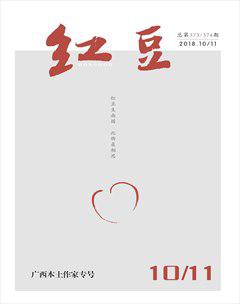黑天鹅之死
李欣,女,广西南宁人,生于20世纪70年代,现供职于广西交通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
那只黑天鹅大概没有想到,它的死亡竟会如此狼狈和意外。法国作曲家圣桑在组曲《动物狂欢节——天鹅》里用大提琴和钢琴描绘了一个高贵娴雅的生灵,它在幽静的湖面上慢慢游弋,自由而又从容;俄国芭蕾舞蹈家巴甫洛娃则将这一曲子演绎成了一段哀婉悲情的舞蹈,那是一只天鹅在绝望中的求生。从《天鹅》到《天鹅之死》如此相同,又迥然相异。
黑天鹅在自己家门口悠闲地散着步(如果公园也能称之为“家”的话),它从未意识到早有两双贪婪的眼睛盯住了自己。2017年5月的某个凌晨,一只半岁大的黑天鹅被人从上海徐家汇公园偷走,之后它死了,原因不明,很有可能是因为窒息。它大概是被包裹在衣物或者塑料袋中,由于害怕被保安和路人发现,黑天鹅一定是被紧紧地捂着,在不断地挣扎、扭动和嘶叫中死去。
天鹅,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因为体型优美、仪态高贵而深受人们喜爱,它们对于伴侣的忠诚被认为是爱情的象征。这样美丽的生物,激发了多少艺术家的创作灵感:柴可夫斯基的《天鹅湖》是一曲爱情的颂歌;安徒生的《丑小鸭》是一则关于天鹅纯真本质的童话;巴甫洛娃演绎的天鹅纵然濒临死亡,却依旧用优雅的姿态来面对。
然而这只黑天鹅却得不到那样的期许和赞叹了。它尚未成年,没来得及体会到爱情的滋味就被偷走;它的羽翼还不够丰满,估计还没尝试到展翅翱翔的快乐;甚至连最后的挽歌它都未能及时吟唱就忽然死亡了。而后它的肉体,一部分和一根廉价的萝卜炖在一起,成为了人类的下酒菜;另一部分因为“口感不好”被当作垃圾丢弃了。
结局竟会是这样。在大多数人的眼里,天鹅应当和《红楼梦》里的林妹妹一样“质本洁来还洁去”才对,它理应带着银白的光环和动人的音乐慢慢从人们的视野里消失,然后在一处宁静而且水草丰茂的地方迎接死神到来,这才是人们赋予天鹅的正常死亡。如果在弱肉强食的自然界里,它极有可能丧生在一只狡猾的狐狸或者凶残的豺狗口中。那些凶猛的动物是不会嫌弃天鹅肉的,它们肯定饥不择食,此等美味的食物可不会时时都有,所以它们绝不会暴殄天物,说不定心里面还在暗暗感谢上天馈赠。这是自然的法则,属于动物的天性和本能。
可是在这个人类构建的文明社会里,被视为高尚珍稀的天鹅却给盗杀了,理由仅仅是因为要“改善伙食”。这算是写给人类自己的冷幽默吧。
俗语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这是对图谋不轨的最佳写照。可吃天鹅肉并不是癞蛤蟆的本性。癞蛤蟆居住在潮湿的草丛和泥地里,以甲虫、蜗牛、蝇蚁等小生物为食,它的食谱里绝不会有天鹅这种高等物种的,癞蛤蟆与天鹅的纠缠完全是出自人类自作聪明的想象,最终它成为了滑稽可笑的形象。其实,真正想吃天鹅的是人类本身,只不过人类将自己的贪欲投射到动物身上,让癞蛤蟆被莫须有地羞辱了一把。
人们谈论此事都是语带嘲讽、面露不屑的样子。我听到一些媒体评论员在用一种调侃的口吻在做点评,当然他们主要是批评两个贼居心不良,并借此呼吁要提高公民的道德素养和改进对公共财物的保护等等。那只天鹅呢?即便谈论起它,也只是将之视为起衬托作用的背景板,没有人留意到它曾经历的苦难,时间一久,不会再有人想起那一摊融化掉的腐肉。
人类是万物之灵,是世界的主宰。我们胜于其他动物的地方在于会创造和使用工具。老虎和狮子能用尖利的牙齿和爪子撕碎猎物,我们则用子弹和匕首击倒对手。老鹰和大雁可以在云层穿梭,我们则能借助飞机和热气球在天空飞翔。我们崇拜猛兽的勇敢和威严,也为鸟类的自由飞行而着迷。可惜它们离我们太远,不便于近距离欣赏,所以我们建筑了动物园。豺狼虎豹、蛇虫鼠蚁被从自然界里捕获而来,它们被局囿在装有电网、铁丝和玻璃幕墙的有限空间里,而我们则在栏杆外欣赏着它们的进食、便溺、交配。有人自认为是征服者而感到沾沾自喜,于是冲着笼子里的动物大声嚷嚷:“蠢货,有本事出来呀,来咬我呀!”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安全是依靠了一些设备,如果在自然界里,只怕他们早已是肉食动物的口粮。当然,更多时候我们是在表现出人類的怜悯和慈悲:我们理解失去自由的痛苦,所以我们给动物设计了各种娱乐活动来舒缓身心;再用特意调制的营养品和饲料将动物喂养得胖乎乎的,以此来证明人类的善意和爱心。
人之初,性本善。这是个很多人都明白的道理,然而有人却不愿将这份善良赠予动物,尤其是鸟类。和猛兽相比,鸟儿过于纤细和小巧,所以被欺凌是常有的事。就像那只黑天鹅,不过如平常般散步,却无意招来杀身之祸,究其原因,无非是因为它很弱小,根本无力反抗贪念滋生的人类。
细看近几年的新闻,发现黑天鹅被侵害的事件并不少见:2017年3月,扬州市瘦西湖公园内,一个游客不仅脚踢黑天鹅,还踩碎了两枚天鹅蛋;2017年2月,泰安市泰山天鹅湖景区5枚天鹅蛋被盗,导致黑天鹅夫妇绝食;2015年12月,湖州西山漾城市湿地公园2只天鹅和5枚天鹅蛋被盗……
在芭蕾舞剧《天鹅湖》和电影《黑天鹅》中被引喻为机敏、充满反抗精神的黑天鹅在现实中却成为了受害者,是创作者误解了黑天鹅的真实形象吗?依我之见,并不是。城市里的公园需要有动物的点缀,所以引进天鹅来饲养是常有的事。黑天鹅繁殖数量多,当然成为了关注的重点。正如小说里的情节一样,美丽的角色往往很容易招致邪恶的垂涎,黑天鹅的灵动与优美同样也引来了窃贼的注意。
何止是黑天鹅,许多鸟类也都面临着危险的境遇。
春节过后,一个温暖的下午,我在江北大道散步。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下面有一个魁梧的男人拿着弹弓瞄准了树上的某处。树梢上传来了鸟儿欢快的鸣叫,高高低低、细细碎碎地交织在一起,仿佛一首奏鸣曲。不用猜也知道那男人想做什么了。我站在一旁留意了很久,那男人似乎很专注,盯着目标一动不动。我们有些胶着,像是在比赛耐心,最后我还是没能坚持下来,只好离去。走出一段路后,我听到身后传来鸟群的一阵嘈杂声,好像有扑打翅膀的声音,但很快又安静下来,这之后,再没有一丝鸟儿的动静了。我回头望去,树荫挡住了视线,那男人好像不见了,我不知道他是否命中了目标,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可终究那一树的鸟儿是缄默了。
小时候就常看到调皮的男生用弹弓去打树上的鸟儿。如果打中了,男孩们就欢呼一片,拿着受伤或者死去的鸟儿四处炫耀,好像完成了一件了不得的杰作。随着年岁渐长,慢慢地男孩们不再打鸟儿,一则是因为接受了老师的教育,知道鸟儿对人类的益处;二则是后来能让他们开心的游戏太多了,所以他们放弃了弹弓。真不知道为什么时至今日还有人喜欢打鸟取乐。是因为鸟鸣惊扰了他的美梦吗?还是小鸟恶作剧将粪便拉在了他的衣服上?这二者似乎都不是很好的借口。我猜想,他们纯粹只是为了娱乐而已。他们带着不怀好意的笑脸,眼神里闪动着残忍的光芒,犹如自然界的野兽一般注视着猎物,一旦时机出现立即动手。野兽是为了果腹才去捕食其他小动物,而他们是为了在猎杀中寻找快感。在人类的社会里,排遣休闲有很多种方式,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非要选择了与野兽相似的那一种。
我的工作是要在野外开展的。乡野之地,应该如文学作品中描写的那样恬静安逸,可这其中却常掺杂了许多的不和谐。好几次我在密林和沿江边发现了一种网,是用透明鱼线织成的,挂在半空中让人难以察觉。鱼线被绷紧后会变得如刀片般锋利,不小心被刮到,必定会出血。幸亏请来当向导的村民及时发觉才使我免于受伤。听他们说,这是当地人用来捕小鸟的,小鸟飞到半空中一头扎入网眼里就再也无法逃脱。我打量着这些网,虽然是透明的,但细细看还是能看到上面暗褐色的污迹和一片片细细的绒毛;凑近了,还能闻到一阵腥臭的味道,这和清新的自然气息是那样格格不入。
前些年我到一个县城出差,一条江水连接了各个小村庄,村道蜿蜒在山间。沿着江岸走,一路都挂着网,如果不是一团团不同颜色的羽毛在微微抖动,不会有人留意到这无形的杀器。抬起头,立即看到一只死去的小鸟,它张着嘴,一双黑黑的小眼睛瞪得圆鼓鼓的,一副惊愕突兀的样子。这样死去的小鸟有很多,它们小小的身躯不再动弹,变成了悬挂在半空中的一个个黑点。向导说,每年入冬和初春的季节有很多小鸟打江上飞过,这里每天都能缠住不少鸟儿。被网住的鸟吱吱地叫着,不停地扇动着翅膀,但是越用力就缠得越紧,渐渐地叫不出声来了,只能偶尔扑腾几下。傍晚时候拉网的人会来查看,死了的鸟被扔在地上,晚上野狗山猫会来叼去吃了;还活着的被扯下来关进笼子里卖到夜市去。一只小鸟价值一元钱。
人类总是喜欢将自己幻想为鸟:我们渴望插上鹰隼般强有力的双翼,这样就可以翱翔在天空之上;我们希望能拥有黄莺似的悦耳歌喉,这样就可以打动听众的心房;我们期待像天鹅那样对爱情忠贞,一生一世真诚到老。于是我们用各种艺术形式来赞美、歌颂它们;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借助了由“智慧”所产生的工具来捕抓它们,褪去羽毛、折断双翅,又或者偷走它们的卵和幼雏,让它们在痛苦和绝望中哀嚎甚至死去。慈悲和冷酷,怜悯和残忍,这是人类情感中的对立面,一方面出自贪婪的野心,另一方面源于潜在的人性。我们就在矛盾中彷徨苦闷,不得安宁。希区柯克的电影《鸟》中描绘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发生的故事:平日里温顺可爱的鸟类对人类发起了一场又一场襲击,它们尖利的爪和喙让人类仓皇失措无所遁逃。当人们藏身在电话亭和阁楼中时,那种恐惧和失落能否让你想起被囚禁在笼中的鸟儿?希区柯克没有在电影中揭示鸟群为何会失控,人类又是怎样脱离困境的,但最终我们都知道:在突如其来的灾难当中,人类和鸟类一样都是如此弱小和无助。我们是否可以设身处地想象一下,如果将鸟儿承受的劫难施加于自己身上,那可会是一场欢愉的经历?
五象湖公园里有好多水禽:黑天鹅、白天鹅、鸳鸯、野鸭。水鸟们并不怕人,常飞到木栈道上歇脚,有时游人凑近来跟它们打招呼,它们就会转动着小眼睛歪着脖子左右打量来人,样子十分逗趣。三月份的时候黑天鹅增多了,是一只小宝宝,那时它还没有披上黑袍,还是灰不溜秋的样子。它浮在湖上,两只脚蹼不停地拍打着水面,努力地跟在父母身后。大天鹅缓慢地游着,偶尔回过头来望一下小天鹅,如果孩子游得慢了,大天鹅就会弯下颈子,伸嘴去啄它一下。太阳底下常常传来天鹅高亢清亮的叫声“昂昂昂”,不知道这是天鹅欢乐抑或悲伤地呼唤。权当它们是在开心地歌唱好了,至少在这个温暖的城市里它们还没有受到伤害。
朱光潜先生说:“残酷的倾向,似乎不是某一个民族所有的,它像是盲肠一样由原始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还没有被文化洗刷净尽。”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较之以前早已是大步地前进,也该把那种残忍的劣性抛弃了。不论是圣桑的《天鹅》还是巴甫洛娃的《天鹅之死》,都不应当是无奈的绝唱。
责任编辑 练彩利
特邀编辑 张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