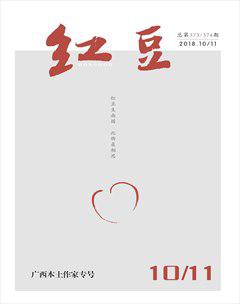乡邻人物三题
伍飞跃,1965年6月生,籍贯广西全州,1987年广西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文学学士学位。曾在广西电视台文体频道、体育频道、公共频道等做过副总监。现任广西电视台办公室副主任,主任编辑。
“苞谷”国华
国华是我的堂兄,长我三岁。至于为什么叫“苞谷”,我不知他的来历。
堂兄是我的真堂兄,他有三兄弟,我伯父的儿子。我家也是三兄弟。不同的是,我们三兄弟都托高考政策的福,考上了大学,在外面有了“体面”的工作。而堂兄家的三人,却无人上高中,早早就辍了学。村里人常说,是我祖父下葬的时候,头向右多拐了点,所以福气全让我家占了。
并不是伯父没有实力供养,而是他们确实不是读书的料。伯父在村里曾经担任过队长,堂兄三人得其滋养,个个长得面容方正,身材修长,所以都娶得一房好媳妇,在村里有个好口碑,日子过得有模有样。
其他两兄弟还好说,唯独国华性格有些怪,不合群,不跟人抽烟喝酒,还动辄发脾气,跟他外号还真有点像。开始时媳妇们很不消受,时间久了也就习以为常。年二十八,我刚一到家,妈跟我说,今年封岁各做各的,不要和他们一起了,说是堂兄说的。我问啥意思。妈说国华嫌人多,做起饭来太累,他不干了。我想这是啥子事啊?平时聚餐都是我们掏钱,杀鸭杀鸡由媳妇们负责,在我家一起吃,他没出过多少力,他累什么累?凭什么?但一转念想到他的怪脾气,这样各自轻松,也就释然了。
堂兄是这些年一直留守在家从事农业的人,他的努力可以代表村里的一部分人。日子虽然没有像外出打工做包工头大富大贵,但日积月累下来,该有的还是有的。
过完小年过春节,拜完祖宗拜长辈,这年的春节也就差不多了。我想明天就走了。
就在我准备晚餐时,妈跟我说晚上有大餐,在国华家吃。
妈说:“他家新媳妇上门,正高兴着呢!”
到晚上,一大家子又像往年一样,济济三桌,热闹非凡。炭火吐旺,米酒飘香,腊肘子、醋血鸭、粉丝鸡、腊猪肝、酿田螺、水库香鱼、高山崽牛,盛不下的家乡美味;行酒令、猜码声,此起彼伏,杯盘狼藉。这才是过年的样子。
国华是后半才上桌——这是我老家的习俗,主人家要亲自掌厨,摆弄手艺,才显得热情好客。
大家吃得香,聊得欢,调侃新人。新人有些生,藏躲在后面,根本看不见,下次遇见还是识不得。我倒是奇怪堂哥今天的失态,频频举杯,话语啰唆,似乎有点上头。
我故意逗他,说:“媳妇有了,儿子桂林的房子装修好了,是不是到城里去住?”
“不去,不去。”他跟我来了个满大碗,“去城里干吗?我在家种十多亩,每年得个五六万,吃蔬菜葱蒜不要钱,随便摘就是,比你嘛差!”
“土鸡土鸭不要钱,自己养的,原生态。”国华有些醉意。
“米饭可以吧?告诉你个秘密,这是二苗大米。你们吃的米,我们从来不吃,那米能吃吗?全是化肥农药喂出的!”
“走的时候送你一袋,送些给你朋友尝尝,给领导尝尝……”
堂兄醉了,真有些醉了!
回来的路上,我也有点醉。南风渐起,清风拂面,不觉凉意。仰望星空,繁星点点,清透得深不见底。我自言自语道:“乡下真好!人好,房子好,空气最好!”媳妇在后面说:“怎么?后悔出去了吧!习大大不是刚说过吗——以后,要让你们城里人羡慕农村人的生活!”我无话搭理,心里却在默念着。身子跟随着晃晃悠悠的手电光,踉踉跄跄走回了老宅。
“嘎子”斌斌
嘎子斌斌在村里可是个风云人物。
他是羊头村里第一个外出打工的。那时我还在读大学。
他人胆大敢为,为人又大方,讲江湖义气,很快夹金带银回家,在村口头建起了两层水泥楼房。
当时说钱不太够,所以在起了个毛坯后就搬进了。虽是毛坯,却很突兀,在周围鳞次櫛比的瓦楞中,显得格外张扬,极不协调。
嘎子和我最亲。我俩家的老宅门对门,算辈分他是侄子我是叔;算妈的关系,他是表哥我是表弟。我俩的妈是同村堂姐妹。
嘎子年长我两岁,打小身体好,长我一个头,时常帮我干些力气活。让我印象深刻的一次是,我们一起上越城岭打柴,担柴回来的路上,因为贪多,我慢慢落了单。但每在我又惊又饿的时候,嘎子哥就折回来了,帮我挑一程,一段一段,来来回回,接应到家。
这件事让我记住了一辈子。
后来,他外出打工,我上大学,大家的见面次数就少了。他搬进新房后,离我家又远了一些,见面就更少了,慢慢越发生疏了。
再后来,村里人出外打工的越来越多,老家起的水泥房像笋子样多起来。有长方的,有方正的;有两层的,有三层的;有白色的、青色的、红色的,还有黄色的;各式各样,各色各样。我家的瓦房子就越发寒碜,有点像围城里的钉子户。
还有不协调的,就是嘎子家的毛坯房,多年还是老样子,日晒雨淋,水泥都发了白。听说,这些年嘎子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子女又多,所以没钱装修。
八九年前——应该不到十年,在省城里工作的我,突然接到嘎子老婆的电话,气喘吁吁说他被人抬进江滨医院,好像是中风脑梗,不行了,问我有没有熟人,看能否帮上什么忙。我尽力搜索,想到好像有个同学的弟弟在那里做财务,于是赶紧打电话叫关照一下。到下午下班,我赶到医院,见到人已经不能说话,只是握住我的手不放。他媳妇说,中午还和人喝酒,没想到下午送客人时,突然间就倒地了,还好离这家医院近,大家帮忙抬到这里。
“你能不能先垫点钱?”他媳妇说医院钱不够不接收。
我帮他垫支了住院费,医院算是收住了。离开时,他拉住我的手不放。到门口我回看,看到他的眼角微微挂着两滴泪,格外显眼,我心里涌起了一阵酸楚。
大概住了一段时间,花光了钱,康复治疗再也付不起了,就被孩子接回老家了。
那年春节我回家,看到他家大门紧闭,了无生烟,但我知道他在家,脚步不自觉向前挪动,想去看看躺在床上的他,却被母亲叫住了,不叫我去,说怕我沾了晦气。听我妹说,嘎子回来可惨了,躺着动弹不得,整天被老婆指桑骂槐……而且传言两个人正在闹离婚。
最近几年过年,我有时在乡下过,有时在城里住。渐渐地我越来越少见嘎子,在我的记忆里他好像已经不太存在。
年二九,上山封岁回转,路过嘎子宅子,突然听到隐约有人叫我小名,循声望去,看到嘎子倚在他家门口。冬天的暖阳包裹着他,有点像我印象中过世的爷爷,当时就是这种情景。我妹提示我,说是嘎子。我走过去,近看他,见他神情还可以,老了些,黑了些,但不像得重病的样子。
他告诉我,现在可以干活了。
这让我有些诧异,印象中这种病很难好起来,他有这种状态还真少有。
“我不想死,我要好起来,我天天走路锻炼,我上山自己挖草药……”他言语多起来,一咕噜数着,让我脑子有些走神——确实,村里有人得癌症开刀,说活不过三年,现在已经活了十三年了,而且还能喝半斤酒……
我问:“现在过得怎么样?”
他说:“现在可以了,贫困户补助,药可以报销些,每个月政府有些钱补,在村里收垃圾,每个月有五百多。”
聊起他的病,他说:“有事做,身子反而灵活了。”
“你莫担心,不要紧了……”
这次我们聊得很久。
回家的路上,我一路一回头,看到曾经的水田崛起很多新起的楼房,新鲜整洁有些别墅的样子。而嘎子的房子还是老样子,挤在欠规划的里间,和二十年前一样,还是那样不协调。
“农村还真的是病不起,但是病好起来比城里人要快!”我妈见我高兴说。
“斌斌现在好了,家里也和气啦!”妈继续说,“过几天他生日,好像是五十五寿,他儿子要给他过,你不在家,要不要打个红包?”
我高声说:“当然要打啦!还要打多点。”
“贼老板”翟家和
我老家人喜欢给人起外号。
荔浦县的翟家和来承包土地,就是现在的流行说法叫土地流转,村里人见他胆大,性格活络,我们那里人叽里呱啦讲土话,“翟”“贼”不分,就随手给他起了个雅号“贼老板”。
我因为回家过年,被单位交代了任务,要做调查,建言献策,需要琢磨琢磨。
事情有点麻烦,心想农村情况复杂得很——小村庄,大中华,自己脱离农村三十多年,一周能做什么事?胡言乱语怕要被人笑话了。
话虽如此,任务还是要完成的。思来想去,觉得农村有三种人是能够代表乡村特有经济现象的:一种出外打工做包工头“老板”的;一种常年在家务农的;还有就是最近两三年时兴的承包土地,搞土地流转的。把这三种人的现状写出来,算是一种交差吧。
前两种人,我选择最熟悉的国华和斌斌,后一个村干推荐我从没见过面的“贼老板”——他恰巧就租住在我家老宅子。
前两年,我是有机会一睹“贼老板”真颜的,但是因为他的砂糖橘没挂果,每到春节,他就提前回老家了。今年果已黄熟,估计采访他没问题,但还是没见到,他又回荔浦了。
回城的前一天晚上,南风大作,吹得老树弯了腰,屋瓦翻了个。早晨起来,路面被刮得干干净净,像清水冲洗过一遍似的。路过老宅子,看见屋顶冒着青烟,心想运气还不错,老翟回来了。
吃过早饭,拿着病历本走去——几年没做记者工作,采访本没了——翻遍车厢,只有病历本在,将就用吧。
老宅很大很空,早已没人住。但这是我孩提时蹦跶乱跳的地方,我太熟悉了。
在里屋靠边的地方,一个人正在摆弄摩托车,估计是要出门。
“我是这宅子的老人,叫……”我突兀地说,缺底气有点生,似乎他是宅子的主人。
他扭过头看着我,有点惊鄂。
在他抬头一瞬间,我打量他,觉得这是一张似乎有些熟悉的脸,跟我从前的一个荔浦同事有些像。中等偏瘦身材,国字偏型脸,颧骨微凸,双眼微眯,配上两撇稀疏的八字胡,整个人不笑而笑,让人感觉亲近。
“我想采访你,我是广西电视台的,要来采访你,看看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情况。”
他愣了愣之后,很快就定了神。“这个吗?这个我们不太好说。这两天刮大风,把树上盖的膜吹走了,我们可惨了!”我想这是个闯荡江湖的人。他理解错了,他可能是把我看成是政府補贴的人。
我掏出一支烟,递给他,再次解释我的意图。
这回他清楚了。在很快看出我对他没有多少帮助后,他的神情略有些失望。之后只是应付着我,但因为我有备而来,早就拟好了提纲,所以不到半小时,我就完成了任务,了解到基本情况。
问完基本情况后,我跟他套近乎,说我是这家的老人,他说早就看出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说。
“你跟他有些像。”他指着墙上我父亲的遗像说。这么快的观察力!我感觉到这个“贼老板”还真是个精明人。
在祝他新年快乐生意兴隆后,我转身准备离开。就在我快到家门时,他骑车赶到我身边,戛然停住,大声说,“走,我带你到地里去看看,尝尝你们家水田种出的果。”
来到我家的老水田边,映入眼帘的是绿油油一片,与周围的枯黄景色截然分开。近看,每棵树下挂满了黄澄澄砂糖橘果,光灿灿诱人。
“这一片200多亩,每亩4000斤,虽有损失,但丰收是不难的!今年还本,明年盈利。”他眯眼微笑着说。
“在这里,种橘子是没问题的,你们下面的那片水田,我的一个老乡也准备来承包。”
他从树底下摘下一串砂糖橘,递给我,“下面的果没有过冻,比较甜。”自己吃着一片说,神情有些傲气。
“到时我们一起把这里搞成规模,带领你们村的人走富裕的道路。”
他快乐地笑着,放肆地笑着,他的快乐牵引着我的快乐,我的心豁然开朗起来。
二月的桂北,大地有些干渴,在企盼着雨水的滋润。远处的越城岭山峦有些光秃,黄黄的一大片,和往年不一样,据说是被人承包后,把原来的杂木砍光,准备种植新的树种;而在近点的水田里,三三两两的人在指指点点,听说也是在商量着承包土地种植砂糖橘的事。
早春,这么多的忙碌人群,这在我家乡是很少有的。我高兴,高兴多年的企盼到来了,但在这种高兴中又隐约感到一丝丝担忧……
这些天,我回到南宁正常上班,满脑是承包土地的事,碰到的人都在聊着砂糖橘、沃柑。
一天,接到一条灌阳籍同事的微信,说今年广西桂北砂糖橘大量滞销,卖不出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心想这件事千万不要波及到“贼老板”。我希望他的橘子早已经卖掉,希望他能在我们那里赚到钱,因为他是我们村里的引路人。他的存在,还满载着我们村里的希望呢!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