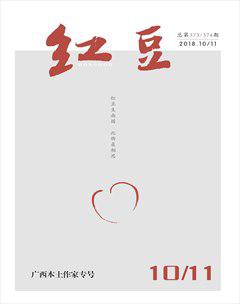老平房和旧邻居
蒙卫东,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当过知青、矿工、教师、军人,现供职于南丹县人大常委会。曾在《广西文学》《红豆》《广西日报》《微型小说选刊》等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数十篇。
手机谋杀了家信
自从手机像很难治好的传染病广泛流行以后,很多人就不再使用家书平信。我们更加远离古人,渐渐淡忘旧诗词中“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和“驿寄梅花,鱼传尺素”所描绘的意境,再也没有期待远方来信的焦虑和收到远方来信的喜悦。我们曾经用心用血写在信里的友情、亲情、相思情、离情、别情、生死情和写在信封上以为会永生不忘的地址,也像慢慢消失在长路尽头的背影,只有在无眠长夜或者黑白梦里,才找到一丝丝痕迹。天亮时,便觉得沉重的回忆穿透了胸膛。
我也是偶然才想起过去在信封上写得最多的地址:河池,南丹大厂矿务局巴力下区四片四栋7号。那是我少年的家。很久以前离开了她,可是我的父母家人,还住在那里,我不会忘记。就算在梦里行走,醉后迷茫和脑子进水的时候,也找得到回家的路。却想不到,几乎记不住她的通信地址了。我已经二十多年不写家书平信。
一个旧时邻居打电话托我帮查找1974年当知青时的资料。来到县档案局,管档案的大姐问我具体家庭地址是哪里。我懵了蛮久,才不很肯定地回答说好像是巴力下区四片四栋7号。档案大姐按这个地址翻开一沓发黄的资料说,对了,就是这里,你的记性真好。我笑了笑。我的笑容一定很苦涩。我居然要认真回想思索很久,才记起家的地址,还被人夸记性好,对此我无语向天,心生伤感。如果不是偶然查阅发黄的档案,也许有一天,我就会把家的通信地址,连同拴在这个地址上的悲欢时光,全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才突然发觉,现在的脑袋里,装了太多QQ、微信,装了太多进退去留,装了太多物欲企盼,装了太多计较攀比,已经很难容得下往事。一路走来,我们到底忘记了多少过去的岁月?还记得初心的模样吗?
长夜无眠。星光下的大地万物沉寂,入眼竟有绵绵苍凉,往事才一点点清晰起来。有的可追,有的再也追悔莫及。我在回忆中来到少年时的家:大厂矿务局巴力下区四片四栋7号。
那是矿区常见的老式平房,土砖灰瓦,每栋住了十家人。每家每月向矿务局交一块五毛錢的房租。
老平房不是鸡毛鸭毛
南方山谷里的大厂矿区,盛产锡铅锌,宋朝的皇帝就知道在这里开矿赚银子了。我在这里长大的时候,住在矿区平房里的国家职工,来自全国各地,但是当时没有发现台湾籍的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举报有几家人讲话的口音有点像台湾的,公安干警一去深查,才查出来他们的老家在福建省厦门那边。当时,大厂矿区少见楼房。手指可以数得来的楼房,最高不过四五层。绝大多数干部职工都住在依山而建的栋栋平房里。每家平房都是直通式的一大一小两间屋。大房二十来平方米,小房十多平方米。有条件的,可以在房前或者房后自搭一间小厨房。没有条件的,就到职工食堂开伙。但是去食堂开伙,费用比自己开伙高。我们都认为当时能去职工食堂吃饭的人,算是比较有钱。实际上,那时就是有钱去食堂开伙的干部职工,大部分都愿意自家搭厨房自己煮吃。大家都想尽量节约一笔钱,去买一块上海牌的手表,或者是一台红灯牌的收音机、一台飞人牌的缝纫机、一台飞鸽牌或者是凤凰牌的单车。虽然有人传说在大厂矿区骑单车可以不要链子,因为矿区的道路大部分除了上坡就是下坡,然而我们都非常羡慕那时就能骑上单车的人。他们骑上单车时的臭模样,现在想起来也还很拉风。直到1985年我才买得一架永久牌单车,天天擦得亮闪闪的,总算为谈恋爱增加了一点物质基础。这架承载过爱情的永久牌单车现在已经不知哪儿去了。
站在高坡上望我们的大厂矿区,就见很多栋平房,横七竖八趴在坡坡岭岭上。有些平房趴卧的地方,地基下曾是无主的坟茔,却也无人去想过,无主的坟茔中是否有古墓。那些建着平房的坡坡岭岭,有的像鸡,有的像鸭,有的像鹅。趴在上面的平房,像它们灰色或者土黄色的鸭毛鸡毛。一条长长的矿水沟从长坡矿那边流下来,穿过鸡毛鸭毛的平房流进了绿荫塘。矿务局就把这些有鸭毛鸡毛的坡坡岭岭划分为长坡区、巴力上区、巴力下区、洪塘区和铜车江区。我们少年打群架的时候,也是以区分边。那时少年打架斗殴一律不用凶器,比的就是拳脚,这才是真男人的勇武,不像现在,动不动就用刀用棍用砖头,就连女的也会用利器伤人,法律意识很淡。话说回来,现在看当时我们的平房,非常狭小拥挤。一家三口人也好,六七口人也罢,都是住在这种一大一小的平房里,最多的一家,还有住十二个人的。我们普遍认为,这种平房比农村的竹篱茅舍强多了,何况农村的竹篱茅舍,还要和猪圈、牛棚、鸡栏、鸭窝紧紧挤在一起。工人和农民,生活不会一样。那时工人阶级的生活比贫下中农好,现在农民的生活比工人雄头多了。以后谁好,我不知道,做梦也想大家更好。
巴力下区四片四栋7号的家,就在这些鸡毛鸭毛中。我站在高坡上,随手就可以指出她的具体位置,但我远离她的时候,就差点忘记她的通信地址。为此我深感羞愧,我对生我养我的家还不够眷恋。如果我的后人忘了她,情有可原,因为他们衣食无忧,除了偶尔去大厂走亲戚或者清明给先人烧香烧纸钱,基本不在大厂生活成长。而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没有什么理由忘记她的通信地址。我们在热爱一个善良的姑娘时,不应该忘记她美丽的衣裳,也不应该忘记她长发上美丽的发夹。
巴力下区四片四栋7号,我在大厂矿区的家,和矿区的老平房一样,其实并不是一片片鸡毛鸭毛,而是一块块巨石。我们游子才是一根羽毛,轻轻的,在南方山谷的风中飘走,从此远离家园旧居。但家如巨石始终压在心头,也许我们会忘记她的衣裳和发夹,却难忘她的温情和悲欢。
老平房的墙壁不隔音
现在大家都喜欢住在宽敞的房子里,伸手就可以开水开电,一般还有二卫二厅,生活方便轻松,但街坊邻里很少串门,互相之间难得交根交底,知肝知肺。家中有困难有意外,也很难及时发现,谁也听不见、看不见邻居的房子里发生的事情,就是有心帮忙,也不知怎么出手。有一次,我父亲突发急病,我不在家。母亲和妹妹手足无措。家人在门口喊了两声,便来了左邻右舍,很快就把我的父亲送到医院。后来我想,如果是一个人住在现在的大房子里,就算病得死了臭了,旁人也难知晓。但在老平房里,绝不会发生这种事。
当然,住在简陋的老平房里,也有一些不方便。那时矿区的自来水还没有接到家里,只在房头有水龙头,两栋或者三栋房子共用一个水龙头。所以,每户人家每天都要到水龙头那里挑水供家用。因为是定时供水,早上一次,晚上一次,人多龙头少,就得按规矩排队,更多的时候,排队挑水的是各家少年。有时候来的水量小,要等很久,等得人心火毛跳,满嘴粗口,翻出别人的祖宗八代。但是二妹一来挑水,个个就装得文明起来,像天天向上的好学生一样,找着由头和二妹说话,问她是否有了亲家,闹得二妹满脸通红。大家就像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赴宴斗鸠山一样哈哈大笑,笑得很老鄙。到1975年以后,自来水逐步接进了各家各户,少年们再也没有在挑水的时候撩二妹的机会了。这一变就是三十多年,二妹早就穿上了别人做的嫁衣。
在老平房里住着的时候,没有卫生间,所以用厕也比较困难。记得我们巴力下区的三片和四片十多栋一百多户人家,共用一排公厕。男厕这边前排后排共有十八个蹲位。女厕有多少蹲位不知道,任我再调皮捣蛋,也不敢进去数。如果进去数,早就被当作大流氓抓起来,在个人历史上留下严重的污点了。从外观看来反正比男的这边少。我想这也是我国当时男多女少的一个佐证,不像邻国朝鲜女多男少。每天早上五点半到七点钟的时候,很多干部职工以及家人都亲自排队上厕所。大家非常自觉,哪怕内急扭得身体像一根天津麻花,都不敢插队。内急但不能立刻解决也是人生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男厕所这边排一行,女厕所那边也排一行。队伍有时排得很长,像两条横过公路的老蛇。二十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物质还不很丰富,买米、买肉、买豆腐、买布、买油、买早餐都要排队,排出了很多生动的故事。虽然排队的时候很多人都感到烦燥,但心中都有美好的期待,所以大家都任劳任怨。现在买东西基本不用排队了,却经常有人去哄抢过路翻车的物资。这种行为比我们少年时把死老鼠扔在别人家门口过分和恶心多了。
有一个夏天的早上,排在女厕所这边的长队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少年男同志。他戴近视眼镜,一边排队,一边看书。那天的阳光刚出来。大家都很奇怪,这个少年看起来很本分,一点不像坏人,难道他小小年纪就有神经病吗?心想只要这个男同志进了女厕所,肯定会被当作大流氓抓起来。想不到他排到女厕所入口时,就转头朝厕所旁边的菜地里大声喊:妈,轮到你了。原来他的娘亲在菜地里劳作。
矿区的老平房里不仅没有卫生间,而且墙壁的隔音性能也很差,不够保密。对此儿童少年觉得无所谓,这也没什么问题,偶然听见隔壁的两公婆斗嘴打趣也蛮好玩的。但是大人们就觉得有所谓了,稍不注意就可能泄密,传出先洗脚还是先亲热之类少儿不宜的趣闻。这种半夜三更才会发生的事情,不知道是隔壁邻居听到的,还是矿区的民兵巡逻队听到的。总的说来,有关少儿不宜的传闻,和我们四片四栋无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厂矿区,每晚都有民兵巡逻队巡逻,所以治安很好,从来无人搞老鼠洞偷矿。但是巡逻的民兵里,有的同志就喜欢把耳朵贴在人家的窗口门边,使劲地听平房里的动静,却理直气壮地说是在侦察是否有敌特或者阶级敌人在搞阴谋诡计。我在长坡矿当井下工人的时候,也作为普通民兵参加过这种夜里巡逻,但从来没有听出什么名堂。我能当民兵并且扛着半自动步枪在矿区巡逻,从本质上证明了我的父亲是冤枉的,和很多冤枉的人一样终于得平反了。不然的话,我不可能当上民兵扛着半自动步枪半夜三更巡逻在矿区的大街小巷里。我庆幸我们生活在一个勇于改正缺点错误的国度里。
苍天瞎眼的时候
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矿区在建设这些平房的时候,每栋房子的这头或者那头,总会留出一块半个篮球场大小的平地。这块平地就是矿区少年儿童游乐的天堂。女孩子们在平地上跳绳、跳田、跳橡皮筋、踢毽子,男孩子们在平地上打玻璃珠打三角板打撩棒。打玻璃珠就是在平地上掏出三个等边三角形的小洞,在任意一个小洞边隔一定距离画一条线,站在线外排队轮流把手中的玻璃球或者小铁球先后弹进三个洞里,中途还可以把别人的珠子弹走,弹得离小洞越远,自己的胜率越大,先入完三个小洞者为胜。不知这种游戏是高尔夫球的雏形还是变态。打三角板就是用香烟盒折叠成三角形,平放在地上,然后另一方就用另一块三角板去掀,掀翻了就赢了。掀翻哪张就赢哪张。没有掀翻,能插入它的下面叫插角,也算赢。如果是压在上面,就输了。赢家可以拥有很多式样的烟盒,有的还是和平鸽、大前门、飞马牌等少见的烟盒,因為矿区的干部职工抽的香烟大都是比较便宜的漓江红灯和转运。三炮台、哈德门和驼牌的香烟盒更稀罕,要二十张以上的漓江和红灯才能换一张,还很难有这种机会。打撩棒又叫打鸡棒,用铲把刮把大小的木棒割出三截,一长两短。长的一尺多,叫母棒。短的五六寸,叫鸡仔,也可以多做几根鸡仔。画一条横线,站在横线这边,手握母棒,把鸡仔往上一抛,然后用母棒奋力击打,打得越远得分越多。另一方就估摸着对手击打鸡棒的距离,尽量去接,接住就得分,接不住就捡起来往回扔。这时对方还可以再用母棒击打,对方又可以继续接,打不中或者接不住,都会丢分。既讲力量,也讲技巧,还能锻炼身体的反应。不过也有一定的小危险,偶尔动作不协调反应慢一点,就有可能被鸡仔打中身体。矿区少年大都有过这种经历,受点小伤也不当一回事。
那时住在老平房里的矿区少年儿童,还会玩很多胡天胡地的游戏乐子,但没有一样跟手机以及电子产品有关。我们打心眼里也不愿意我们的游戏乐子和任何悲剧有关。当时玩得比较野的还有一种游戏叫“新兵捉土匪”。这种游戏不限场地,规则简单,白天晚上都可以玩。人越多越好玩。一两个人或者三四个人当新兵,蒙住双眼,叫声一二三,然后当土匪的男女少年儿童四处跑散,迅速找地方躲藏起来,躲身不及又跑不快的,被新兵捉住就算完蛋了,立刻退出游戏,然后新兵又继续去搜捉剩下的土匪,直到捉完为止。当时我们谁也想不到这种很有趣的游戏会玩出一出悲剧。
那天晚上玩这个游戏的时候,有一个九岁的“小土匪”为躲开“新兵”的搜寻,就藏身在一辆解放牌汽车的后轮阴暗处。想不到这辆白天一动不动的汽车会在晚上突然滑动,就造成了悲剧。这个聪明伶俐但非常不幸的小男孩,就是我的左邻刘叔家的独生儿子。
那段时间刘叔一家伤痛欲绝。刘叔一家忠厚善良,与世无争,好不容易才得一个儿子传宗接代。我在夜里经常听见隔壁“呜呜”的哭声。从那以后,我们没有谁再去玩“新兵捉土匪”的游戏。发生这个悲剧以后,有人悄悄说刘叔家的房子下面可能是很久以前的老坟墓,风水不好,阴魂作祟,不然的话,为什么会有这种意外!但是我们不太相信。老平房下有旧坟是事实,我家的大房地板就莫名奇妙塌陷过,还在塌陷的坑里发现了腐朽的木板和两颗白白的大牙,看不出是豬的还是人的。但填好坑以后我家依然住着。这种情况四栋3号的卢家也发生过,但刘叔家的地板从来没有这种现象。然而刘叔相信了这种说法,就千方百计找人换房子,还是搬到四片六栋去了。和刘叔家换房子的是顾家,住不到两年就搬走了,说有时半夜三更,好像听到伤心的哭泣。然而刘叔家和顾家换房子以后,不但没有换来好运,反而祸事连发。先是刘叔突发重病住院,然后是刘大姐刷新房时闪了腰,然后是刘老三,一个可爱的邻家女,摔折了条胳膊,接着又因烤火打瞌睡烧伤了腿。好好的一家人,无端连受创伤。直到今天,在为刘叔一家叹惜的时候,老邻居们都想不通这是为什么。尽管命途多舛,生活悲苦,但刘叔一家,依然坚强挺住,相逢时,照常笑得很善良真诚。
不做“新兵捉土匪”的游戏以后,我们的野性更大,开始迷上了捉竹骝。竹骝就是竹鼠,现在有的人拿来饲养赚钱,在那时,还是完全环保生态的野味,很多人虽然很想吃它却无法捉住它。竹骝也是一种狡猾凶猛的小动物,如果被它的四颗黄板牙咬住,传说雷公不叫它不松口。那四颗黄板牙可以非常轻松地咬碎利刃都难对付的竹子和芭芒的老根。如果咬住人,后果很严重。
带我们去捉竹骝的就是3号邻居卢老大。卢老大一家也是与世无争的人家,只祈愿能平平安安过日子。但是老天好像有意和好人家过不去,经常把乱七八糟的苦难强加到好人的头上。强加给卢家的灾祸,格外恶毒,居然让卢叔患上了麻风。
麻风病在古代的时候叫疠病,会传染给别人。得了这种病虽然不容易挂掉,但是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治疗,面部和全身皮肤就会出现大量的斑疹和斑块,呈出浅红色或者暗红色,损害处毛发脱落,到了晚期,会五官曲扭,面部歪斜,四肢蜷曲,肢端残废,很可怕。古代里一发现这种病,整个寨子的人都会被活活烧死,或者被撵到人迹罕至、与世隔绝的地方自生自灭。新中国以后必须坚决对患者隔离治疗。现在我国已经基本消灭了麻风病。卢叔不幸染病之后,马上被送到建在南丹县八圩乡偏远山沟里的麻风医院里医治,三年多以后才回来。 因为治疗及时,卢叔的面容没有什么异常,但心理上留下了沉重的阴影。矿务局给他安排了在矿井下看水泵的工作,那是一个人就可以干好的寂寞工种。下班以后,他很少出门,家人也很少出门,都紧紧地把自己锁在一大一小的平房里。我们做各种游戏的时候,基本没有卢家老大老二两个少年的身影,只是发现,天气好的星期日,卢叔就带着两个儿子出门,黄昏归来时,就见他们拴在锄头把上的帆布口袋里有活物在挣扎,里面装的就是竹骝。
我们也很想去学习捉竹骝,但是父母们早就严厉禁止我们和卢家少年来往,都怕被传染上可怕的麻风病。虽然医院的医生早就说卢家没有问题了,人们还是担心。从古到今遗留下来对麻风病的畏惧,很难完全消除。然而,我们还是很难抵挡竹骝的诱惑。卢家烹制竹骝肉的时候,那种奇异的香味就一阵阵钻进我们的鼻子里,香味和猪肉鱼肉的不同,比牛肉羊肉更好闻。在当时一星期才有一两餐见荤腥的年代里,如果经常有香喷喷的竹骝肉解馋就太好了,何况竹骝不要肉票,也不用排长队,只要你会抓竹骝,可是我们没有这种技能。很想去向卢家两兄弟学习,又怕惹上麻风病。
有一天,卢家来了两个大人一个小孩,进门时还提了很多的礼物。这三个人不但在卢家坐了很久,居然还和卢家一起吃晚饭。胆子太大了,难道他们不怕被传染吗!我们很惊奇,就在卢家的门口溜来溜去,想看清楚正常的人和曾经患过麻风病的人交往以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只看见房子里的大人还在碰杯喝酒,卢家的老大老二和客人的孩子在说话。后来就见这个孩子和大人经常来卢家。有时是一起来,有时是分别来。我们才知道,这个小孩在野外玩耍时掉进山塘里,被正在山上挖竹骝的卢家父子看见,救了他,然后两家就做了干亲,也不见这家人身体有什么异常。于是我们也慢慢接近了卢家少年,开始是说几句话,然后是共同游戏,然后就发展到一起练习摔跤,一起到野外去钓螃蟹捉青蛙,一起去学校上课。大人们开始还说几句,但看见有客人经常去他家,也就不多说了,因为那个客人还是矿务局的一个小领导。领导都不怕传染,一般人还有必要怕吗?终于有一天,卢家少年同意带我们去捉竹骝了。
暑假里,走在满眼翠绿的山路上,我们很开心。卢家少年平时郁郁寡欢的脸上也呈现出微笑。老二扛着锄头,锄头把上拴着准备装竹骝的帆布口袋。老大一边走,一边告诉我们,竹骝很刁,一般都挖了前洞后洞,前洞是正常进出,后洞口是准备逃跑,像古代的奸臣贪官一样早就留了逃跑的后路。所以要捉住竹骝,必须首先搞清楚它的两个洞口,然后根据地形再挖开它的洞,也可以用水灌,也可以用火烟熏,把竹骝逼出来。竹骝长年生活在地下,见光了就成睁眼瞎,白天捉它没有什么可怕的,手快脚快不让它咬住就成了。卢老大带我们走到一个长了很多芭芒的山坡上,说这个坡上一定有竹骝。我们只看见满坡的芭芒草,绿意葱葱,看不出别的名堂。卢老大在芭芒蔸下扒见了两个洞口,说这是新的洞,一定有竹骝了,就指挥我们填死一个洞口,在另一个洞口挖起来。我们按照他划定的线路挖了一条沟,三米多长,弯弯曲曲的,果然就挖到了一只两斤多的大竹骝。我们很佩服,也很奇怪,他怎么就看得出深藏地下的竹骝洞穴的走向呢!
卢老大指着挖倒在洞口两边的绿芭芒,神秘地告诉我们,你们认真看看这些芭芒,因为根部被竹骝咬断了,吃掉了,表面上看还是绿的活的,其实已经开始发蔫,要死了。这说明竹骝刚开始在下面做窝。如果等到上面的芭芒蔫了死了再来挖,可能竹骝早就搬家了。我们把挖倒的芭芒和还生长着芭芒进行了认真比较,好久才看得出来,被竹骝咬烂根系的芭芒稍微有一点蔫,差别非常小,但就是这点细小的差别,却逃不过卢老大的眼睛,这就是眼力、是水平、是能力、是经验了。就算得知了捉竹骝关键秘密,没有一定的经历,也不可能捉到竹骝。很多事情就是这样,窍门大家都明白,但有的人做得风生水起,收获丰富,有的人一事无成,关键还在怎样去经历。
现在也有好邻居
我的老平房的旧邻长辈们,很多已经作古,还健在的也是白发苍苍,老树枯皮,步履蹒跚,说起来就生出悠悠伤感,总恨时光无情。卢家的老大老二,也不再是捉竹骝的少年,和我一样,还有旧邻的同辈们,都已经五六十岁了。相逢诉说往事,感叹命运无常,还讲到如果刘老五不出事,以他的聪慧,肯定有大出息,最起码在书法上非同一般,太可惜了。可无论叹息还是追忆,谁也不能改变所有故事的结局。虽然曾经有缘在一起做过近邻,彼此相处如亲,依依不舍,最终还是星散云去,各奔东西。
现在,无论我们在哪里生活,也还是有邻居的。我现在住的小区,已经不是旧时的平房。现在的小区基本不建平房,都是楼房,或者是从地到天,或者是公寓楼。进进出出的人们匆匆忙忙的。我们小区的邻居都很好,我的老母亲就经常得到邻居们的关照,非常感谢他们。但是我们小区的少年们,人人都忙着读书学习,从幼儿园开始,就要练习写字、跳舞、学外语、学习弹钢琴了,很少见他们一起在大院里玩游戏。我们小时玩的游戏,他们根本不去玩,也基本不知道。他们彼此之间很少来往。我想现在大人都很少串门了,小孩们又怎么亲热得起来呢?我甚至连一些邻居的名字都很难准确地喊出来,在院子里或者大街上相遇,感到面熟,便哼哼哈哈笑着点头致意,过后却想这个兄弟住在哪一家。我们住房的空间越来越大,却越来越自我封闭,邻里之间交往的空间越来越小了。
我不知道其他小区是不是这样,更不知道在很多人都向往的大城市里各类小区的情况,他们的左邻右舍彼此相识吗?互相来往吗?有事会互相帮忙吗?
站在大厂矿区的高处,我们依然还看得见很多趴在坡岭上的老平房,我依然指认得出我家所在的四片四栋,走进平房群中,依然还熟悉拐来拐去的道路。然而物是人非,抚摸平房的老墙很冰凉。前栋后栋之间,两头都砌了水泥砖墙,装上铁门,一到晚上就紧紧锁住,防止小偷强盗。房头的平地也被扩展出来的屋子占光了,也不见玩耍的少年们。老住户们有的搬走了,不再回来,有的跟儿女住高楼了,把房子租给了外来人,还住在那里的老住户和租房子的外来人,很难亲热,总有一圈竹篱笆围住各自的心,像围住自留地一样,防鸡防鸭防牛羊进去吃自家的青菜、萝卜、黄瓜,过年再也不会在一起轮流打糍粑了。过去已成回忆,回忆中就有很多断片空白,想不起我们在那里面经历了什么,而且断片和空白越来越多,故旧邻里越来越少,再相逢时,都觉得有陌生的感伤。
都说恩情易断,仇恨难消,歡乐易淡,苦难久长。如果这样,我宁愿把我在老平房里度过的时光,无论悲也好、喜也好,忧也好、乐也好,都当成另类的苦难和仇恨,永远铭记,不再出现回忆的断片和空白。
责任编辑 蓝雅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