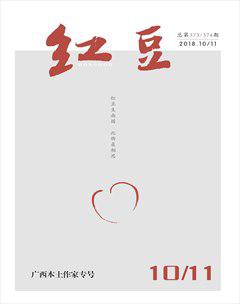棉花尾巴(短篇小说)
陆荣斌,1980年生,广西大化人,广西作家协会会员,曾在《广西文学》《红豆》《北方文学》《民族文学》《滇池》《延河》等期刊发表小说。现居大化。
1
阳光把张北的影子投射在满爷家门前的青石台阶上,他清晰暗黑的影子如潜行的蛇,攀上一级又一级台阶,甚至越过了横亘在门口的青石门槛,与纺车的影子部分重叠在了一起。娅满仰起脸,摇动纺车的速度慢了下来。张北看到一张老人的脸,皱纹密布,干枯如秋后的丝瓜,却倍感亲切。娅满对眼前这个陌生人的突然造访似乎并不诧异,只是微微笑,像对着疼爱的孙子笑。然而他不是她的孙子,他得表现出一个陌生人上别人家门时应有的礼貌:“奶奶,您好!” 娅满还是不说话,只是点头微笑。张北问:“奶奶,您这是在纺线哪? ”娅满停止摇动纺车,摇摇手,嘴里叽里咕噜说着他听不懂的方言。
张北环顾屋内,想看看是否还有别的人。这时,他被满爷吓了一跳。在离门最远的角落,有一口看上去有些年岁的漆黑寿方敞开着,寿方盖搁置在旁边。他隐约看见里面仰躺着一个人,心里咯噔了一下,心想这户人家应该是刚有人过世,顿生恐惧,双脚下意识地向后移动。在他转身就要离开的刹那,满爷的声音便急匆匆地朝他赶来:“谁?!”那是刚睡醒的人才会发出的声音,像从某个遥远的深处传来。张北忍不住回过头去寻找声音的来源,发现寿方里躺着的那个人现在坐起来了,两手正扶在寿方边沿,眯着惺忪的睡眼望着他。满爷这一看,张北再次被吓着了,顿时像只受惊的小鹿噔噔噔飞奔下门前的青石台阶。身后,娅满像在安慰自家孙子似的叫道:“傻孩子,怕什么咯?” 张北听不懂娅满的壮话,也没听清,只顾着快点逃离,差一点就跌倒在青石台阶下。
张北疾走在七百弄弄籁屯的青石板小巷中,他的慌张与落魄被迎面而来的德春撞见了。身着保安制服的德春警惕性顿时被提高了起来,心想大白天的,这个年轻人慌里慌张的干吗,就叫住了张北。此时,张北已经走过德春身旁,突然停下脚步。他往德春的背后不安地張望了一眼,确定安全后才说出自己刚才的所见。德春顿时哈哈大笑起来,说:“这有什么奇怪的,在我们这儿,有哪一家没有一两口寿方的?哦,对了,我们不叫棺材,叫寿方。”张北问:“为什么?”德春说:“这是我们的风俗,给老人预留的呗。不过,别人家的寿方都闲置在阁楼上或隐蔽的角落里,可满爷家的寿方却是个例外。他家有两口寿方,一口在阁楼上,那是娅满的;一口在堂屋的角落里,那是他的。你看到坐在寿方里的老人,准是满爷,九十一岁的满爷,整天嚷着活得不耐烦的满爷。”
原来,在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壮族家中如有老者,一般都备有用木棉、松树、杉树或椿木等大块木板拼合制成的棺材,平时用来存储谷物。这是晚辈们对老人尊敬和爱戴的信物,也是晚辈们对老人健康长寿的一种祈祷和祝愿。如今,大化许多壮族家中已渐渐摈弃了这种备棺习俗,但弄籁屯的许多人家还是保留着。
听罢德春的话,张北松了一口气,可还是有些疑惑,那个叫满爷的老人为什么躺到棺材里去?德春说:“在我们这,给老人预留的寿方要么空着,要么暂时当米仓用,像满爷这么用来当床睡的,还真没有过,天晓得他午睡时为什么不到床上去偏爱躺到寿方里。”张北“哦”了一声,也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好奇。当前,他最关心的不是一个老人为什么午睡时喜欢躺在棺材里而不是床上,他最关心的是,还有没有一个让他长住的地方。
张北是个网络作家,有一次,他跟随南宁一群热心公益的朋友到大化的一个教学点开展爱心公益活动,在感叹那个地方贫穷落后面貌的同时,也不禁赞叹起那个地方美丽的生态环境来。张北对爱心公益活动的领队说:“这地方真好!对我们这些城里人而言,简直就是一个世外桃源。要是这里通网络,我真想带上我的笔记本电脑来这里写作。”领队笑了笑,说:“这就算世外桃源了?你没来过你不知道,这地方不仅没网络,还很缺水。把你丢在这地方,你还有心思写作?你还是先想想怎么生存下去吧。”张北自嘲地笑了笑。领队又说:“你要真想来山里写作,我介绍一个地方给你去。”张北问:“哪里?”“大化七百弄弄籁屯,人称‘世外桃源,那里已开发民宿旅游了,你去那里肯定能安心写作。”
张北把领队的话记在了心上。刚进入夏天的时候,他沿着从山外逶迤而来的水泥路出现在弄籁屯东面山坳口,看到了参差坐落在北边山脚下红砖黛瓦的半楼式干栏建筑和一座座雪白的平顶房,还有南边山脚下流淌着的一段河流,以及河流边上的景区接待中心。整个屯落被四周的青山紧紧围拢着,真是个安静的所在。他想,自己选择来这里避暑写作看来是对了。
景区接待中心是一栋四层的仿全楼式干栏建筑。弄籁屯被开发成度假山庄后,保留了原有的砖瓦房,通过装修其内部,发展民宿旅游,同时在屯子边上建起雪白整齐的二层小楼让村民们居住。可是,在这个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屯落里,也就只有不到一半的人家常住在小楼房,另一半多的人家因为地处偏远,早已在县城里买地建房了,旅游开发公司帮建起来的小楼房只是他们偶尔回故乡的落脚点。而满爷,拒绝搬出自己的老房,搬到小楼房里去。
张北来到景区接待中心,穿着无领破胸对襟衣的女子很不客气地对他说,民宿已经全部住满人了,接待中心倒是还有几间客房,不过你就是住上十天半月也没用,住在老瓦房里的游客最快的也得到夏天快结束时才离开。
张北想,在弄籁屯长住的愿望看来是要落空了。他找到德春,想在德春家的新房里住一段时间,德春不答应。张北说:“我付给你房租就是了呗!”德春说:“旅游公司规定,屯里的居民不能私自留宿游客。我看哪,你就在接待中心住几天,玩够了就回去。”张北说:“我不是来玩的。”“你不是来玩的你来干什么?”德春的警惕性一下子又提高了起来。“我——”张北刚要说,想想还是算了,说了德春也未必让他住进他家里。德春说:“你倒是说啊!你不说清楚就别想走。”德春一下子揪住了张北的衣襟。张北挣脱掉德春的手,没好气地说:“说了你也不懂。”德春不高兴了:“哟呵,你这小子,你不说清楚我还真不能放过你。”张北被德春缠得没办法,只好说:“我想在这住一段时间,好好写小说。”“写小说?!”德春像遇到知己一样高兴。张北说:“对,写小说。你也喜欢小说?”德春有些不好意思地嘿嘿笑了两声:“对,喜欢看点。”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个智能手机,摁亮屏幕刷刷两下就给张北看:“你是写这种小说吗?”张北瞄了一下后摇摇头,说:“我不写悬疑推理,我只写奇幻异世类的。”德春说:“哦,那些我也喜欢看,我还喜欢看惊悚恐怖、科幻异能类的。反正一天到晚我都是在这山弄里巡逻,有的是时间,就喜欢看小说来打发。”
突然,德春瞄着张北狡黠地笑了一下,说:“你要是答应让我当你小说的第一个读者并不用付费,我可以帮你去问问满爷,他或许会让你住进他家里。他家在我们屯是个例外。”
2
初次见面,睡在寿方里的满爷着实把张北吓得不轻,但在目前住房紧缺的情况下,满爷要是答应让他住下来,他求之不得。他答应了德春的要求,跟着德春又来到了满爷家。在满爷家门前,满爷正扛着绑成一捆的两截枯竹走过来。德春忙迎上前去,想从满爷的肩膀上接过枯竹,却被满爷拒绝了。德春知趣地闪过一边,和张北亦步亦趋跟在满爷的身后,登上门前的青石台阶。张北看到了满爷身后垂着的雪白的棉花条。娅满还在门边上纺线,看到张北回来,脸上就漾开了涟漪一样的笑。张北也报之以微笑,掏出手机蹲下身来对着娅满拍了几张相片,还给她看。娅满看着手机中的自己,那笑容已不只是涟漪而是浪花了,笑声也如浪涛声一样悦耳。
满爷把枯竹扛到厨房去,德春也跟着进去,就东拉西扯地跟他聊起来。满爷有一句没一句地应着。两人聊着聊着,就聊到了张北想借宿的事。满爷说:“到别处去!我家不欢迎陌生人。”满爷家是三间红砖瓦房,中间堂屋,连着堂屋后门就是伙房。他和娅满睡东厢房,两个女儿出嫁后,西厢房就一直闲置着。满爷又说:“再说我们都是老人家了,跟着我们住一块,只怕他不习惯。”
张北走到堂屋后门,看着德春跟满爷在厨房里聊着,一句也听不懂。张北问:“怎么样?答应没有?”德春不耐烦了,说:“哪有那么容易?你去外面等一下,这事包在我身上。”张北知趣地回到堂屋,蹲在娅满的旁边看着她一手摇动纺车,一手捏着棉花条。那棉花条像蚕吐丝一样,被抽出的细细线条紧紧缠绕在纺轮上。娅满安静地坐着,悠然地摇着,不疾不徐,不时地转过头来微笑着看张北一眼,还对着厨房里正在说话的两人插上一两句。张北看着娅满抽到第三根棉花條的时候,听见德春叫道:“小张,进来!”张北忙不迭地进去,问:“答应了?”德春说:“答应了,但你得答应满爷一个条件。”张北说:“只要让我住下,别说一个,三个都行!”德春说:“满爷说了,他不收你的房租,但要认你做干孙子。”张北想,这样的条件对他来说不是个条件,可以接受。
3
在南宁,张北习惯昼伏夜出,每当华灯初上才开始一天的写作,到人们开始入睡的时候,才散步到中山路去吃夜宵,回来再继续写作到凌晨三四点。在弄籁,在夜里写作,对他来说,很不适应。他有些怀疑,他来到的地方不是一个被开发成风景区的山寨,而是一个原生态的山寨。那种无法抗拒的静谧会时时刻刻如丝如缕地浸透到他的骨髓里,让他觉得万分安逸,一心只想蜷缩到被窝里睡大觉。虽然已进入夏天,可夜里还是很凉。他蜷缩在单薄的被窝里,听着满爷的絮絮叨叨在空旷的老房里回荡。因为听不懂,再加上是在夜里,那绵延不绝、像是在自言自语的絮叨声也就显得不烦人,习惯了城市噪音的张北依然可以安然地写作或睡去。而每天清晨,他会在满爷的叫声中醒来。满爷主要是叫张北起床吃早餐,尽管张北多次跟满爷说不要叫他起床了,他睡到自然醒会自己找吃的,满爷还是一如既往准时准点地叫。张北也没办法,他得接受这份好意,虽然他起床后不吃两位老人煮的玉米粥,但是他也得起床,开始一天的写作。久而久之,张北发现,满爷经常一大早就出门去。出门去的满爷,腰上绑着一条用布条搓成的绳子,绳子靠近脊椎骨的位置,还悬着一条拇指粗的雪白棉花条,一直垂到他的膝弯处。
张北很好奇,满爷为什么会在屁股后头悬着棉花条?他问过娅满,可当他的话一出口,他才恍然记起,娅满是不会说普通话也听不懂普通话的。晚上,他拿着当天写好的小说去给德春看,顺便问起满爷在屁股后头绑着棉花条的事,德春淡然一笑,说:“满爷就那样,像一个任性的孩子,我们早就见怪不怪了。”
德春继而说道:“二十多年前,屯里来了一个城里的照相师傅,住在满爷家,整天除了给我们屯里的人们照相,就是让满爷带着他到暗河里去拍照,到山上那些溶洞去拍奇形怪状的钟乳石。就在满爷带着照相师傅爬到东山顶上去看那个清朝时期的瞭望台,顺便拍弄籁屯全景的时候,照相师傅不小心失足从山顶上摔了下去。面对照相师傅的家人,年近七十的满爷无助地跪了下去,诉说着他的悲伤和歉疚。照相师傅的家人似乎也沉浸在极度的悲伤中,全然不理会跪在面前的满爷。村民们把照相师傅抬出弄籁去到村部边上的公路上车,满爷始终像个做错事的孩子,跟在照相师傅家人的身后,一遍又一遍地诉说,从最初的歇斯底里到后来的喃喃自语,照相师傅的家人都没有正眼看过满爷一眼。屯里的很多人都很为满爷感到不值,说那个城里人又不是满爷推下去的,再说,那个城里人到东山顶上去,也不是满爷主动带去的,是他让满爷带去的。在那之后,满爷经常喃喃自语,诉说着东山顶上的事故。直到有一天,满爷向娅满要三条棉花条缀连在一起,悬挂在屁股后头上山去后,娅满意识到,满爷可能是疯了。一连几天,满爷都没有下山来,大人们就山里山外、山上山下问了个遍、寻了个遍,也没见到满爷的踪影。直到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满爷才像个邋遢鬼一样出现在娅满面前。那个夏天,满爷并没有走远,一直跟在一群猴子的后面,游走在弄籁屯四周的山林中,渴望有朝一日变成一只猴子。”
“变成一只猴子?!”张北很惊讶。
“是的,变成一只猴子!” 德春说,“我们都认为,满爷是疯了,才相信屯里口口相传的一个常用来吓唬小孩的惯用语。”
“什么惯用语?”
“在弄籁屯,人们小的时候都因为调皮捣蛋被奶奶们吓唬说再不听话,就在屁股后头粘上棉花条赶上山去与猴子为伍。”
张北“哦”了一声,德春又说:“很多年后,我听说,如果照相师傅听满爷的话,也不至于摔下山崖。那天在东山顶上,满爷就站在他的身旁,不停地提醒他不要太靠近悬崖边。可是他为了站到更好的位置拍照,还是向前挪了挪,一不小心就失足了。满爷在惊惧之中,发现他悬挂在崖上的那株榕树上,就试图循着崖壁攀爬下去,可是没办到。满爷又试图在山顶上找些粗壮的藤蔓伸下去,让他抓住,可是他还没等到满爷找到藤蔓就已经支持不住了。满爷一直认为,对于那次事故,他是负有主要责任的。”
“屁股后头挂棉花条上山去就能变成一只猴子啦?这满爷真是疯了。”张北说。
“可不是!村民们说,可能是当时照相师傅家人不理会满爷的倾诉,使得满爷心怀抑郁,才整天念叨着,他要是像猴子那么灵活矫健,就可以快速地从山顶攀岩而下,救下卡在鹰嘴岩榕树上的那个城里人。”德春说,“没有人能确定满爷是否真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他再怎么拖着棉花尾巴上山去跟那几只猴子混在一起,也不可能变成它们中的一员。后来,他渐渐失去了在屁股后头悬挂棉花条上山的兴趣。”
4
满爷想变成一只猴子的渴望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2009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山上的草木静止不动,鸟儿也不知隐遁在何处,人们都待在自家的屋里,村支书带着乡长和几个外乡人来到了弄籁屯。留守在家的十几个老人在村支书的吆喝下,陆陆续续地聚拢到了晒坪边上的大榕树下,听着乡长像树上的知了聒噪了一个下午。老人们在村支书、乡长一行离开后,纷纷回到家里,拿起无线电话,把乡长的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传到了散落在山外各地的弄籁人耳朵里:弄籁屯就要开发成风景区了。
老人们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和感慨,想不到偏远闭塞的弄籁屯竟也有被外界青睐的时候,更想不到的是,带来这一切的,竟是一张相片。当乡长从其中一个外乡人手里接过那张相片,跟老人们展望弄籁屯的未来蓝图时,老人们都看出来了,照片里就是他们世代居住的弄籁屯。他们基本上都能从照片上认出各自房子的位置,只是,没有看见屯里仅有的几间平房。乡长说,当然看不见了,这是很多年前拍的照片。老人们似乎已想不起谁在很多年前就来给弄籁屯拍照,而且拍得那么美,让他们一看见照片就懊悔,自己在弄籁屯呆了一辈子也没发觉弄籁屯是那么美,像图画一样。只有满爷,注意到了相片右下角标注的一个名字,想起了那个从鹰嘴岩上坠落的人。那张照片,就是那个照相师傅拍的。乡长说,要是李总早发现这张照片,弄籁早就变模样了,弄籁的青壮年劳力也用不着背井离乡到处打工了。满爷想起照相师傅的时候,心里不知是应该怀念,还是应该埋怨。那天晚上,他比平时多喝了一碗酒,话就像南山脚下的暗河一样滔滔不绝,又像山里的风一样,这里刮一阵,那里刮一阵,全无章法。
没过几日,散落各地的弄籁屯青壮年劳力们陆续回到了屯里,村支书、乡长又带着几个外乡人来到了弄籁屯。他们谈了整整五天,终于就开发弄籁屯成为民宿旅游景点达成了协议。轰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开始在弄籁屯此起彼伏。水泥路,一米米地铺向山外;登向东山顶上瞭望台的石阶,一级级地向山顶盘绕而去;屯子前面的田地里,盖起了一栋栋小楼房;南山脚下河流流出的巨大溶洞里,渐渐被改造成一个巨大的大厅。弄籁屯平静的生活被打破了,满爷变得烦躁起来,他无法忍受一个被改造了的弄籁,更无法忍受在余生里被扰乱的生活。在这一派繁忙的景象中,满爷闷声不响,从家里那个樟木衣柜抽屉里,又拿出娅满存留的棉花条,绑扎在腰间,奔上了后山。在满爷的潜意识里,与其整天被人们叨扰着,不如上山去与猴子为伍。
人们都忙于建设一个全新的弄籁,再加上满爷不像从前那样一去就是一个夏天,没有人注意到他怪异的举止。即使满爷站在一个显眼的地方远远地看人们修路,人们也没有去注意他,注意他那冷酷的表情和哀怨的眼神,还有那条垂在他屁股后头的棉花条。或许,人们是注意到了,只是假装没看见,就像早已看惯了路过身边的山羊或攀援于树枝上的猴子。
人们对一头山羊的重视,是在准备宰杀它的时候。同样,人们重视满爷的时候,是在他们需要满爷搬出老房子的时候。那时候,除了满爷家,弄籁屯其他人家都从老房子里搬进了崭新的小楼房,老房子的内部被装修得和酒店一样漂亮。就剩下满爷家最后一家没有装修了,人们想动员满爷和娅满搬进分给他们的小楼房,可是满爷总躲着,不给人们动员的机会。他就那样一如既往地拖着长长的棉花尾巴,走在人们的视线之外。直到有一天,有人说,你们就不要费尽心机去动员满爷了,就让时间去动员他吧。人们一开始没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待领会过来,也就放弃了动员满爷搬出老房的念头。这时候,人们开始动员娅满。人们动员娅满,不是让她动员满爷搬出老房子。在家里,满爷说的話才算话,从年轻到年老,一直都这样。指望她去动员满爷,基本是浪费时间。人们动员娅满做的事是,让她重新拿出她的纺车,每天坐到家门口纺线。
娅满已经很久没有纺线了,她的纺车就闲置在樟木衣柜上。人们把她的纺车拿下来,对她说,你每天没事时就纺纺线,尤其是有游客登门的时候。娅满还摇得动纺车、捻得住棉花条,就照做,反正每天闲着也是闲着。渐渐地,她发现,那些从山外来的人,路过家门前,看见她在纺线,就很好奇地来到跟前,看她从一根根棉花条中抽出一条细长细长的线条,绕成一个又一个鼓鼓的纺轮。有的人觉得很神奇,就要求也动手纺线。娅满没有反对,让过一边,笑呵呵得看着他们把一根根棉花条扯断时无计可施自叹不如的样子。经常的,也有一个人,甚至是三五个人,端着照相机对着娅满咔嚓咔嚓地拍,或者是或蹲或站在娅满的身旁,让同伴帮忙照相。每每这时候,娅满都旁若无人、自顾自地纺线。日积月累,娅满身边就堆积着一堆缠满棉线的纺轮,旅游公司的人就来把那些纺轮收购起来,还额外给她工资——娅满以八十几岁高龄整天坐在门口纺线,不仅为弄籁度假山庄制作壮布提供源源不断的棉线,还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人文景观。满爷知道这事后,把旅游公司额外给的工资还回去,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钱就是废纸。满爷说的是实话,他和娅满每月不仅都能领到政府的高龄补贴,还领到旅游公司给的生活补助。对于习惯粗茶淡饭的两人来说,已足够应付生活了。最令满爷感到不快的是,度假山庄的人竟然把娅满当作赚钱的工具。为此,满爷不让娅满再纺线,还数落了娅满好些天。娅满对满爷从来都是言听计从,可满爷还是不放心,就整天陪着娅满呆坐着,有时候两人一整天不说一句话,有时候又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闲得无聊透顶时,满爷不知开的哪个脑洞,叫德春几个年轻人帮把阁楼上的一口寿方抬到堂屋的角落里。德春几个年轻人正纳闷满爷叫把寿方抬下来,是不是预感到自己时日无多了,正要问,满爷却抬脚迈进去,很享受似的躺了下去,说:“这人啊,活得太久了也是一件挺没意思的事。”继而伸出手来对德春几个年轻人挥了挥手:“没你们的事了,该干吗干吗去吧。”
满爷没有德春几个年轻人猜想的那样时日无多,他活过了九十岁。娅满,见满爷经常绑扎棉花条上山去,或是躺在寿方里午休,很少和自己聊天,覺得挺无聊,就又拿出纺车来纺线。满爷也没说什么,只是留心着不让人踏进他的家门。有一次,他躺在寿方里正要午休,突然有游人有说有笑地走上石阶去和娅满这个老寿星合影留念,满爷一骨碌从寿方里爬起来,没好气地呵斥了一声:干什么呢?!把那几个游人吓得魂飞魄散。
自那以后,鲜有游客上门去和娅满打招呼,也少有游客再去和她合影。
5
张北每天除了呆在满爷家里写作,到德春那里上传他新写的小说,还经常到屯里四处走走,看看游人们在操场上举行碰蛋活动。这碰蛋活动本来是当地壮族青年男女在每年的“三月三”歌圩上传情的一种方式,如今成了一个旅游活动项目。张北偶尔也拿着用红色染料涂红的熟鸡鸭蛋跟其他游人互相碰击,被碰破蛋成为输家的时候,他把破蛋交给赢家,却无法唱首赞美的山歌给赢家,只好唱一两句流行歌曲搪塞过去。
张北去得最多的就是东山顶上的观光亭,和南山脚下有河水流出的那个巨大溶洞。去观光亭,他主要是去听听每天坐在亭子里的三位大叔和三位大妈对唱山歌。他们是弄籁屯唱山歌的好手,弄籁屯开发成旅游景点后,他们常常对唱山歌给游人们听。张北不想听的时候,就眺望眼前那些挨挨挤挤、密密麻麻的峰丛洼地。去溶洞,则是为了游泳锻炼。经常的,张北会看见满爷,静静地站立在某个地方,冷冷地朝着他看过来。那时候,张北说不清楚,满爷是在盯着他看,还是盯着他周围的游客。有几次,张北走过去和满爷打招呼,满爷却像不认识他似的,看都不看他,就更别说应答了。张北很纳闷,满爷在家里和在外面对待自己,简直就是天壤之别。知道张北在满爷家住的人,就问张北,那老头子好古怪啊,你住在他家不害怕吗?张北反问,那么和善的一位老人,有什么好害怕的?
张北说的是真话。没错,他第一次踏进满爷家门的时候,是被满爷结结实实地吓了一回,那真是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住进满爷家后,他发现,满爷除了喜欢拖一条棉花尾巴上山去,以及经常在夜里没头没脑地自言自语外,跟一个正常的老人没有啥分别。住在满爷家,张北感受到的不是害怕,而是温暖,是那种被宠爱后心底里不由生出的汩汩暖流。那股暖流,就像南山脚下那段裸露的暗河,表面上看知道来处,也知道去处,其实真要追根溯源,也难说得清楚。在张北不喜欢吃玉米粥早餐的时候,满爷会像哄三岁的小孩一样,告诉他吃玉米粥的好处,硬是让从来没吃过玉米粥的张北迷恋上了玉米粥。渐渐地,张北心甘情愿地和满爷娅满一日三餐都吃着玉米粥和自家种的绿色无公害蔬菜,有时还能吃到满爷从山上采摘来的野菜。也因此,张北改掉了在城里养成的饮食不规律的毛病。重要的是,张北感受到了他不曾感受到的来自祖辈的关爱。
在满爷家住久以后,张北恍然觉得满爷娅满就是他的爷爷奶奶,而他就是他们的孙子。可不是,张北要给满爷生活费,还有住宿费,满爷一概拒绝。满爷说,我和你奶奶归西后,这个房子就送给你了,交什么房租?!提了几回,满爷都不收,还一直说要把房子送给他。
张北就把这事告诉德春,德春说:“你是不了解满爷的心思。满爷只有两个女儿,本打算让其中一个女儿招个女婿上门,来供奉自家香火,继承自家财产,让他们生育的子女随自家姓氏。不曾想,两个喜唱山歌的女儿偏偏在对唱山歌时看上了两个都是家中独子的小伙子。没办法,满爷娅满成了五保户。特别是弄籁屯开发成旅游景点后,他们想把满爷的房子改造成民宿,满爷坚决不同意。如今,他是想待他两老归西后,宁愿把那三间老房子赠送给你,也不愿把房子让给旅游公司。”
张北听见德春这样说,心里顿时涌起一股暖流。自此,他再也不跟满爷提起房租的事,真就把满爷家当成自家一样,把自己当成了满爷家的一员,也敢在聊天时斗胆问满爷,为什么总是喜欢拖着条棉花尾巴上山去,又为什么总是在夜里自言自语。面对张北的提问,满爷从来就没有给予过回应,倒露出一副茫然无辜的表情,好像很奇怪张北为什么会问这样的问题,好像拖着条棉花尾巴上山以及半夜里自言自语不是他经常干的事那样。
6
眼看着夏天就要走远,秋风开始吹过弄籁的草木间,娅满看看煮晚饭时间到了,一向按时下山的满爷还没见回到家,就来到山脚下,朝山上喊着满爷的名字。没有任何回应,那茂密的树林把娅满所有的叫喊声都收了起来。
后来,德春和张北在满爷家后面的山腰上,发现了满爷。他躺倒在一棵香樟树下,像是已经睡熟的样子。在周围的树木上,三五只猴子静静地看着满爷,见到张北和德春到来,就都一哄而散了。
看着攀援树枝而去的猴子,德春幽幽地说:“从此以后,满爷再也不用与猴子们为伍了。”
张北若有所悟地“哦”了一声,陷入了深深的沉思:对于满爷而言,开发成景点后的弄籁不再是他熟悉的弄籁,更不是他满意的弄籁;可对于来这里避暑休闲的城里人,包括自己,却是喧嚣的城市之外,一个幽静的、宜居的僻静之所。
按照壮族习俗,满爷在外亡故,是不能抬进屋内的,人们只好在满爷家门口搭起凉棚,把满爷的寿方抬出来。人们把满爷安放到寿方里,他的模样,也和往常睡在里头一般自然。满爷寿终正寝,人们为他举行了最为隆重的道场。在道场中,除了他的两个早已成为奶奶的女儿,张北也为他披起了麻戴起了孝。
有人说,满爷走了,娅满应该也不会活很久了,她跟着去只是早晚的事。他家的老瓦房,迟早会成为新的民宿。德春说,不可能!满爷生前答应把房子留给张北了,他也为满爷披麻戴孝了,他可是要陪着娅满终老,继续在这世外桃源里、在满爷家写作、生活下去的。
现在,春天就要来了,娅满还经常坐在门口纺线。张北不写作时,也常常坐在她的身旁,看她慢悠悠地摇着纺车,一圈又一圈,像无数个日日夜夜,轮回往复。
责任编辑 练彩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