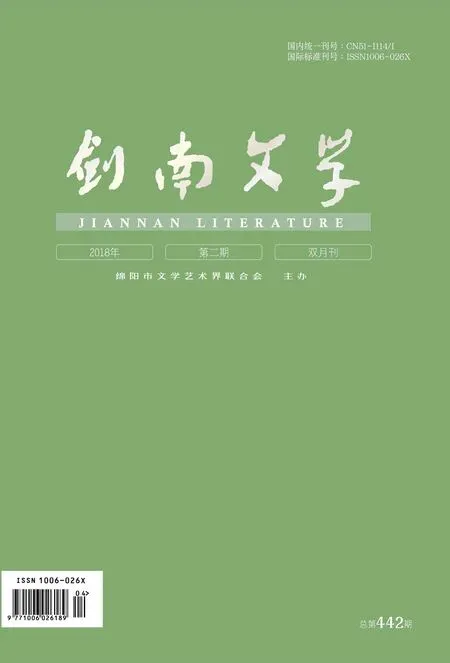论贺小晴小说的语言艺术
□ 李左人
贺小晴著有长篇小说《花瓣糖果流浪年》、中短篇小说集 《等你把梦做完》《脆响》、纪实文学《牛津不是梦》、报告文学《英雄无名》《艰难重生路》等,曾获徐迟报告文学奖提名、四川文学奖等,取得可喜成绩。
语言是小说家立世的根基,是作品灿烂的缘由。贺小晴非常重视语言,有一种自觉的语言意识,她说:“语言在文学中的重要性在我看来是绝对的,至高的。它既是形式也是内容。”(贺小晴《小说从现实中获得种子,却在内心长成》,当代微信推广。)下面,我们就打开其代表作《脆响》,探讨她小说语言的艺术特色。
一、形成个人语体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必须根据语言衔接和语义连贯规则组织语句段落篇章,呈现为一种具有表现性目的和个性特征的结构系统——文本。一个作家驾驭语言文字能力臻于成熟的标志,就是在构建文本的实践中形成了个人语体。所谓个人语体,就是作家的叙述有一种独具个性的言说方式,一种个人的表述风格。
贺小晴小说的魅力,很大程度出自语言。读她的文字就能感觉到她的格调、气派,感受到她的魅力和气场。她那样遣词造句的用语习惯,那样的叙事修辞手法,那样的表达方式,那样的才情机趣,形成了特有的语感、色彩、节律和柔性,仅从那娓娓的叙语即可认出此即小晴,就像从运笔的线条笔触、色泽韵致就能确认画家的手笔一样。
她的语感极好,这不只是天赋,更是一种功力。一方面,作家必须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触觉等感知外界事物,将对象内化于心;另一方面,还要对语言文字本身有一种深切的感受,即对语言文字意蕴、隐喻的心领神会,及对其形、色、音、味的敏悟贯通。两方面契合,产生了一种将客观事物和与之对应的语言文字相匹配的本领。贺小晴就具有这种感于物而源于心的敏智通达的表述才能。
贺小晴的叙述极富个性,文字简洁利索,呈现出清新雅致、流利俊爽的语体风格,在奔放与婉约交响的节奏中显示魅力展现韵味。试读:
我们的面前各放着一只托盘,那是加工和摆设珍珠的专门用具。大红漆底,乳白色的绸缎镶面,形如小报大小。一条条珍珠放上去,珠的含蓄温湿的光与绸缎华丽冷艳的光相互交汇,在大红底色的反衬下,形成一派光的奇观,光的极致,仿佛天上的银河掉下来,落到了眼前。(《台风》)
她重视语言的意美(文字内含)、形美(长短句交替)、音美(音调、节奏和韵律),仔细琢磨其中的奥妙,斟酌拿捏十分到位:
北海的美,美在海,美在街的深处。偶尔和朋友聊起它,我总是说,你知道吗,那个地方,三面环海,每一条街的尽头,都是海……海,海,海。海不在眼前时,是一份牵挂;海装在脑子里,是梦幻的代名词;海在我和小蒙这般从大山里走来的群类,是希望新奇机会挣扎冒险……甚至死亡,也说不准。总之,每当提起它,我总是小心的,细微的,怕它受惊似的,怕冒犯了谁……或许,海在心的深处,是一种预感,一份敬畏,也说不准。……海就在耳边,不到一米远的海堤下,啪啪啪拍着。那是海的语言。我们听不懂,但爱听。(《台风》)
虽出自人工却洗尽斧凿痕迹,虽经锤炼却不见打磨印记,仿佛灵光一闪偶然得之,浑然天成。由是观之,贺小晴已经找到一种属于自己的语言,拥有了个人语体。
二、精妙的比喻
在驾驭语言方面,贺小晴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比喻。明喻、暗喻、借喻、博喻、略喻……比喻的十八般武艺她样样精通,且能自出机杼,别开生面。有钱钟书《围城》的机趣和韵致,不过更现代更时髦;有张爱玲比喻的精妙,只是除却了悲凉意象。
贺小晴比喻的第一个特点是新颖奇崛,摇曳多姿。例如:“很多的时候,在大叔叔面前,我是一只贪吃的猪,可这时候,我却是一只伤心的企鹅,不吃不喝,眼前只有冰天雪地。”(《成长纪》)刚看到“我却是一只伤心的企鹅”时,会有些莫名其妙,“我”和“企鹅”间似乎找不到可供比喻联系的相似点,然而读到“不吃不喝,眼前只有冰天雪地”时,让人眼前一亮,曲径通幽,一个精妙的比喻出乎意料地闪现出来。再如:“我仿佛看见地上的那些落叶,金黄色,火红色,在艳阳里疯跑,在风里翻飞,就像小鸟一样,边跑还边停下来,看看我,就像看着关在笼子里的另一只鸟。”(《成长纪》)想象奇特,描绘出美妙的意境。
比喻贵在创新。有创造性,才能出语惊人:“正是中午,阳光落在地面,又像煮沸的汤汁一般溅起来,跳得老高。”(《脆响》)她深得比喻的奥妙,准确把握好本体和喻体之间相同处与不同处的“度”,匠心独具地创造出令人拍案的鲜活句子,透露出诗人般挥洒自如洒脱不羁的气质。比如:“说到伤心处,加上几滴眼泪,那故事就有了冤屈之意,她也就成了带雨的梨花。 ”(《蹦极》)意象华美,蕴含丰富。
在喻体的取材上具有多样性,身边的寻常物什看似平淡无奇,被她信手拈来,通过睿智的联想升华化作比喻,就变得生动贴切,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如今离了婚,老四的心就像腾空了的抽屉,七七八八的搬出去,倒掉了,装什么进去都有位置。 ”(《蹦极》)“妈妈说,我哭的时候也没有声音,就像一条湿毛巾,只淌水珠,没有任何动静。”(《舞台上的树》)
贺小晴的比喻不拘一格,手法变化多端。她用眼、耳、鼻、舌、身全方位进行感知,将各种感觉打通,互相转换,或将嗅觉变成温度,或将情绪换作颜色,或将声音转化为气味……通感超越了逻辑,句与句之间的一步跨越,直接置换,造成心理感觉的跳荡起伏萦回环绕。如《脆响》:“她终于忍不住搭起话来,好情绪也跟着话音漏出来,阳光般跳跃。”——将听觉转为视觉。如《成长纪》:“我妈妈这才有了笑容。很淡的一点点,就像枯萎的花上很淡的一点残香。”——将视觉变为嗅觉。
贺小晴打比方,就像说话一样随便,似不经意,张口即来,妙喻连珠,令人拍案叫绝。比喻,是她的个人语体之魂。
第二个特点是创新思路,运用递进的方式拓展比喻的修辞手法,创造了递进式比喻。
贺小晴的递进式比喻,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在一个比喻内更进一层,将事物的特征或内涵作深一步揭示。她的长篇小说《花瓣糖果流浪年》有一个这一特色的典型比喻:“他有一双深井般的眼睛,掉下去是听不见响声的。”人们大都能想到把深邃的眼睛譬作深井,她却更进一步,引申出掉下去听不见响声,其水之深,深不可测,奇思妙想,便非同一般。这类比喻在作品里比比皆是。
第二种是在一个比喻之后,再跟进一个两个比喻。请看《蹦极》:
茶在上面,汤在壶底,那茶汤就像是煮化了的琥珀,绿得发黄,黄得泛金,只是被夜色罩着,又被头顶的一盏惨白的节能灯射着,变成了一种灰黑色,仿佛头顶的天空掉下来,装在壶里,成了标本。鲁兵将壶里的夜色倒进杯里,一口一口呷着……
第一个比喻“茶汤就像是煮化了的琥珀”,因夜色和节能灯引出第二个比喻“仿佛头顶的天空掉下来……成了标本”。前一比喻是后一比喻的踏跳板,让想象倏地腾飞起来,盈满茂盛的生命感觉。再用“夜色”直接替换“茶汤”:“鲁兵将壶里的夜色倒进杯里,一口一口呷着。”这一意象的呈现才是比喻的落脚点,才是最精致的感觉和想象的独步,深得路转溪桥忽见之妙,最富小晴修辞的个性特色。
写作都须遵循一定的规则,做到有节有度,而小晴却采取《台风》里小蒙的做事之道 “做过头”,即做过分做出格玩到极致。一般人只使用一个层级的比喻,用跟甲事物有相似之点的乙事物来描述或诠释甲事物,这只是一种“说明”,难以唤起更多联想。而她下重手,使出一连串比喻,渐次递进,层层加码,循循然诱人勾人,直抵心灵深处,炫出令人惊喜的个性特色。例如:
每次跳舞前,我备服装,借道具,梳头化妆,忙得像只猴子(猴①),把自己涂得也像猴子(猴②);跳舞之后,我撑着张猴脸(猴③)满街走,大家频频回头的目光让我觉得与众不同,也让我妄生了不想过平常日子的幻想。我想把日子搬去舞台上,让人每天都像看猴戏 (猴④)那样看我。(《成长纪》)
紧扣像只猴的比喻,接二连三做意想不到的后缀补充,形成她语言的独特句型——这是贺小晴的绝招,是她比喻的秘密所在。
递进式结构原系论说文的议论方式,用在小说的叙述结构里,即在表述某件事情时,各层次、段落步步相连逐层推进,最后完成对形象的塑造。
不仅如此,贺小晴还将递进式比喻发展成一种叙事手法。试举 《成长纪》为例——
她先用一个段落总括小叔叔送交情书一事的过程:“回想起来,我与小叔叔的交往,也仅仅是限于招惹与反击,炫耀与被冷落之间,仅此一点,却足以让小叔叔心生星火,再成燎原之势。”接着,推出第一个比喻:“那之后,有一天,我放学回家,遇到了火焰般的小叔叔。”这是第一层,算铺垫。再看下面:
……那天傍晚放学后,夕阳已去,却又在另一个地方冒出来,火苗一般,在玻窗里燃烧。我看着窗里的那堆火苗,其实是在看自己。
第二层,夕阳和“我”都映在玻璃窗里“火苗一般”燃烧。看来,小叔叔的“招惹”并非没起作用,“我”也燃起火苗了。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一堆熊熊火焰,静默地逼近,那是一颗人头,每一根毛发都在舞蹈。
我猛转身:你……
我的表情肯定可怕,惊恐中带着恼怒,以至于小叔叔后退一步,张开嘴,半天没声音出来。
以上是第三层,小叔叔已燃成“一堆熊熊火焰”。
我缓过神,尽量地放平语气:你……你怎么在这里?
小叔叔不说话,只用脸色做反应。小叔叔的脸,平常因为少见阳光,也因为阴郁和寡言,白得瘆人,白得易碎,如同刚洗过的盘子。此时那白脸红起来,仿佛柴房着火,一寸寸爬高,一寸寸升腾,直至在头顶形成烈焰。
这是第四层,小叔叔仿佛柴房着火,烈火越烧越旺,“形成烈焰”。
小晴牢牢抓住“火”,用层层递进的比喻推动故事发展,演绎小叔叔从爱心萌动到交出情书的整个过程。这种有序编织的递进招数,在各篇小说中均有明显的路径可寻。
由此可见,层层递进的比喻不仅是手法的创新,还将比喻从修辞手段扩展为小说的一种叙述方式,上升到写作的方法层面,成为贺氏个人语体的一大亮点。
三、灵动洒脱的叙述人语言与耐人寻味的人物语言
小说语言大体可分为叙述人语言和人物语言。
叙述人语言由叙述语言(间或夹以议论)和描写语言构成,叙述语言主要用于交代背景、推进情节,而写景状物刻画人物形态则用描写,凸显细节,使形象鲜明生动,活灵活现。
贺小晴的叙述人语言,用她在《麻利花》里形容紫冰穿着搭配的话说,就是“于隆重中见疏淡,于素雅中见华彩,看似有意无意,实则格外的独具匠心”,感觉是“淡雅的,轻松的,不耀眼,却让人舒服,给人很深的印象”。具体来说,就是雅致简洁,灵动洒脱,自由而轻盈。试举一例:
紫冰这一圈走下来,竟起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原本她只是去到五楼,见一个交往多年的老友,没曾想在老友那里,见到了大多数评委。她一屁股坐下来,这才发现,她坐在了评委中间,评委们呈狐形状包围着她,形成了一种空间上的优势和向心力。她在视觉的中心,打哈哈,喝茶聊天叹天气,同时依稀地意识到,这一串哈哈下来,仿佛八月的风,吹落了一地桂花,一路的香气。至此,评委们再见了紫冰的名字,甚至见了报社的名字,就不再是从材料到材料了,而是从材料到人,从材料到桂花香……(《脆响》)
“桂花香”最有蕴涵,话中有话,别有意趣。
贺小晴的叙述文字奇异多变、波诡云谲,极富创造性:
我不能急,得让他慢慢说。但他说不成句子。他的那一口带有浓重口音的普通话,加上他那些混乱的词汇——他的词汇在平常的日子里,倘不标好数码,按照顺序说出来,便时常混淆视听;如今排序一乱,所有的词汇逃命一般,一古脑儿向外挤,堵塞了大门,妨碍了交通——我咬牙切齿,只听懂了几个字:空调没有了……(《台风》)
她善用细腻的文字叙述内心真实的情感,将无法捉摸的心理呈现纸上。下面一段,将离家之人对家乡的思念,说得极其透辟:
离家的人,在家纵有千般不好,真离开时,那家便背在背上,如同背着一台脱粒机,曾经的不好被扬出去了,剩下纯白的米粒,能抵过千般风景,万种美食。班上有一个女生,来自偏僻的小山村,大概因为思乡心切,开口闭口都是,我们村……而她的那个村子,在旁人看来,是不值得思念的,同学因此成了笑料,成了井底之蛙的代表。我也曾讥笑过她。那时候我们不懂,这是多么忧伤而无助的一种感情。家养育了我们,又抛开我们,没有家的孩子如同没有土壤的种子,我们随时都在做着回归的梦。(《成长纪》)
贺小晴思想敏锐,常常把对现实、历史、人性的洞察思考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泄露出来:
偏偏就在她命运出现危急的时候,大姐出国去了。没能听到大姐的意见,对她是个损失。大姐的电话她不是没有,也不是心疼钱,只是隔着漫漫重洋去说这等事,这事也就好像受了颠簸,经过了海水浸泡,变得不咸不淡了。她说不出口。再说就算她说出口来,她也相信这中国的喜怒哀乐落到异国他乡,有一种水土不服的异样感,既烦乱别人也帮不了自己,倒不如不说罢了。(《蹦极》)
叙述人语言一般都用来演绎故事交代情节,对于贺小晴来说,叙述最主要的作用是刻画人物。小说集《蹦极》里的作品都不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她往往随着事态的发展,对人物心理的变化作深入肌理的剖析书写,揭示人物前后嬗变的过程,比如《蹦极》里老四内心的斗争从挣扎到平复,《麻利花》里紫冰的思维脉络、吴总对紫冰态度前后的变化等,而对故事情节,如老四婚变的过程、结局,紫冰找评委、庆功宴席等,则用极具形象感的粗疏笔墨,避免了因交代过程而使记述沉闷。
即使是在交代事实敷陈过程时,也要随笔点染,描摹出人物在特定现场的心理脉动。如《蹦极》写老四:“她本能地打起了精神,走起路来特别轻松,转身的速度不但快,还带着美感,就像她是刚旅行回来,满肚子装着潺潺的流水,就要越过喉咙,跑到外面来唱歌。”
小说家大都不直接站出来议论,贺小晴偶或发表意见,亦如蜻蜓点水般点到即止,却藏着对世态人心的体验体察,犀利而深刻:
四川男人的身上,有一种巴山蜀水的迂靡气息,骨子里放了香料似的,男人们多多少少带点阴柔气。(《台风》)
有时用三言两语表达抽象的人生经验、生活哲理,画龙点睛,生动形象且风趣幽默:
假如套用一个老掉牙的比喻,女人如衣服,那么小黄就是内衣,好好赖赖的,总是穿得越久,越感觉舒服;而静秋好比外套,越是华丽的外套,穿的时间越少。(《台风》)
再谈描写。贺小晴的描写语言,简洁,准确,写景状物绘声绘色生动传神,给人身临其境之感,刻画人物栩栩如生,仿佛近在眼前触手可及。
贺小晴善于通过人物的行动、动作刻画人物。她含英咀华、揣摩琢磨,挑选精确的词汇赋予一个动作以实际内容和直观效果,表达极具张力与想象力。看看下面的例子:
二姐突然大呼出一口气,呼救一般,张着嘴,却发不出声。眼睛定定地挂在天花板上,像被绊住了,取不下来。(《蹦极》)
“她的心一疼,像被人生切下一块。”(《脆响》)
“再进屋去,她显然有些谨慎,连呼吸也是轻拽着的。 ”(《脆响》)
这“挂”“绊”“切”“拽”,充满动感和韵味,透出力道,其间的字斟句酌、与其它语词的搭配勾连,显露出作者语言的功底和表达功夫。这需要平时进行细致的观察、揣摸、体悟,观察越细致,发现的东西越新颖,表达便越独特;感受越深切细腻,描绘就越准确精微。
再如《扶桑》里的人物描写:
父亲在上座上,安静地坐着,脸依然端正,依然白净,只是白净的脸上,挂满了沟壑。那些沟壑不因为风吹,也不因雨打,是心的拖累,让它直往下沉。父亲脸上的皱纹是纵向的。这让他的脸看上去,像一片瀑布结成了冰。然而父亲正拼尽心力,要让自己回暖,这从他的目光中看得出来。父亲没有笑,只柔柔淡淡地看着亲友,那眼神,仿佛黑屋子里透出来的几缕灯晕。
描写“父亲”这样的川剧艺人,小晴只需调动早年的生活积累,回放记忆就行。镜头对准他的眼神、脸色,精细描绘他的动作细节,便把他的内心、气场,以及他冷峻、严厉的性格表现出来,极富现场感。
再看看《台风》里描写的酒店老总方远:
他也笑。但一眼可见他是不擅长笑的,甚至还有些不屑,又不得不临时敷衍。他的皮肤因为常年撑着,已少了弹性,往一块皱时,仿佛石头上的波纹,老半天成不了形;成形了,又一生一世,再也难以复原。
同样是描写男人的肖像,小晴只写方总皮笑肉不笑表情引起脸皮打皱变形,其它外貌特征一概略去,就将他对 “我”冷漠、傲气、僵硬的德行表露出来。
她特别注重景物描写的意味,即使作为背景也要写出散文的意趣、诗的机趣,酿成满纸风情,于洒脱中见大气,于爽利中见俏丽:
四川的风光,是山为主体,水为魂灵的世界。山和水彼此相依,互为缠绕,却又和平相处,平分着秋色。好比一对举世无双的恩爱夫妻,山水之间,形影不离,神韵相伴。离开了山,水就失去了方向;离开了水,山就失去了原能。而不像江南的景致,水就是一切,除了水,一切都是附庸,是佩饰,是点缀。然而江南人想造一个以大大小小的山为主体的景致不容易,四川人却偏偏莽撞着,要在任何一个稍微平坦的地方,造一片江南出来,倒不能不说是一种盆地心理。(《蹦极》)
红叶还没有出来,还躲在绿叶里说着梦话。绿多了,多成了酒,饮着,喝着,不知不觉,醉了……(《麻利花》)
再看下面一段对“尘土”的描写:
她领他回到了他的家。是一套久不住人的房子。人离去,灰尘从天空落下,伞兵一般布满了整个空间。是灰尘的味道。人离去时,无形的尘土渐渐现身,有形有味,盖过了曾经人的气息。死寂的,尘土。家已不在,唯有房子。(《脆响》)
小晴常用比喻把不可触摸的抽象概念描绘成具体可感的物象,如《蹦极》里的例子:“人一得意,思绪就像潮水一般涌上来,啪啪地拍着她的脑袋。”
除了比喻,她还善于用夸张。比喻和夸张都是最富浪漫意味的小说修辞手段。
她们的朋友任刚从外地蹦极回来,眼发亮,脑冒汗,心根本就没在衣服里蹦,而是直接蹿出来,在大家的面前手舞足蹈。(《蹦极》)
客房到海滩的距离,顶多不过五十米。感觉中,人在客房,打一个喷嚏大一点,唾沫星子都可以掉到海里去。(《台风》)
作者抓住事物的特点,透过主观情绪予以渲染,用夸诞的喻象,强悍有力的文辞,或放大或缩小,突出实质,将自己的意图和情感表达出来,增强了文章的气势、张力,达到震撼效果。
她也采取象征手法,借物写人,如用小蒙特别买的一把摇椅寄寓他的人生命运:
我这才在意起来,用手摸着椅子的扶手。是不一样,实木的颜色,实木的质感。纹路一条一条,清楚可鉴,几乎可以看出它整个的命运:长在大山里,被斧头伐下,再运到城里来,脱胎换骨。(《台风》)
下面谈小说的人物语言。人物语言必须切合人物的身份、职业、年龄、经历、个性、场合,用他(她)自己的语言刻画自己:
我妈妈看着我,就像看着一堆甲骨文,皱着眉,身体微微拉开,说,你看你,黄毛丫头一个,头发那么少,眼睛又那么小,就像用茅草割开的一样,一条缝,额头又那么高,眼睛长进去,就像长在岩腔里,下雨也打不湿眼睛眶眶……(《成长纪》)
“妈妈”的市民腔调,对“我”的厌烦,表露无遗。
对话,不仅是人与人交谈,不只是简单地交流信息、交代事情,还是人物间关系的“碰撞”,或久别重逢谈笑风生,或话中有话各怀心计,或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或款语温言却暗含机锋,或“顾左右而言他”避开尴尬,或相对无言唯有眼波流动……有千百样的人物性格和千百样的人际关系,就会有千百样的话语角逐和千百样的言辞交锋。在《麻利花》里,评奖结束,午饭过后,紫冰和吴总回到客房准备午休。吴总躺在床上转向紫冰,用手枕着头。紫冰意识到她有话要说,爬起来,倒一杯水放在床头——
吴总说,我发现,你平常手不离杯,睡觉也要放一杯水在床前。
紫冰笑道,我这人爱喝水,有时候不是喝,是一种习惯,就得有水放在眼前,喝不喝不重要,没有水,就像没有魂似的。
后面的话夸张了,是拿自己打趣,调节气氛。六天了,她和吴总第一次说起工作之外的事。
喝水好,吴总说,但我不喜欢喝水,渴了才喝,不渴总想不起来。
紫冰见过吴总喝水的样子。一大杯水,对准了嘴,杯子倒栽着,喉咙里咕嘟咕嘟响半天。再看杯子,只剩下茶叶。
紫冰心里笑着,竟说出口来:你那是牛饮,不叫喝水,更不叫品茶。说完又觉得自己冒失了,失了度。换着以往,在报社,她是打死也不会这么说的。
吴总倒是笑了,说,是啊,你看你,包里随时还带着茶叶,真是会生活。
“言为心声”,吴总、紫冰的对话,泄露了各自隐秘的心理活动。二人平时常发生龃龉,但通过评奖配合拼杀,共同的胜利让她俩渐释前嫌,这一席交谈充满生活意味,表明关系出现微妙的变化,悄然推进了情节发展。
再看《成长纪》阿姨对恋爱中的“我”的一番劝诫:
阿姨说,这个周末,你带他来,让他来认认门,这样我们放心,这样你们也比在学校……好!阿姨的意思我明白,原本她想说,“这样也比在学校方便”,可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方便一词含义复杂,话说透了,让人难堪,也让长者失了分寸,便临时凑合个“好”字。
阿姨欲言又止,“方便”一词,有所顾忌,话到嘴边吞了回去,换成了“好”。这吞吐之间,人物彼此的关系就有了意味,那说出口的“好”字也让人领略到未能明说的意思来。
小晴处理对话,多用逗号、句话断句,省略了引号。对话与叙述夹杂在一起,加重了叙述人色彩。延绵不绝的陈述,仿佛回到不使用现代标点符号只点出 “句读”的年代,使叙述更加口语化、生活化。特别是她爱用第一人称叙事,更增加了直接向读者倾述的亲切感。缺点是,淡化了对话当事人的语言个性;偶尔,还让读者弄不清是人物说的话还是作者的叙述,得回头再看、理顺,影响了阅读的流畅感和兴致。
仔细研读《脆响》,可以看出贺小晴其人,才、情、趣兼备,文笔清新雅致,轻盈洒脱,尤以想象奇崛意象诡丽的比喻见长,行文舒卷自如、灵气流转,形成了个人语体,彰显出与众不同的语言个性。作家马笑泉在《小晴印象:一半是酒,一半是茶》中说:贺小晴是一位“真人”,她的精神特质一半是酒一半是茶。状态最好的时候,能将“酒”与“茶”调和于一体,创造出既冷酷又温暖既尖锐又柔软的文字,却又浓烈得令人心碎……马笑泉识得贺小晴语言真谛,论说透辟到位,我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