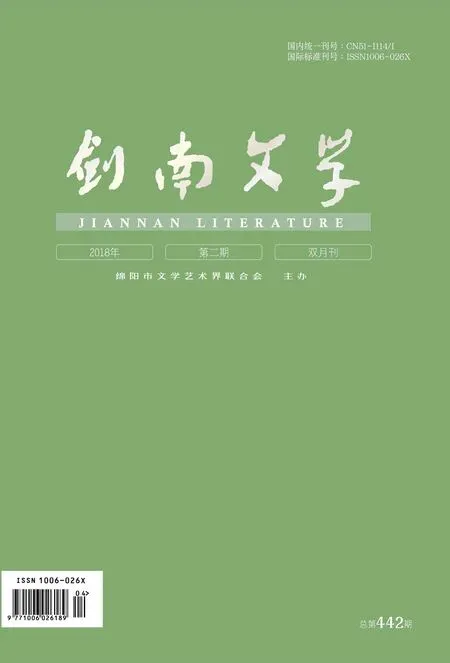追忆年少轻狂(外一篇)
□ 石纽山
邀约几个好朋友,买回几个订书机——我想取用里边小小的弹簧,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设计一个机关,让若干弹簧产生的力无限放大,驱动曲轴带动轮子旋转……我吹嘘道,事成之后,我们的银子要比诺贝尔当年挣的还要多得多。我暗中算过,要是将来汽车、拖拉机都换上这个机关,几年下来——那可不得了!然而,反复试了几次,材料浪费不少,直到第二年春季,也没取得成功。期末,成绩出来,我的名次由班上前几名陡然下降到40多名,气得老师大发雷霆。班主任刘家祥老师终于摸清原因,找我谈心。刘老师说,你搞这个就是外国人几百年前想搞的永动机,是违背自然规律的,是搞不出来的。我的心里一下凉了,但不服气,直到初三学了能量守恒定律,知道了什么叫省力不省功,这才完全死心。
我家世居农村,长期困于山国。我课堂上开小差,想到父母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头就有几分酸楚、几分不忍……现在发明的事落空了,要想解放父母,除了考学,无路可走——北大清华名声响亮,可那不读高中不行——要想短平快,只能考中专。初三那年,在一座木楼上,教我物理的孟关军老师背靠床位伏案批改作业,我就坐在他的对面悬梁刺股,直到零时,夜夜如此。周末,刚传来不久的稀奇玩艺儿——电视,放得十分火爆,我也能忍住不看。1981年9月,我考入邻县一所师范;校园依山傍水,风景如画,我却无心读书。偶然看了居里夫人自传,她的家乡绿草茵茵,她的少年生活戚戚,可她历尽坎坷,终于到了巴黎,进了高等学府,而我面前,看不到一线曙光……正当我在沮丧之时,一颗救星从天而降,他说,用坛坛罐罐做试验已经行不通了,你作文写得好,还是当作家比较现实——当作家只要有笔、有生活就行了……所谓救星就是桂玉德——我的同班同学,时任《寸草》(校刊)主编。他说,你可先给《寸草》投稿,好稿我们可以向《剑南》杂志推荐……
不过,我心比天高的毛病,还是没改。唐诗宋词汉赋和《樱花赞》这类散文,读来朗朗上口,倒是有些情趣。但那鲁迅,结构助词太多了,读来拗口,很是让人厌烦。我想自己随便写篇作文,也比鲁迅顺畅得多。有了这份轻狂,就想一鸣惊人;有了这种自大,就想一飞冲天。我过铁索桥到安昌古镇偷偷买了一摞作文本,每天上完课草草完成作业,就独自躲进图书室,偷偷从事“文学创作”——短的不写,偏写长的。到了第二学期,写出10来万字,沉甸甸的——感觉不到那是轻飘飘的。我只知有天,不知有地,没想过投寄《剑南》,想的全是如何炸开《当代》《钟山》这样的大刊。不料期末考试,竟有两科不及格,老师瞪着眼,我则低着头……挨批事小,到时候拿不到文凭,解放父母的计划泡汤了,这可不是小事。
我盼星星盼月亮,盼到师范毕业,被分配到北川贯岭乡上村庙小学。山是巍巍群山,道是羊肠小道。我从早上8时出发,背着一床被子、一口木箱,迎着朝阳上路,穿越鸽子花早已凋零的原始森林,直到黄昏时分才赶到学校。校如其名,的确是座古庙,建于明代,梁柱特别粗大,庙里没有菩萨,只有摆放杂乱的课桌。南北两侧各有三四间木房,有作教室的,有作宿舍的。有间宿舍没有闭门,面积10来平方,内置一桌一床……因为太累,我草草做了一下清洁,就铺开床单躺到床上睡了……耳边,山风呼啸,禽兽啼鸣,分外凄清;到了半夜,居然出现灵异事件——我清清楚楚地听见,在距离床面不足两米的木楼上,一会儿窸窸窣窣,像是有人走动;一会儿敲着鼓点,像是有人追逐……我闭上眼睛,想到了古庙里的菩萨,想到了傍晚在庙后野草丛中看见的孤坟,继而联想到了孤坟里的野鬼。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连大气也不敢出一声;等到天明,爬到楼上一看,除了鼠印,什么也没发现。
就在这所学校,我白天守着古庙,教书育人;就在这个房间,我晚上就着青灯,写诗作文。时隔一年,我改定了第一部大部头《山里的绿》。对于这部“作品”,也是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没有投寄《剑南》,而是跑到乡场上,包裹严实,投寄给了《中国作家》。
当年,都坝与桂溪之间,顺着都坝河蜿蜒蛇行的那条古道,长约60华里。每天早上,来自都坝的若干马帮驮着山货,途经上村庙浩浩荡荡地朝着桂溪方向进发;傍晚,这些马帮驮着洋货,踏着落日余晖,又经原路过上村庙向着都坝方向行进。都坝、贯岭两乡教师等人的供应粮,都靠这些马帮驮运——每人每月供应29.5市斤粮,每次收取运费五元。
文稿寄出不久,我托一位马帮朋友,请他路过乡政府顺便到邮政上看看……终于,马帮朋友帮我带回一个包裹,右下角印有《中国作家》编辑部地址,我一看就知道——黄了……独自回到宿舍,轻轻闭上柴门,默默拆开邮件,里面附有一封短信——比退稿本身还要刺伤我的,就是这封短信!草草读了一遍,化成一地碎片。但其核心内容,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分明。开头称呼培芳老师,接着写道,从你的来信看,你是一个豪情万丈的青年,但从你的作品看,你的表现能力还很差……我今天给你泼一瓢冷水,你会生气……但过些年气就散了……最后写道:“作家的梦不是好做的,但只要肯做,也许能成功。”落款:萧立军。
这个萧立军,我查了资料,是吉林人,比我年长12岁,早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国作家》编辑、主任、编审,是一位作家,我读过他的长篇小说《无冕皇帝》,这部作品因为伤及“皇帝”,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据说曾被“停职反省、停发工资”。就是这个萧立军,让我这颗飘忽的心从天上回到了地上,从盲目走向了清醒,从狂妄走向了谦卑……
我在星光之下
我在星光之下,身上也能沾上一点星光,这除了感恩《剑南文学》、感恩编辑老师之外,更要感谢生活、感谢时代。我的生活沮丧过,也开心过;曲折过,也顺畅过……
我生在一个偏远山村——家住阳山之阳,隔一小溪就是左氏一家。记得儿时,左氏和我母亲闲聊,说她身上有点奇怪。母亲问,啥子奇怪?左氏答,她有四个奶奶。我妈不信,她就脱了上衣。我因好奇,也把脖子伸得老长老长,见她果然长了四个乳房,其中两个挂在胸前,上下闪动,与常人之乳无异,另外两个长在臂上,酒杯大小,像是胸前二乳按比例缩小的一对样品。母亲又问,有奶水不?左氏再答,坐月子那会儿有一点,但是很少。
就是这个左氏,生产能力极强,生养了13个。当年,每当收割季节,队上分配粮食,都要人均分足基本口粮;基本口粮分足以后,所剩无几,所以左氏一家所得总量最多。如此一来,劳动力多的农户就有意见,这些意见不能采纳,就有人出工不出力,成天磨洋工。有人成天磨洋工,地里的收成也就一年不如一年,最后酿成一个结果,家家户户一贫如洗。左氏一家,众人以为占了便宜,其实也是凄凄惨惨。有一天,我从她家路过,左氏热情邀我吃饭,可是看见一家大小碗里只有菜、不见粮——不客气地说,像是猪食,哪里还有胃口?
穷则有梦,不能等死。村上几个知青,有个洋玩艺儿——收音机。他们怀着对现实的失望,曾在夜深人静之时,邀约几个同伙偷听敌台。我也凑过热闹,收音机里像我多年以后在电视里看广告一样,节目正式开始以前总要提高嗓门:“台湾,中华民族的复兴基地……”然后说些什么,我已毫无印象。后来,民兵连长左夫,带上几支步枪,摸到现场逮个正着。翌日开批斗会,我等正在村口观音庙读书的小学生也被应邀到场。犯人交代问题很多,其中唯有苏联谩骂中国“三个人穿一条裤子”这一条,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所以至今还能记得。
我的父亲,只做实事。当时农村类似井田制,要等一个月才放一天假。父亲抓住这个机遇,钻进深山老林捡木耳,然后弄到江油去卖——那里建有国防厂矿,可以卖个好价钱。有一回,天降暴雨,父亲直到半夜都没回来,急得母亲跑到雨中号啕……父亲第二举措,就是天不亮起床,利用出工前的空当到屋后背土,把门前那块晒粮食的坝子铺成一块田地,种上洋姜,再用洋姜辅以麸子、野草养猪,一年出槽两头,一头交公,一头食用……如此一来,小日子也就相对滋润一些。可是好景不长,因为来了一场什么运动,要割资本主义尾巴。
有一天,我的老师——肖公联扬,中江县人,后来调回老家,再没见面——把我叫到一边,轻轻抚摸一下我的脑袋,和颜悦色地说,明天别去开会,你的日记写得好,你的作业就是回家写一篇日记……我把日记交了,肖老师打了100分,称赞我有出息。可是那天下课之后,就有一位同学数凳相叠,爬到台子上,模仿我的父亲低头弯腰:“我向革命群众敬礼……”台下哄堂大笑,我则无地自容。因为就在写好日记那个晚上,父亲回来,我就知道他被批斗,还被罚款558元……多年以后,回想此事,我才悟出,肖老师叫我写日记、不参加会,随后又夸奖我,不是因为别的,而是他心中拥有一份对我这个无助孩子的深厚的爱。
小小年纪的我,经历如此之重的屈辱,难免有些悲观、有点绝望,但是,生存的欲望,以及对于美好明天的向往,又让我有了无穷无尽的力量,生长出了永远压不弯的脊梁……
几年以后,迎来改革开放,我的境遇渐有改观,我的家乡、我的祖国渐有剧变。我经历过原始性的生活,也体验过现代化的生活——在这三十多年,我好像穿越了三千年的时光隧道,充分感受到了中华民族成就伟业的曲折历程。在这伟大的时代、英雄的时代,个人虽是沧海一粟,但我毕竟参与其中,至少流过汗水、淌过眼泪……现在想来,我真幸运——如果上苍让我生在富贵人家,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就可能停留在皮毛之上,不会如此通透。
前些时候,有人抱怨,或是带有歧视心态抱怨,抱怨农民伯伯辛辛苦苦生养了好多好多坏孩子。仔细想来,其实毫无道理。大凡中国人,都与农民之间有一根长长的脐带——你不是农民,你的老爸是农民;你的老爸不是农民,你的祖父是农民……所以,无论老虎,还是苍蝇,他们都是中国公民辛辛苦苦生养的孩子,这与农民的身份并无直接因果关联。
我问自己:面对弱者,我为什么不欺?面对强者,我为什么不怕?面对众生之苦,我为什么心酸?莫言老是抱怨儿时挨饿、母亲挨打,为什么面对曾经迷恋斗争哲学、如今两鬓苍苍的故人,我会心生悲凉?萨达姆、卡扎菲之流活着固然风光,为什么想到他们的结局、家人的不幸,我会心生怜悯?回望历史,有人为了权欲,刚在帐外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回到帐内即刻就可变脸——喜笑颜开、搂着妃子很快进入欲仙欲死的境界,我为什么无法理解?
我想,或与血型有关,我是O型——万能输血者,先天无害;理想主义者,特立独行。
当然,也与文化基因有关,我的母亲走路,看到蚂蚁搬家,就会主动避开。我小时候,三爷曾经拿出几本古书,说是族谱,教我背诵祖训:“夫言行可覆,信之至也;推美引过,德之至也;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兄弟怡怡,宗族欣欣,悌之至也;临财,莫过乎让。此五者,立身之本。”那个时候,似懂非懂。多年以后,方知其意:说话做事要经得起时间检验,这是诚信的最高境界;把成绩让给别人,自己敢于担当,这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建功立业,为父母增光,这是孝敬的最高境界;兄弟姊妹开开心心,族中老少和和睦睦,这是友爱的最高境界;面对财物,尤其应该谦让,不能过于贪心。这五条,是立身处事的根本。
我想,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我的世界,阳光比影子多,光明比黑暗多。我的小学老师、初中老师,我读师范和到绵阳脱产学习时的老师;我的好多亲人、好多乡亲、好多同学、好多同事、好多领导;我的文朋诗友,以及《剑南文学》的编辑、作家和诗人……他们眼里闪烁的光芒,就是沐浴我的阳光;他们嘴角绽放的微笑,就是黑暗中的光明。这些数以千计与我有缘、助我爱我之人,有的伟大,有的平凡,有的艰难,有的顺畅,有的叱咤风云,有的默默无闻……不管属于何种情形,他们勤劳朴实、心怀善念、坚守正义和远离邪恶的美德,都在漫长的岁月之中化作春风春雨,吹在我的叶上,浇在我的根上,内化成了我的人格。
回首当年,我就是一个梦想家。我的梦想,除了自己的前程,以及如何解放父母,很少联系到别的什么。当然,我不认为这是什么坏事,相反,对于我的成长,还是一件无可替代的好事。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现在,我虽同样有梦,但与前程无关,我知道,我就是地方上一个小文人,如此而已;也与解放父母无关,因为父母的坟头早已芳草萋萋,他们的灵魂是否栖居天堂,我想将来到了那个地方,就会找到答案。现在,我已衣食无忧,所以,我最大的梦想,就是尽我所能,为我的桑梓、为我的祖国做点什么——不辜负疼过我的父母,不愧对爱过我的亲人;不白吃禹里的山珍,不白饮羌乡的山泉……
我热爱我的生活,我喜欢我的职业,我将继续行走在天空与大地之间,上可接触大小官吏、文化名流,下可亲近黎民百姓、父老乡亲,生活既不繁冗,也不单调,岁岁年年,年年岁岁,那颗星辰都会从我东西两侧的窗口,把光亮洒进我的房间,照亮我的心灵……
想到多年以后,我们坐在夕阳下面,对饮一坛咂酒,此时此刻,顿生诗情——
儿时的玩伴,头发花了,胡子白了;吸管里流动的时光,都化成青山了。
儿时的玩伴,皱纹深了,眼睛浊了;吸管里燃烧的岁月,却更加芳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