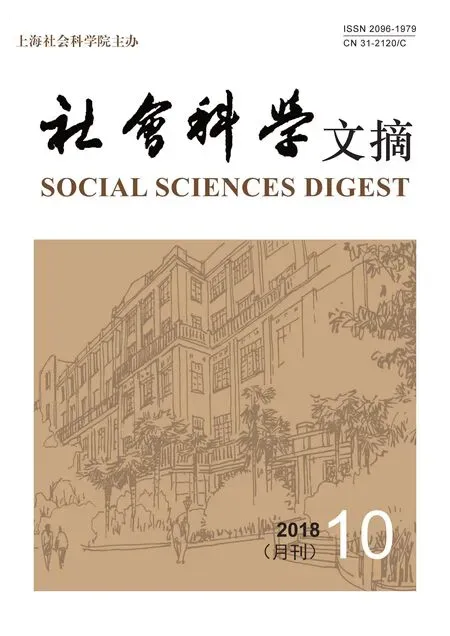论美学与文艺学的关系
关于美学和文艺学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
在中外美学界,关于美学与文艺学之间的关系,一直存有争议,迄今为止,大致已形成了以下三种看法:
一是美学与文学艺术无关,美学与文艺学是毫无关联的两个学科。如被称为“美学之父”的鲍姆加登,在所界定的“感性认识的科学”这样的美学定义中,艺术就未被提及。苏联美学家尤·鲍列夫认为“文艺美学”“音乐美学”之类的提法原本就不够科学,是“把美学泛化了、庸俗化了”。德国美学家康拉德·费德勒更是曾以激烈的口吻断言:“美学不是艺术理论”,“美学和艺术的结合”毋宁说是“美学领域的第一谬误”。从逻辑上来说,这类看法是有一定道理的,由于研究对象、研究视点、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方面的差异,“美学”当然不应是一般的“艺术理论”。但由于文学艺术呈现为感性形象,能够给人以情感感染,因而无论从源于鲍姆加登的“美学”之本义的“感性学”,还是从后来康德及其他许多美学家所主张的美是一种心神愉悦的情感判断来看,美学与文艺学之间又有着天然的不解之缘。
二是美学基本上就是文艺学。如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虽亦论及自然美与现实美,但在“全书序论”中已点明,他的美学,是一部关于“美的艺术的哲学”,其研究对象的范围是“美的艺术”;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强调“整个艺术、特别是诗的共同原则的体系”才是美学研究的中心对象;苏联学者布罗夫认为美学就是“艺术哲学,是一般艺术理论”;我国美学家马奇在《关于美学的对象问题》一文中亦曾明确强调:“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这类将美学等同于文艺学,否定了美学与文艺学之间学科界限的看法,显然是不合理的,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按此看法,美学与文艺学,只能二者留存其一。如认定“美学就是艺术观,是关于艺术的一般理论”,“文艺学”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或将美学的研究对象完全集中于文学艺术,现已成为世界性学科的“美学”,也就同样失去存在的必要性,难以成其为独立学科了。
三是美学与文艺学密切相关,认为美学研究的对象既包括现实美、自然美,也包括文学艺术美,美学可介入文学艺术的研究,形成诸如“文艺美学”“艺术美学”之类的交叉学科。如《美国学术百科全书》对“美学”的定义是:“美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其目标在于建立艺术和美的一般原则”;德国《哲学史辞典》认为美学“研究的是美与艺术”;在我国,胡经之先生的看法是,文艺与审美,既不完全等同,亦非毫不相干,二者之间是一种交叉关系,并据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开始了关于“文艺美学”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与探索。与第一种、第二种看法相比,这类看法无疑更为合理,不仅有助于美学体系自身的完善,以及美学研究的切近实际,亦有助于文艺学研究的扩展与深化。多年来,在我国美学界,这类见解与主张基本上也已成为共识,且已形成了“文艺美学”“艺术美学”以及更为具体的“小说美学”“诗歌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等研究门类,并已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在教育部颁布的现行学科专业目录中,文艺美学与艺术美学 ,也已分别被列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文艺学”与艺术学的二级学科“艺术学理论”中的主要研究方向。但由于美学与文艺美学、文艺美学与文艺学之间的界限尚存混乱,以及究竟何谓文学艺术的美之类问题的模糊,在我们现有的研究中,也还存在一些需要深究的问题。
美学与文艺学常被混淆
我们已有的“小说美学”“诗歌美学”“绘画美学”“书法美学”“音乐美学”“文艺美学”之类著作或教材,常常给人不顾学理与实际效果,让美学过度侵入了文艺学领地的感觉。
或未经理论内涵的有效置换,将原有的文艺学范畴贴上了美学标签。如在我们的美学教材中常见以下论述:“在魏晋玄学的影响下,魏晋南北朝美学家提出了一大批美学范畴和美学命题,如‘气’‘妙’‘神’‘意象’‘风骨’‘隐秀’‘神思’‘得意忘象’‘声无哀乐’‘传神写照’‘澄怀味象’‘气韵生动’等。所有这些范畴和命题,对后代都有深远的影响。”且不说将一些古代文论家称为美学家是否合适,进一步推究会意识到,将许多本已有特定内涵的文艺理论术语改称为美学范畴,这除了贴上一个美学标签之外,似乎并不具理论内涵的增值意义。谁又能说清楚“气”“妙”“意象”“风骨”“神思”之类的文艺学范畴与美学范畴的“气”“妙”“意象”“风骨”“神思”等有何实质性区别?
或将原有的文艺理论,纳到了美学的名目之下。如在一些题为“艺术创作美学”的著作中,我们仅由“艺术本体”“艺术创作动机”“艺术构思”之类章节标题就会感到,这“艺术创作美学”不就是“艺术创作学”吗?在不少美学史、文论史著作中,亦常见美学思想与文艺思想的重合,如由“小说萌生的语境”“小说意识的自觉”“小说繁荣期的建树”之类论题及相关内容就会让人感到,一部《中国小说美学史》,大致上也可叫作《中国小说理论史》;李泽厚那本影响颇大的《美的历程》,也基本上是一本“美学”特色并不突出的关于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的简史,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对中国古典文艺的匆匆巡礼”。在朱光潜先生的那部《西方美学史》中,亦多见“但丁的文艺思想”“文艺的社会功用”“意大利的文艺理论与美学思想”“狄德罗的文艺理论和美学思想”“艺术的本质和目的”之类文艺理论内容。面对这样一些论著,人们必会愈加困惑于何谓美学,何谓文艺学。
即以一些比较优秀的艺术美学论著来看,作者虽对一般艺术研究与美学研究尽力予以区分,但二者亦存缠绕不清的缺憾。
浏览美学、文艺学、艺术学论著,我们还会发现,同一个人的同一些思想,可被甲说成是“美学思想”,亦可被乙说成是“文学思想”或“艺术思想”,而实际上,这“美学思想”与“文学思想”“艺术思想”的所指之间,并没多少根本区别。同一位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有人以审美特色论之,有人以艺术特色论之,所论内容也往往没多大差别。
这样一种混淆美学与文艺学的现象,当然不止见于我国美学界,读一下日本美学家今道友信的《东方的美学》就会感到,他所讲的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刘勰等人的美学思想,不就是我们的中国古代文论中所讲的他们的文艺思想吗?在今道友信的论述中,王羲之的《书论》也被称为“美学著作”,羊欣也被称为书法美学者,这与一般书法史上所说的《书论》是书法理论著作,羊欣是书法理论家,又有何本质区别呢?在论及《文心雕龙》时,今道友信道:“这些诗人辈出之后,《文心雕龙》对文学的美学原理,创作方法和欣赏的原则等极有深意的问题,作了探讨。若与西方同时代的情况相比较,恐怕这确实是可惊叹的高水平的文艺论。”这里,作者已径直将“美学原理”与“文艺论”等同划一了。既然“美学原理”就是“文艺论”,那又有何必要在已有“文艺论”的情况下,再另外加一个“美学原理”的名目呢?
传统美学准则无法全面解释文学艺术的特征与价值
美学之于文艺学研究的重要意义或许在于:能够从美学角度,更为科学、更为深入地解释文艺作品的特征与价值,但我们已有的相关见解与论述,则时见捉襟见肘,或生硬牵强。
在中外美学史上,极具普遍性的一种观点是:“美”的事物的根本特征是能给人心神愉悦的快感,审美价值就是愉悦价值,这看法无疑是符合实际的。但用以“心神愉悦”为基本特征的审美价值观解释自然美与现实美,容易说得通,而用之于解释艺术美,情况就比较复杂了。因为在自然与现实事物中,令人愉悦之“美”或不愉悦之“丑”,是比较容易区分的,如凡一位心智正常的人,面对一丛鲜花时都易生欣悦,面对一堆粪便时常会厌恶作呕,前者即可谓“美”,后者即可谓“丑”。而用此道理解释文艺作品的美时,就不如此简单了,有的说得通,有的则榫卯难合了。
对于表现了自然与现实中原本就是美的事物的作品来说,这是说得通的。如在阅读“两个黄鹂鸣翠柳”“东风夜放花千树”这样的诗词时,在欣赏齐白石的花鸟画时,我们自是会产生“心神愉悦”之美感。但当面对表现了丑、恶、凶残之类事物的作品时,我们就不是如此的“心神愉悦”了,因而也就有点说不通了。英国美学家李斯托威尔在1933年出版的《近代美学史述评》中就曾指出,在艺术欣赏过程中,不可能全是“纯粹的享乐”,“当观看莎士比亚、易卜生、梅特林克或者霍普特曼的一些伟大的悲剧的演出时,或者当阅读哈代或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些忧郁而又具有强烈的悲剧性的小说时,谁不曾忍受过最残酷的痛苦呢?谁又不曾一下就为杜米埃那种卓越的漫画,为左拉或莫泊桑所写的那种卑微而又带有兽性的人物,为吐鲁斯-劳特累克所画的卖笑的娼妇,或者为田尼哀所画的酒气醺醺的农民,所吸引而又感到厌恶呢?”英国著名诗人艾略特也曾这样指出,文学作品的价值决非仅是体现在让人得享阅读的“愉快”,认为“当文学被‘纯粹为了愉快’来阅读的时候,它是最危险和最扭曲的”。事实上,诸如《哈姆雷特》《战争与和平》《红楼梦》这类伟大的文学作品,给予读者的,就决不可能仅是“心神愉悦”之类的审美满足。如果仅是“纯粹为了愉快”而阅读,恐也就难以体悟到这些作品的伟大之处了。
近些年来,有不少西方学者,对传统的以“心神愉悦”为基本特征的美学准则,论及艺术之是非的见解表达了更为强烈的质疑。美国学者丹托在《美的滥用》一书中,就曾更为明确地指出,“好的艺术”不一定是“美的艺术”,并举例说“马蒂斯的《蓝色裸女》是幅好作品,甚至是一幅杰作——但若有人说它美则是一派胡言”。这类质疑与反驳,是值得深思、值得重视的,当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探究:艺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美学的对象?美学应从哪些方面介入文学艺术的研究?
文艺美学应着眼于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
由于美学与文艺学,毕竟是两个不同学科,二者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根本区别,交叉而形成的文艺美学之类,自然也应既不同于美学,亦不同于文艺学。也就是说,只有切实抓住文艺美学的特征,真正从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着眼,我们的文艺美学之类的研究,才有可能走向深入,才能更有成效。具体来说,应进一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应进一步明确文艺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视点及研究方法等。虽然,与文艺学相同,文艺美学之类的研究对象亦是文学艺术,但二者应有的区别是:文艺学重在研究的是不同艺术门类的特点、创作规律、艺术技巧、价值系统等,在价值系统中当然亦可包括审美价值,而文艺美学则应与一般文艺学不同,应更专注于研究文艺作品的审美价值,并深化关于文艺作品的“美”及相关的美学问题。
第二,既然文艺美学要研究的是文艺作品的美,就要进一步深究:到底何谓文学艺术的美?又何谓文学艺术的丑?如以能否给人心神愉悦的标准判断,文艺作品中的美当是源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作品中表现的原本就是自然与现实中那些美的事物;二是作者肯定性、赞美性的情感倾向;三是作者的艺术化能力,即如同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所说的,美的艺术的优越性在于“它美丽地描写着自然的事物”。根据这三个方面,文艺作品中的美与丑,会有如下复杂情况:同是自然与现实中的美,在文艺作品中,会因作家、艺术家“美丽地描写”而益生美;亦会因作家、艺术家艺术才华之不逮而败坏其美;同是自然与现实中的丑,会因作者肯定性、赞美性的情感倾向及“美丽地描写”而生出审美价值;又另有一些事物,如蛆虫、尸体、血腥暴力、屠戮残杀之类,因难以投入作者的肯定性、赞美性情感,故而无论作家、艺术家如何“美丽地描写”,恐也难以叫人“心神愉悦”,但正如美国学者丹托所说的,这类“不一定是美的”艺术,同样可能是“好的艺术”。
第三,要加强对不同门类文艺作品审美特征的研究。如以语言为媒介的诗歌、小说之类,缘其语言符号的灵活性、抽象性及自由表现性,会创造出诸如李白“白发三千丈”、李商隐“望帝春心托杜鹃”之类无法诉诸感官,无法像造型艺术、表演艺术那样直观,却有着决定了文学艺术独特生命力,造型艺术、表演艺术无法替代,能够给人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及更多自由想象之欣悦的审美效果。同是语言艺术,重在抒情的诗歌与重在叙事的小说,其审美特征又有差异,诗歌重在以意境感人,小说则主要以形象感人。与语言艺术不同,在综合性的舞台表演艺术中,现实中的丑陋、邪恶人物或凄惨的场景等,会因演员的高超演技而博得观众的喝彩。
法国美学家杜夫海纳在《美学与哲学》中曾这样谈过文艺作品审美价值的生成特点:“我们必须做到集中注意力于作品本身,并且以无利害的方式去欣赏它,玩味它。也就是说,除审美兴趣外,不为其他兴趣所动。”杜夫海纳所说这样一种纯然静观的审美状态,可能更适于形式美感更为突出的造型艺术,而对于语言媒介的小说、诗歌之类时间艺术,就不易做到。可见,只有着眼于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特征,相关的艺术门类的美学研究才能更为深入,否则,就易导致肤浅化与普泛化。就笔者所见,吴功正先生的《小说美学》,堪称是一部真正的“小说美学”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作者扣住小说家的审美感知的整体性、审美情感的典型性及典型人物这一基本审美范畴,比较充分地阐明了小说美学的相关问题。但其中的有些论断,如“小说美学作为艺术美学之一种的审美本质,它是再现又是表现,既有造型性又有表情性”,“小说是在主体和生活结成的审美关系中进行审美创造”,“小说美学的特殊本质是,主体对生活的认识在审美中进行”等,也因其道理的普泛化,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其特定的“小说美学”内涵,影响了其学术深度。
经由上述分析,我们或许可以更为清楚地意识到:只有进一步明确文艺美学的研究视点、研究目的及研究方法等,深究何谓文艺作品的“美”,以及不同艺术门类的审美特征,切实抓住文学艺术中的美学问题进行研究,才能更好地避免美学与文艺学之类研究的重复与缠绕,才能使美学对文学艺术的介入更富有学术增值之效,才有助于回答原有文艺理论难以回答的某些问题,也才能有助于美学与文艺学自身的丰富与发展,有助于人们的审美能力与作家、艺术家创作水平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