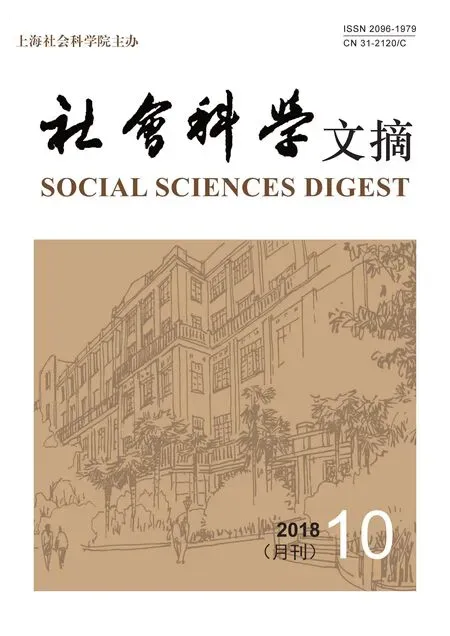中国哲学研究的世界视野与未来趋势
在全球化背景下,重新思考并深入阐释中国哲学的思想特质、当代价值和未来趋向是中国哲学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主讲者与评议人就此深入探讨了中国哲学何以是一种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梳理了其思想渊源、经典文本、核心命题和发展逻辑,阐明了中国哲学在人类遭遇文明困境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在此基础上力图结合全球文化的最新发展,思考当代中国哲学如何实现方法论转型,如何解答遭遇的现实问题,如何开拓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视野,并向世界传达积极的、开放的、多元的、自省的文化信息,来彰显出中国哲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进而指出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世界文化之立法的积极参与者,它对于理解人类历史、思考人类文化的未来发展、重塑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杜维明:作为全球性论域的“精神人文主义”
“精神人文主义”是一个正在涌现的全球性论域——当然,我提出的是扎根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在宏观的视野上,这一思想关联着我们如何能够找到一条通向永久和平的道路、如何通过文明对话达成文化谅解、如何与地球形成一种可持续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有赖于一种新的思考问题的方式,即一种新的思想的出现,这就是基于儒家传统的“精神人文主义”。那么,儒家传统是否拥有可以解答这些问题的资源?“精神人文主义”是否能够(抑或已经开始)在当今中国涌现?
“精神人文主义”这个论域首先产生于对启蒙问题的反思。在人类过去的几百年中,启蒙运动及其构想的人类整体计划,在历史上发挥了极大作用,财富和权利成为人们最关注的对象;而在启蒙运动之前人们所珍视的那些生活中重要的东西,则不再被关注。由此,世俗的人文主义事实上成为了主导世界的意识形态。所以,我们亟需在启蒙运动之后,对它带来的诸多不良后果作出反思。这些不良后果包括:带有侵略性的人文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过强的欲望以及占有性的个人主义,等等。“精神人文主义”则倡导“天人合一”的理念,要求对天敬畏、对地球尊重和爱护,进而建立一种互相信赖的社群,并以天下太平为文明对话的目的。总之,“精神人文主义”特别强调和解与和谐的重要性。儒家思想认为,“和”的对立面是“同”,而“和”的前提条件是“异”;这种认识与近50年来兴起的女性主义、环保主义、多元文化论等所提倡的观念有不谋而合的地方。
这样一种人文主义的出现,是我们设想“一个真正意义上永久和平的世界能否出现”的先决条件。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具有各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中国的、印度的、希伯来的、希腊的……,它们都提出了与现代的哲学、宗教、文化有密切关系的理念。而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全球生态环境失衡、世界社会秩序重组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的精神文明都需要经过一个重要的转型,以促成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的出现。
每个人都可以信奉不同的哲学理念、信仰不同的宗教、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是每个人其实都面对着当前世界的共同现状,也就是我们整体人类所遭遇的存活困境。这就要求我们除了有一种特殊性的背景外,还要有一种站在人类高度的思考。所以,真正能够指引我们在21世纪生存并持续繁荣的思想,应该可以拓展我们从启蒙运动以来被狭隘化的心态,而获得一种更加深沉厚重的道德积蓄。其中最低的要求是,我们要能超越我们这个时代各种狭隘的特殊主义——世俗的人文主义就是其中一种;在世界各地正在兴起的国族主义、民粹主义也是其中的典型。
我们作为中国人,要想探索一种新的思想,不能脱离自己的传统。一种在中国兴起的人文主义,一定天然地与中国的儒家、道家有关系,否则它将缺乏深沉的思想根基。而且,只有具有这种深沉的根基,它才能带给人们以当今这个时代所最缺乏的敬畏感。我们常说,年轻一代迫切需要敬畏感的培养,即对天地自然的敬畏、对超越财富与权利的整体人类精神世界的敬畏;但如果这种敬畏感没有扎根于本民族文化之中,那么它是很难真正产生作用的。
我所提倡的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作为一种面向未来的、实现人类持续繁荣与昌盛的渠道,将有助于各种思想、宗教、文化传统发展出真正的公共意识,以解决整个世界和人类所面对的困境,而这也将有助于世界各国关系的改善。因为这种人文主义,要求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融通、互信与了解,这是对他者的一种尊重,也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整体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文明体,通过不断重新发现、重新修复、重新建构自己,进而更新了自己。也就是说,中国文化不是过去和历史,而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大传统。我们都正在参与这样一个工作。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人发现了一种能与世界分享的重要的意义资源与宝藏,它在中国还活生生地存在着。
2001年我在联合国参加文明对话的时候,孔汉思教授曾提出将基督教的“己所欲,施于人”作为人类在文明对话中的最基本共识,我在原则上同意他的意见的同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更适合作为文明对话的基础。我当然同意将自己认为最好的理念与他者分享,也希望他者可以接受,这是一种非常好的利他主义;但是如果我过分执着,则会认为他者理应接受,倘若他者不接受,我不会认为自身有问题,相反会认为他者对我了解不够,从而会用一种强有力的方式令他者接受,这样就会引发各种各样的冲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表面看虽然是一个消极语言,但其背后却蕴含着积极的因素,这就是了解他人、尊重他人、承认他人、互相学习、互相参照的精神;由此出发,文化沟通、文明对话就成为真实可能的。应当说,这种价值虽然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儒家话语提出,但它绝不是儒家独享的价值,也不是中国人独享的价值,而是达致真正的互惠沟通的道理,是人类遭遇目下世界困局时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于很多价值的理解和西方不一样,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看来,正义的价值和自由一样重要;同情比理性更有必要;人的责任,特别是一个人对家庭、社会、人类的责任,比权利更重要;礼治比法治更为基础;社会的和谐比个体的发展更优先;等等。而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则要跳出一种狭隘的、武断的、过分简化的处理方式,来建设一种具有包容性的人文主义。所以,基于儒家思想的“精神人文主义”要建构的是一种可以容纳众多重要价值的人文主义:我们既应注重关系、注重和谐、注重人对社会的责任,同时也应注重自由、注重法治、注重理性。
我们正处在一个多元现代化的世界,这个世界不仅有西方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也有中国所代表的、印度所代表的、非洲所代表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因此,我们需要对其他文明进行了解、学习,其目的并不是要放弃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而是要把我们的根源性、特殊性扩大,扩大到可以包容整体人类。因为只有能够包容,才可能逐渐成为人类都认同的一种真正意义的人文主义精神。
在我从事文明对话的过程中,我发现儒家传统中的很多内容,不仅是关于地球的,而且是关于整个宇宙的。如孟子所讲的“天”、宋明理学所讲的“天理”,它们乃是从宇宙的角度来关怀人类,而这种关怀可以和世界各个文明发展出来的重要的“精神人文主义”相配合,以构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未来的“精神人文主义”。也就是说,每个人在自己可以扮演的诸多独特的角色之外,还有一个无法选择的根本——每个人都是人。而我所提倡的“精神人文主义”,就是试图从这个角度立论的。
目前,我对“精神人文主义”形成了一个框架性的认识,谨提供给大家,作为我的一个结论。作为一个包容而综合的人文主义,“精神人文主义”分为四个不可分割的侧面:第一是个人,指个人的身体、心知、灵觉和神明这四者的融通;第二是个人与他者、与社群之间的健康互动,所谓社群包括家庭、邻里、社区、城市、国家、世界乃至更大的宇宙;第三是人类和自然世界的一种持久和谐;第四是人心和天道的相辅相成。一般我们思考人文主义时只考虑前三个侧面,但真正的“精神人文主义”还应该包括人和天道的关系问题。总之,现代中国除了给世界带来政治、经济方面的新道路外,还应当在文化方面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这个贡献所带来的成果当然并不是中国强迫全世界接受的,而是它更具有包容性、涵盖性,它是一条真正宽广的道路,能够让全世界的人都行走在上面。
安乐哲: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
我讲的主题可归纳为“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与趋向”,其中涉及中国哲学在世界哲学研究格局中的地位、现状和遭遇的问题。
美国哲学家杜威于1919年来中国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重建哲学》,这本书告诉我们:做哲学的人是有责任的,我们既要知道哲学家的问题,也要了解民众的问题。而中国古典哲学坚守的正是须臾不离日常生活的、知行合一的哲学传统。因此,美国的实用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有很多相通的地方,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关于“人”的理解。
杜维明教授提到,个人主义在西方已经变成了一种意识形态。因为是意识形态,所以西方始终以个人主义为本。但是,儒学和杜威则提出了另外一些观念来谈论“人”。
因此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也必须让儒学传统发出它的声音。而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在现在西方、东方的文化比较中,仍然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对称的情况。比如我们去北京师范大学的图书馆,无论是社会学、人类学,还是哲学、历史学等方面,都会有非常多的西方著作摆放在书架上;但在欧洲、美国的图书馆,中国最优秀的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几乎是没有的。
这涉及很多问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翻译中带来的误解。比如,在基督教的影响下,西方把中国的“天”翻译成Heaven;把非常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礼”——包含着丰富的历史、人文与哲学内涵的一个观念,翻译成Ritual;把“道”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哲学概念翻译成了Way。其实这些翻译和中国传统哲学究竟有什么关系呢?而这导致的结果,是中国的儒学、道家变成了西方的宗教,这使很多在西方研究中国哲学的人都感到尴尬。因为在现在西方做哲学研究的学者眼中,中国哲学不是哲学,他们常以为儒学、道家和西方的宗教传统是一类东西——而西方知识分子对宗教是没有多大兴趣的。
在中国也有类似的问题。在19世纪中期之后,中国、日本、韩国和越南把西方的制度、思想、文化等予以引进。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个现代主义的词汇被翻译成东方的语言。尽管当他们把philosophy翻译成“哲学”的时候,借用的是中国经典文化中的相关词汇,但其实它是一个新创造出来的东亚西方化的概念。所以有学者不支持用西方的概念结构来理解中国的哲学,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就等于把中国及东亚西方化了。再举一例,儒学在西方的翻译是Confucianism,这个英文听起来有点类似激进主义或者黑格尔主义这种词汇的感觉。可是儒学并不是一个教义性的学说,儒学是传统中国的精英阶层对优良文化的传承与提倡。比如,若一个儒者回到商朝的话,他就要接受以前的文化,同时还要面对所处时代的一些问题而对文化进行更新,另外还要再把这个文化传授给后代。所以,儒学并不是一种意识形态或主义,而是一个社会阶层对本文化传统的传承与更新的责任。
因此,如果在当下我们仍认为应对儒学有了解、有兴趣,并且认为儒学在未来仍有希望的话,我们就要有这样的问题意识:儒学对一个新的文化秩序应作出怎样的贡献?通过回看中国传统文化几千年的历史可以发现,它是一个融合性的、包容性的传统,并不是排他的。因此,我们在今日仍需要好好学习这个传统。
刚才杜维明教授提到“精神人文主义”,他特别强调“敬畏”这个维度。的确,儒学不是宗教,但是它又有宗教性,它和宗教感其实是联结得很紧密的。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每年春节的时候,都要坐火车回家与家人团聚,这是不可理解的。但是对具有儒学传统的中国人来说,这其实是非常有宗教感的一种行为,是用宗教外的一种方式把大家联结在一起。所以,我们还应该学习传统中国表达宗教感的智慧。因为在西方和“人”相对的God概念,在中国是没有的,但是传统中国也能产生浓厚的宗教感。这依靠“孝道”的概念。这一概念在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西方伦理学中是缺乏的,儒学可以对之作出贡献。
倪培民: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
杜维明教授和安乐哲教授的演讲有三个共同点:(1)他们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儒家传统放到历史和全球的时空坐标上来看;(2)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能够为世界作出什么贡献这个问题上;(3)他们都认为这种贡献并不局限于哲学,而是对人类的精神文明,乃至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的贡献。
这三个共同点,体现了时代的转折。大家知道,中国哲学经历了一个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大讨论阶段,在很长时间内,人们一直在纠结着、讨论着中国哲学有没有合法性。现在这个问题本身产生的时代背景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今天我们谈的不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这个概念底下讨一个合法定位的状况,而是中国哲学已经成为世界哲学、世界文化之立法的一个参与者。从合法性到立法则这样一个转折,表明中国已经在积极地考虑如何对世界文化作出贡献了。
如果说我们以前是以西方的概念来看待中国的哲学思想,甚至是以西方所提出的问题来定义我们的学术思想的话,那么在今天,已经有不少人提出要有“以中释中”的气魄和勇气,而且不只是“以中释中”,还要“以中释西”。的确,在未来时代,非常需要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来面对我们这个世界所面临的问题、面对西方学术所面临的问题,并帮助西方哲学、西方文化克服它的局限性。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和哲学也会得到其新生命的展现和提升。
杜维明教授强调的“精神人文主义”,有着非常明确的时代背景之考虑。我们知道,自近代以来,这个世界一直由世俗的人文主义占据着统治地位。而在当下,我们看到了很多宗教的反弹,这是对精神性的一种渴求,但是有些反弹走向了极端主义。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建立人类的精神世界呢?在这一点上,安乐哲教授也有同感,他认为我们要建立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宗教联合体。不过这两位教授有一个微妙的区别:杜教授更多强调东、西方的共同点,并强调人要有一个超越性的层面;安乐哲教授则强调中、西的区别,同时他更强调内在性,而不主张建立一种超越性。
安乐哲教授还提到了中、西之间的不对称现象,这的确是一个非常严峻的现实。怎样面对它呢?我认为,我们现在既要研究中国传统的历史、文化和哲学,同时也要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去帮助世界其他地方的人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与哲学的价值。只有让中国文化充分参与到整个世界文化的构建当中,才能发挥出它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