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慈欣没有改革开放我可能是一名矿工
| 文 · 李晓蓉 张菡

“我的生命中有条很重要的线,那就是1978年。
由此,生命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前,一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这两部分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2018年9月中旬,刚刚结束外地考察,还没来得及回家的刘慈欣便赶赴北京,与多位诺贝尔奖得主和来自国际科学理事会等22个国际组织及37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们共赴一场全球性会议之约。会中间隙,刘慈欣在其下榻的酒店接受了我们的专访。
“改革开放给了我一个全新的人生,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的生活肯定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比现在差得多。”起初略显内向、腼腆的刘慈欣似乎被这个话题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能不能活到现在都不知道。”
当我们把时间拨回到40年前的1978年,我们发现关于科幻作家刘慈欣的故事才真正被打开。
改革开放 命运转折的分水岭
那一年,“60后”的刘慈欣刚刚15岁。按照改革开放前的生命逻辑,作为一名煤炭工人的子女,如果没有高考,他很可能要接父亲的班,成为一名煤矿工人。
以当时的井下条件而言,采煤是一项“高危”作业,不仅没有自动化的机械,甚至连人身安全都不能保障。在刘慈欣的记忆中,父亲下井受伤是常有的事。
“父亲的经历告诉我,你不可能在井下干了30年一次伤都没有受过,不可能。”刘慈欣自述,改革开放40年,最主要的影响还是让他看到了外部的世界,并且接触到了现代文明的方方面面,甚至让他有机会走出国门去体验外面的世界,而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让他接触到了科幻文学。
“假如没有改革开放,科幻小说是不会在中国再次出现的,中国也不会有科幻文学。”刘慈欣表示,从大量接触科幻作品到成为科幻迷,再到成为科幻作家,时代的烙印不可谓不强。
“它让我们由一个生活相对贫乏、贫困的时代,走进到一个生活迅速走向富足的时代,这是每个人都能感觉到的。由一个在文化上相对封闭的国度走向一个开放的、能够面向世界接受所有信息的时代。”刘慈欣感慨。
1989年,刘慈欣第一篇科幻文学作品的诞生标志着他正式从读者向作家身份的转变。在此后的写作生涯中,他的数篇作品问世,其中包括7部长篇小说、9部作品集、16篇中篇小说、19篇短篇小说,以及部分评论文章。
在刘慈欣众多的优秀作品中,《三体》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作品通过两个文明的碰撞与博弈,揭示出人性的深刻与复杂;通过对宇宙规则的思考与探寻,展露出未来的冰冷与残酷。以“硬科幻”为核心,书写了一部从20世纪60年代到宇宙终点的“未来史”。
《三体》的成功使其收获了一批“大咖粉”,比如腾讯的董事长马化腾、小米的董事长雷军、360的董事长周鸿等。
《三体》大热 源于快速现代化进程
“快速现代化进程发展到今天,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三体》大热背后,有着多方面的原因,但在刘慈欣看来,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到了一个快速现代化进程之中。
刘慈欣指出,这种改变让人们以更广阔的视角看到了外部世界,进而让人们每天所关注的不只是周围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东西,也关注一些更远、更广泛的东西,“从身份认同来说,他们不仅仅把自己当作中国人,而是当作全人类的一员。”
在刘慈欣看来,这种改变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国社会和人民生活有一种强烈的未来感。“以前生活变化不大,人们对未来关注也不多,但是今天的生活发生着快速的变化,这个变化日新月异。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会是什么样,人们就会很感兴趣,未来充满了吸引力。”刘慈欣指出,虽然这个未来不全是正面的、也面对着很大的风险、有很多的陷阱,但是它也有着同样多的希望让人向往。
谈及《三体》的创作灵感,刘慈欣表示,除了对三体问题的震撼,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他看来:外星文明其实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外星文明并不是一件虚无缥缈的,只属于未来的事情。外星文明其实是我们人类文明,甚至包括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所面临的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刘慈欣感慨道,人类对目前社会所面临的比如气候变暖、环境污染、恐怖主义等都或多或少有一点准备,但对外星文明却缺少应对机制。
刘慈欣认为,外星文明一旦出现,对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而目前面对这么一个“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人们的冷漠也是难以想象的,国际社会也并没有给予相应的重视。
“没有一个国家或者政府哪怕成立一个象征性的机构,来应对外星文明,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提出这方面的研究。”刘慈欣指出,各个大学里面关于外星文明的学科亦相对较少。种种“冷漠”让他吃惊之余,也萌生了创作的冲动。
这种忧虑在谈及当下前沿的科幻文学时,表现得更为突出。
科幻作品变“内向” 探索的热情在减退
2015年8月23日,凭借作品《三体:地球往事》,刘慈欣荣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故事奖。作为第一个获得此殊荣的亚洲作家,刘慈欣在蜚声海外的同时也将这个名声在“外”的国际性大奖拉进了中国人的视野。
“雨果奖”有着科幻界“奥斯卡”的美誉,与“星云奖”并称美国科幻界的最高奖项,其获奖作品历来都是科幻文学的标杆,获奖作者更是堪称世界顶级的科幻大师。
但是近几年来,雨果奖的获奖作品在刘慈欣眼中失去了原有的味道。在刘慈欣看来,美国科幻界,这个科幻小说生长的沃土正在面临着看不见的“后退”,美国的科幻变得越来越“内向”。
面对我们的镜头,刘慈欣坦言,“科幻文学变得至少对我这样曾经的科幻迷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已经不是我当初喜欢的科幻小说了。”
2016年-2018年,黑人女作家N.K.杰米辛(N.K. Jemisin)接连3年斩获“雨果奖”,她的获奖作品《破碎的星球》三部曲描绘了一部与压迫力量斗争的史诗。其中的故事情节反映了一系列美国社会中存在的现实问题,比如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族群压迫。
在刘慈欣看来,近些年来,雨果奖的评审标准越来越关注于人的自身,它的目光不再投向那些星辰大海,不再是人类探索宇宙的激情。“这么变化有它的理由。传统的科幻小说也一直在创作,但是它无法进入美国科幻的主流了。”刘慈欣表示。
另一方面,现代工业革命,特别是信息时代的来临使得大量原本只能存在于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被拖拽进了现实,科幻小说的“神秘感”在一天天地消失。
谈及“90后”甚至“00后”这些新一代群体,刘慈欣感慨,他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了科幻氛围的环境中。“科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或者说作为一种文化,甚至作为一种商业标签,他们一生下来就很熟悉了。”新一代眼中的科学变得不再冰冷而遥远,它不再是纽约时代广场那个光鲜亮丽的广告牌,而是一小块可以捏在手中任意把玩的信息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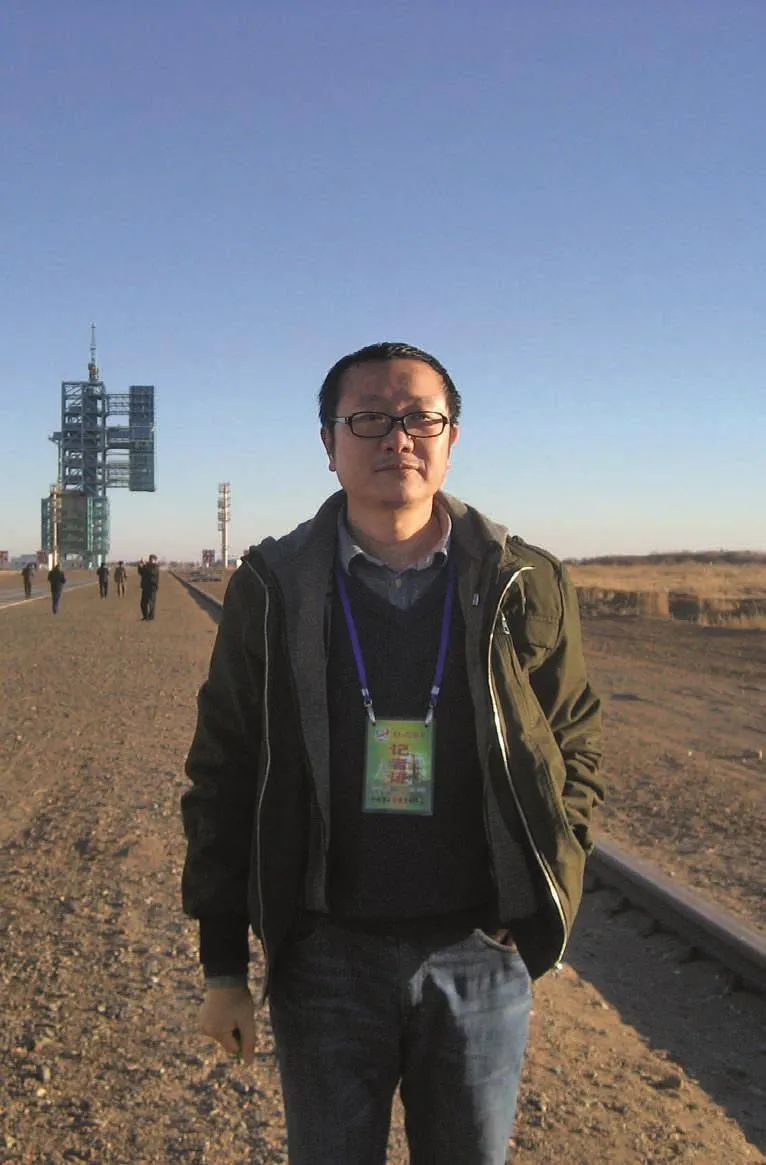
刘慈欣表示,神奇感一旦消失,对科幻的打击是致命的。虽然科幻文学界也采用各种方法来避免这种影响,但是效果并不好。“我认为科幻作为一个文学题材在新一代人中可能会渐渐衰落,但是科幻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甚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会比以前更广泛被人们所接受。”
此外,谈及可能来临的AI、VR时代,刘慈欣在肯定技术发展带给人类舒适便捷的同时,也表现出了一些担忧。
“VR和AI结合起来会让我们越来越随时随地去体验各种远距离的场景,最后的直接结果很可能就是,我们一辈子呆在家里不用走出家门,我们就可以体验遍全世界,也会让人给我们送来生活必需品。”他同时指出,科技的发达会反过来蚕食人的主观能动性,这种社会剥离感的培养会让人类变得越来越内向,失去向外太空、向宇宙的开拓精神和探索欲望,在刘慈欣眼中,这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可能是很致命的。
“人的惰性是很强的,如果我们不走出地球向太空中寻找自己新的生存空间,短时间看一两千年内甚至1万年内问题不大,再往长远看肯定是人类文明的一条死路。”

未来无法预测 要让思想保持活力
在我们的访谈中,关于未来,刘慈欣出现最多的词汇是“无法预测”“很难预测”“预测未来几乎是不可能”。
刘慈欣称自己从来不做30年以后的打算,因为这个时代变化得太快了,别说30年以后,就是10年以后会变成什么样都不得而知,这种打算很可能是白费力气。“10多年前我每天趴在电脑面前,我理所当然地认为10年以后我周围的电脑更多了,面前的屏幕更大了,我每天趴在电脑前的时间更多了,但事实上不是这样,移动通讯代替了固定的网络,手机反而变成了个体的一部分,所以这些东西真的很难预测。”
在他看来,未来无法预测的另一个原因是在目前的技术发展过程中,很多关键点都面临着质的突破,任何一点突破都极有可能会改变目前的生活状态。
刘慈欣列举了他认为5年到10年后能够真正改变人们思维和生活的几项关键技术,如人工智能、VR、还有正在发展的生物基因等。但具体是怎么改变的,科幻作家的思维无法给出答案。
未来虽然无法预测,但作为一个个体如何跟上这个时代,更好去适应未来的发展,刘慈欣指出,首先要保持自己思想的活力。
“传统的知识,依靠记忆获得的知识越来越不重要了。”想象力以及创新力正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要让自己适应这种趋势,让自己的学习方式和思维结构顺应这样的趋势”。
此外,在刘慈欣看来,适应未来生活最大的障碍,比知识障碍更大的是否定人性的变化。正如《三体》中所谈及的: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在他看来,随着文明的发展和技术的突破,人性会在此过程中不断推演前进,而世人眼中的衡量标准亦会发生变化。如果不能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事物,总是停留在过去的偏见中,以蒙昧代替科学,以主观代替客观,拒绝任何改变,那么结局只能走向灭亡。
“未来好与不好,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非正义,这些评价是要发生变化的,这个变化是最难让人接受的,但它还是会发生。”

如今虽然要在各地不停行走,但刘慈欣表示,并不会将自己的家搬到诸如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还是会留在山西阳泉这个小城。他给出的理由是,写科幻并不一定要在最繁华的大城市,比如身为科幻界三巨头之一的阿瑟·克拉克就在远离都市的斯里兰卡小渔村写下了许多气势恢宏的科幻名篇。在一个偏僻的地方,能够抛开一切杂念和扰动,全心全意地去思考宇宙。刘慈欣认为,科幻作品和现实还是有一定距离的,前者往往是作者一个人意识的反映,而后者不是,它是整个社会共同作用的产物,其中不可确定的因素太多。“科技不以个人的意识为转移,而科幻反之。”刘慈欣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