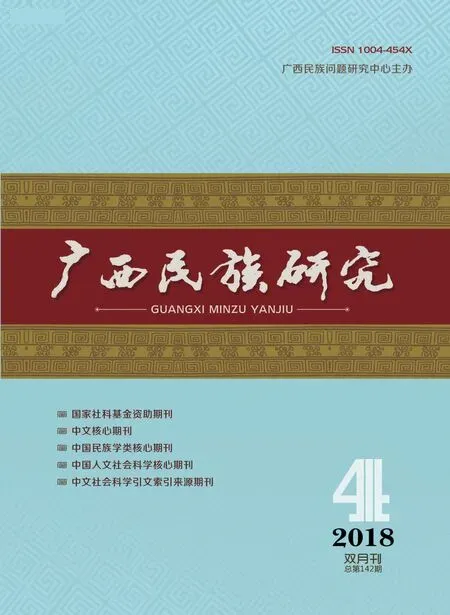明清贵州“土人”问题考释
张洪滨
“土人”一词并非明清时期才有,亦非只有贵州独有,只是因明清贵州史籍中记录了大量的“土人”信息才引起诸多学者的注意。关于贵州“土人”的研究,以李汉林、杨然、李良品等人的研究为代表。李汉林认为,清代部分方志及各版本《百苗图》中所记载的“土人”是今天土家族的祖先,他们在历史上的活动空间一度到达今黔东南、黔南及黔中地区,至清中后期又逐渐退却到今黔东北一带。[1]李德龙亦认为《黔南苗蛮图说》中的“土人”应为土家族,并认可李汉林之说。[2]89李良品则大胆地指出:“明代及清前期贵州方志中的‘土人’,主要指黔东及黔东北的土家族先民;清代中后期及民国贵州方志中所说的‘土人’,主要是指散居在黔中地区的土家族先民,但所载内容也包涵了黔东北土家族先民的基本状况。”[3]可见,李汉林与李良品二人对于明清时期土家族先民的活动空间持有不同的观点,前者认为是活动空间的退却,而后者认为是扩散。此外,杨然对于贵州“土人”分布范围的研究更为广泛,他认为史料中记载的黔西北地区的“土人”和今天穿青人有着极深的渊源关系。[4]18关于“土人”的身份和概念,杨然认为“土人”并非属于同一个族体,而是一种泛称,所谓“土人”应该是“汉化的土司治下的比土司本身汉化程度低,却又比其他少数民族汉化程度高的土著,也即是史志当中所谓的‘熟苗’”。总之,诸家所言各有其理论依据,但又各持不同见解。笔者以为,上述方家对于土人身份、族源、分布区域等方面的论证存在诸多疏漏,对于“土人”概念的由来及明清时期土人群体的发展变迁过程认识不够,有待进一步探讨。
笔者认为“土人”有泛称和专称两种概念。就全省而言,土人散居各处,并非同一族类,因而是泛称;而就某一地区而言,土人在当地是有独特民族特征的群体,是专称。按贵州明清方志所载,“土人”群体主要分为三类:一是明代早期方志中所载的思州、思南、铜仁各府之“土人”及“土人”群体中的“思播流裔”;二是明初以前迁徙或流窜到黔中及黔西北地区的部分外省汉民,他们与当地土著人通婚,居土日久,成为“旧民”,形成有别于“屯堡人”和“苗蛮”之外的特殊群体;三是指罗罗,即今彝族人的先民,嘉庆《仁怀县草志》载“土人,在大定者曰猓猡,本曰卢鹿……仁怀有之”[5]17。可见,贵州的“土人”在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族属与含义。
一、黔东“土人”的由来及民族属性
明清贵州史志多记载有“贵州土人,所在多有之”的现象,并重点突出黔中与黔东南黎平曹滴司“土人”的生活现状。关于这类“土人”引起了许多学者的探讨和争论。李汉林认为,“土人”一名出自土家族自称“毕兹卡”的意译,[1]130贵州明清史志中出现的“土人”一词是指今土家族人的先民。笔者并不完全赞同此观点。明代早期成书的贵州省方志的体例是以各区域为章节来排列的,这便于展现出各府、州、卫所之间的社会差异。其中“土人”一词多出现于黔东思州、思南、铜仁、镇远、黎平等府的章节中。相较而言,现土家族群体的分布区域主要集中在湘鄂渝黔交界地区,而明代方志中所记载的“土人”生活区实际上已远远超出今日贵州省土家族的活动空间。李汉林认为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明清以来土家族先民的不断迁徙和被同化。这一解释显然过于牵强。李汉林还提到,明清史志中多次记载黔中地区存有大量“土人”,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两次民族识别考察中却未发现当地有真正意义上的土家族,李氏言论难以自圆其说。以笔者看来,李汉林严重低估了“土人”族属来源的复杂性,将明清史志中出现的“土人”全都看作是土家族先民,这显然是不客观的。
关于黔东土人的民族属性,有必要做深入探讨。贵州“土人”一词较早出现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 (以下称《新志》)一书。该志虽成书于明中期,但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弘治以前旧志版本的内容,力求“旧志所载尚循其常,今据实书之,不敢以厚诬也,其夷俗有未变者则仍其旧”[6]3。因而此志关于“土人”的记载,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但不可否认的是,《新志》中关于民族风俗的记载较为简略、笼统,尤其是没有讲清楚“土人”的民族属性和分布特点,因而很难对“土人”的族属来源作出判断。《新志》卷五《镇远府》篇载:“境内夷民种类不一,其居山野者曰洞人,曰杨黄,曰仡獠,曰犵头,曰沐獠,曰生苗,曰熟苗。”[6]59可见,《新志》并没有将“土人”归为“夷民”一类。通过该志零散的史料信息,笔者总结出“土人”明显是一类汉化程度较高的群体,他们通汉语,稍知礼仪,多居住在河边村寨,有自己的风俗和禁忌,不但能入穴采砂,还懂得挖井取水。从某种意义上讲,“土人”的生产、生活水平已远超本地普通“夷民”。笔者认为,《新志》中之所以没有记载“土人”的族属情况,很可能是当时的地方官员并不十分了解他们的来源,因而只能根据旧志所载的相关信息进行抄录。这也是符合《新志》编纂的谨慎原则和求实态度的。
相比于《新志》,嘉靖《贵州通志》对于黔东“土人”民族成分和生活习俗的记载就更为具体了。该志卷三《风俗》篇记载了许多关于黔东地区诸长官司治下“土人”的信息。如:
①镇远府邛水司:土人性丑陋,好斗战,出入不离刀弩。衣服婚丧略同金容、金达之俗。每三年杀牛一祭先祖,邻境寨峒男女会饮。
②铜仁府铜仁司:土人亦杨黄之属,服饰近汉人,语言莫晓,务农为本,出则以牛载行李,有疾病则杀牛羊犬豕以禳之。婚姻论贫富,以牛为财礼。祭祀用鱼为牲,葬置棺,俗重山鬼。每年有把忌,饮食、衣服、喜怒哀乐亦多避忌,号为青草鬼,稍有犯者多不利于人。
③铜仁府省溪司:土人离治,远居幽谷深箐之间,常畏虎狼。昼耕则持刀弩往,暮则合聚同归。有疾病徙宅避之,疾愈方回。送死杀牛祭鬼,束薪而葬。
④铜仁府乌罗司:土人亦杨黄之属,言语服饰与省溪、平头二司相似。
⑤黎平府曹滴洞司:土人,出则男负竹笼,妇携壶浆同行。葬以鸡卵土地,掷卵不破者,曰吉地葬之。
根据引文所述,嘉靖时期的“土人”有许多属“杨黄”族类,他们在饮食、服饰、生产、丧葬等方面沐染华风,社会发展水平显然要高于普通的“生苗”。“杨黄”在镇远府施秉县为“思播流裔”[7]269,而清代《黔书》亦记载:“土人,在黎平府曹滴司者,多思、播流裔。”[8]48这就提醒我们,嘉靖《贵州通志》中所记载的“土人”多属“杨黄”,而镇远、黎平等地的“土人”实质上也是“杨黄”之后裔。而在更早的成化年间,张瓒在经过贵阳东北方向的白泥长官司地时,就发现当地生活有大量的“杨黄土人”。他在自己的笔记中指出:“土人,号杨獚,多住山趾,近驿皆偏桥、兴隆、黄平三卫所屯田,颇为富庶。”[9]138这说明“土人”在明中期以前已经开始出现在播州、镇远交界地区。那么白泥地区的“土人”是否也属于“思播流裔”呢?笔者认为这是有可能的,而且他们很可能是由贵阳周边的黔中一带经湘黔驿道迁徙而来。
许多学者因为没有搞清楚“思播流裔”与“杨黄”之间的关系造成了对史料的误解。如李良品直接借用王景才的观点,称“思播流裔”表示“土人”为宋、元以来思、播二土司治下的土民。[3]160笔者认为,所谓“思播流裔”是指“杨黄”群体的某些部族分支,他们的先民是在元代以前由其他地区迁徙而来。元代思、播二宣抚司地范围极广,包括了今黔东北、黔东南、黔中等大部分地区,大体上与明代史籍中所载“土人”的分布空间相吻合。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招捕总录》 《元史》及《新元史》等史书中搜集到了关于“杨黄”的更早记载。元大德五年(1301年),雍真葛蛮土官宋隆济叛,“丙戊,宋隆济率猫、狫、紫江诸蛮四千人攻杨黄寨,杀掠甚众”[10]435。土官宋隆济因不堪忍受元政府的剥削而被迫起义,他之所以要攻掠“杨黄”村寨很可能是因为当地“杨黄”族众顺从了元朝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杨黄”势力逐渐成为黔中诸土司排斥的对象。泰定元年(1324年)春正月,“戊申,八番生蛮韦光正等及杨黄五种人氏,以其户二万七千来附,请岁输布二千五百匹,置长官司以抚之”[10]643。显然,黔中地区的杨黄群体不但数量庞大,①尤中认为:“宋隆济军事活动的区域在今贵阳东部、北部的开阳、修文、息烽、贵定一带。在这一带地方,多处有杨黄寨,即有佯僙村寨杂于仲家、仡佬、苗族之中。”详见尤中《中国西南的古代民族》(续编),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61页。而且已具备较高的社会生产水平。元后期,随着王朝边疆统治力量的衰弱,“杨黄”势力在黔中地区失去了靠山而背井离乡或许正是部分“杨黄”的无奈之举。再从明代史籍中黔东地区出现的大量“杨黄”来看,他们或许有部分支系是来源于本地土著,但应该也夹杂了许多从黔中地区迁徙过去的“杨黄”,即所谓的“思播流裔”。相比于土著“杨黄”,属于“思播流裔”类的“杨黄”显然汉化程度更高。在嘉靖时期的镇远府施秉县,“杨黄,思、播流裔,其俗遇元宵、端午二节临近,寨洞男女期会,架秋千为乐,流风尚在”。另一方面,从明清史籍中出现的“土人”或“杨黄”来看,他们大多集中分布在贵阳至铜仁一线,这种有规律的民族分布现象应该不只是一种简单的地理空间上的巧合。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搞清了明清史料中黔东“土人”的民族属性,亦基本考证出“杨黄”由黔中地区向东部地区迁徙的史实。这个结论基本否定了许多学者提出的“土人”作为土家族先民由黔东北地区向黔中一带迁徙的观点。实际上,由于这部分“杨黄土人”本身就是汉化程度较高且有着一定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群体,明清时期他们不断地与当地的军事移民集团进行接触、交融,最后大多归于同化。清初贵州巡抚田雯言:“土人所在多有之。在广顺、新贵、新添者,与军民通婚姻,岁时礼节皆同。”至清末,曾在贵州任职达30年之久的桂馥更明确地指出,黔中地区的“土人”当时已经变成了汉人。[2]192不可否认的是,另有部分流寓异地的“土人”与其他土著民族交往更深,他们逐渐改变了自己的风俗习惯,最后被同化为其他民族。
二、贵州中西部地区“土人”与“里民子”的关系辨析
贵州中西部地区的“土人”在史志中出现的时间较晚,且常常与“里民子”“穿青人”等联系在一起。关于这些民族群体的记载,不仅表现出更多的汉文化特征,而且其由来也多与汉移民有关。李良品通过对明清史志中记载的“土人”与“里民子”相关信息进行分类对比,认为“土人”与“里民子”的来源没有关系。他还指出:“只要翻检涉及贵州全省的方志或道光《贵阳府志》,没有哪一部方志不是将土人与里民子分别叙述,因此土人与里民子是两个不同的人群集团。”[3]164-165在此笔者承认,即便是在各种版本的《百苗图》中,“土人”与“里民子”亦是作为两种不同的民族群体分别叙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史书中所载的“土人”多是指前文论述的“杨黄土人”,与黔中及黔西北地区“里民子”群体中的“土人”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族别,因而李良品对两者做出的比较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从史源学角度来讲,“里民子”一词最早出现于清乾隆时期的《黔南识略·水城通判》一文,其载:“苗有白儿子、倮罗、蔡家、仲家、花苗、披袍仡佬、里民子,族类繁多,男皆剃发,通汉语,颇知耕织。”[11]498水城厅始置于雍正十一年(1733年),至乾隆时期才有大批汉官、汉民迁入此地,因而时人对于水城“里民子”一族知之甚少,故只将其列于苗民一类,却并无过多解释。至嘉庆年间,李宗昉对“里民子”的解释就更为具体了。他在《黔记》中写道:“里民子,在贵阳、黔西、大定、清镇等处。男子多贸易,妇女穿细耳草鞋,勤俭耕作,闲则纺毛布作衣,爱养牲畜,常带入山做活,每岁节与汉人同。”[12]575至道光、咸丰时期,一些关于“里民子”来源的传说逐渐流传开来。道光《安平县志》的记载首先将“土人”与“里民子”联系在一起,其载:
土人,所在多有,县属西堡尤盛。相传为明洪武时屯军之眷属、亲戚,与屯军先后至者。因其居土日久,故曰“土人”,一曰“旧人”。一说“土人”,楚人也,元末从陈友谅反。及明太祖灭友谅,分兵制其余党,反者皆逃入夷蛮中,以避诛戮。一名“里民子”,衣尚青,妇人以银索盘头,与屯堡人无甚差异。(见《徐志稿》)妇女不缠足,男子娴贸易,耕作多妇人为之。称曰县民,以别于屯军也。岁时礼节,俱有楚风。[13]112
该段史料记载的是安顺府属安平县“土人”的族属来源及生活习俗状况,其反映的信息只能代表“里民子”在某个区域的部分群体的某些特征。因而,关于“土人”族属来源的记载,无论是“屯军亲眷说”还是“楚军避难说”都只能代表“土人”群体中的部分现象,不能以一概全。这也间接说明,“里民子”并非单纯的民族群体,而更应该是一种泛称。咸丰《安顺府志》载:“里民子,相传皆外省籍,其流寓本末无考。”[14]198可见,“里民子”是一类主要由外省移民构成的复杂群体。另外,明初移民因居土日久而俗称“土人”,说明这种称谓是后期得来,而并非始自明初,这与前文论述之“杨黄土人”在民族属性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再考虑到“里民子”一名的由来是在清雍正朝改土归流之后,那么这种“土人”的称谓亦很可能是伴随着清代大批移民的迁入而出现的。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里民子”都可能被后期移民或外来者称为“土人”,即“土人”只是“里民子”部分群体的另一种别称而已。除此之外,如光绪《永宁州志》、民国《贵州苗民丛考》等史志亦有关于“里民子”及“土人”信息的记载,但其内容与道光《安平县志》无甚差别,很可能是照抄而来。
三、黔北仁怀县“土人”概念的由来及变化
关于“土人”之来源,前两类常被诸方家争论探讨,而第三类却少有人关注或提起。仁怀之“土人”有着极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这关系到明代永宁奢氏土司在赤水河中下游地区的领土扩张。由于此话题与本文内容无关,故笔者在此不作详细探讨。实质上,乾隆年间贵州巡抚爱必达所著《黔南识略》一书就已提到仁怀土人,其言“茅台村地滨河,善酿酒,土人名其酒为‘茅台春’”[11]542。但是爱必达所言之土人显然不是专指“罗罗”,而应该是泛指当地土著居民。一是因为仁怀之“罗罗”(彝族)只分布于今仁怀县西南部的茅坝镇一带,不但数量较少,且与茅台村相去甚远。此外爱必达在仁怀县苗夷种类中提到有“倮 ”,但并未提及有“土人”。可见《黔南识略》中所言仁怀之“土人”不是指“罗罗”。如果再往前推,“土人”一词甚至可以追溯到明中后期。据仁怀合马镇马胡沟《罗氏家谱》 (1984年石印本)记载,罗氏先祖金旺于明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 因参与平播战争而留驻当地。时仁怀县汉土交错,兵民各司其职,该谱云:“明征播地,恩威相施。土人自治,以安边邻。异地军士,屯堡戍守。军务既战,平时耕耘。土流兼治,政归明君。”[15]57
“土人自治”是汉移民迁入仁怀之后的第一印象。时仁怀之“土人”依附于各里之土目豪强,自成体系,不与外来军士接触交流,堪称当时特殊的人文景观。而就“土人”来讲,他们主要有三部分构成:一是早期汉移民的后裔,二是部分汉化程度较深的“苗蛮”,三是早期汉移民与当地“苗蛮”相互通婚以后繁衍之后裔。此三部分群体在长期的接触交融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上层土目或族长为首的地方势力,此即是“土人”群体。因而,“土人”一词的得来与使用跟后期大规模的外地移民迁入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区有关,是后期外来汉民对于土著居民生活状态的客观认识。在此,“土人”含有“旧人”的意思,表示与新移民相区别。在乾隆前期成书的《黔南识略》当中有关于仁怀“土人”的记载,这说明在明清之际的150年间“土人”群体一直存在。在此期间,新移民不断涌入仁怀,并与当地“土人”进一步接触融合,致使“土人”群体发生变化。虽然汉、土居民不断加强交往和了解,但这些后期移民对于当地“土人”的身份隔阂依然存在。正如李德龙所说,人们对民族概念的认识、民族的自觉意识和民族的划分标准,会随着历史的进展不断地发生变化。[2]3到嘉庆时期,“土人”群体的民族属性就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甚至变成了“罗罗”的代称。
“土人”的概念为何在清乾嘉时期由“旧民”转变为“罗罗”,这是一个值得深究的问题。首先,仁怀地方政权在雍正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仁怀县署由县境北部之留元坝(今赤水市老城区)迁至南境生界亭子坝(今仁怀市中枢街道),①“雍正九年始,题请移县治于生界亭子坝”,详见嘉庆《仁怀县草志》之《城池》,第7页。此使得仁怀南部地区的广大“土人”直接转变为流官政权统治下的县民,造成了“土人”身份的蜕变。既然土人政治身份发生了改变,那随着新旧县民的不断融合,人们对于土人旧有的认识观念就逐渐得以矫正。其次,土人称谓在仁怀由来已久,人们对于土人的客观评价标准逐渐固定,而这个标准体现在样貌特征和风俗习惯两个方面。仁怀原先的旧民在乾嘉时期在样貌特征、生活习俗等方面已与新民无异,实际上已超出了“土人”特征的标准。再者,“罗罗”是土人群体的后来者,是在明末奢安之乱平定以后安插到仁怀威远卫辖地的。[16]210,237仁怀之土人“在大定者曰猓猡,本曰卢鹿,深目,长身,白齿,钩鼻,或曰罗鬼”[5]17。由此可见,在时人心目中,土人是有着特殊样貌特征的土著群体。
仁怀之“罗罗”在明末入籍仁怀以后,一直生活在今仁怀县西南端茅坝、龙井、九仓一带,与外人接触较少。基于这个原因,一直到民国时期,仁怀土人群体仍然存在。九仓镇曾有明代土官铁坟,墓主人为明代永宁奢氏土司的后裔奢宣谕,这在民国《续遵义府志》卷七《古迹三》中有记载。即“明奢宣谕墓,在仁怀县南一百三十里之排楼……镕铁铸其外,土人以‘铁坟’呼之,亦谓之奢宣谕墓。”[17]337因此,笔者推测仁怀之“罗罗土人”很可能来自于四川永宁,与黔西北大定府之“罗罗”无关。仁怀“土人”群体在清乾嘉时期发生了变化,但之后一直到民国时期,“土人”在当地专指“罗罗”,并得以确定。
从仁怀“土人”的概念由来及“土人”群体的变化来看,“土人”一词的出现与使用跟后期汉移民大规模迁入边疆地区有关,源于人们对于新旧居民的区别称呼。实质上前述两类“土人”称谓的由来也与此有关。所谓“土人”是一群与新移民交错而居的土著群体,并无民族属性上的分类与区别。土人群体不同于“生苗”,他们处于半自治状态,其生活的社会环境已具备了较高的物质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土人”群体亦不能等同于“熟苗”,因为他们的族属关系非常复杂。由于“土人”是一群依附于地方土目或豪强的群体,因而在客观上各地之土人群体表现出不同的地域特征。有些土目可能是“罗罗”,有些土目可能是宋元以前入黔的中原大族,因而其治下土人的开化程度也各不相同,这就造成了“土人”概念上的多样化和风俗习惯上的差异。因而,杨然认为土人是“汉化的土司治下比土司本身汉化程度低,却又比其他少数民族汉化程度高的土著”,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入清以后,随着王朝边疆统治力量的不断加强,原部分“土人”不断与后期移民接触交融,其原始特征不断退化,直至消失。而另有部分“土人”因长期生活于较封闭的社会环境中,鲜与外界接触,“土人”的身份和称谓一直保持到民国以后。
四、余论
明清贵州史籍中出现的“土人”一词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有着民族属性上的多元化,来自于外来移民对于本地部分土著民族的一种较客观的认识和区别称谓。总体说来,“土人”一词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土人”群体居土日久,相比于后期迁入当地的移民属地方土著。第二,“土人”群体大多构建起较独立的社会体系,个别势力弱小者或依附于地方土目豪强,或最终融入其他族群。但毋庸置疑的是,他们都曾属于一个有着鲜明社会特征的民族群体。第三,“土人”群体既有别于普通“苗蛮”,又不同于后期迁入的汉移民,但同时又兼具了两者的某些文化特征。换句话说,“土人”在生活习俗与文化水平方面有着较高的汉化倾向,但并未完全脱离“苗蛮”的特征和习俗。
对于后期外来移民而言,他们对于“土人”的认识和评判标准可能相差无几,但由于年代、地区等方面的差异,“土人”往往表现出不同的民族属性和文化特征。明清史籍中出现的多种“土人”群体,源自于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官民对于当地土著群体的认识评价,是贵州古代民族多样性的真实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