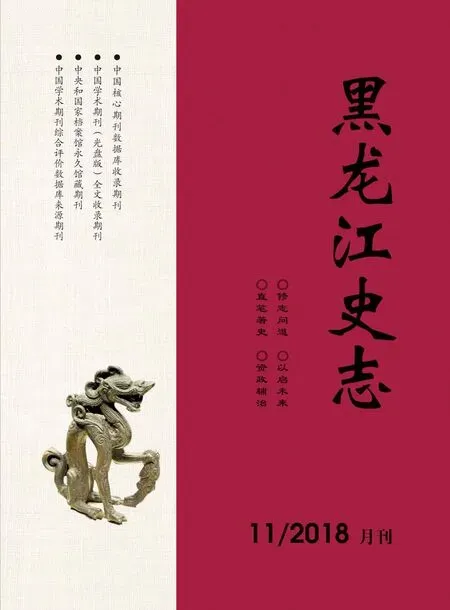甲午风云中的晚清外交
——基于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外交实践的考察
杨玉荣 龚 耘
(海军工程大学政治理论系 湖北 武汉 430033)
纵观人类历史,战争与外交结下了不解之缘。外交成败关系着战争发生、发展的全过程。甲午前后清政府外交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甲午战争的爆发与结局。目前,学界对于李鸿章外交思想的研究颇多,研究甲午战前清政府外交的文章亦有几篇,(1)但从国际化视域和整体的角度研究清政府外交与甲午战争相互作用及其成败教训的文章颇为罕见。然而,国际风云的变化多端,晚清外交的纷纭复杂,与甲午战争的烽火连天紧密相联。探讨二者关系,总结经验成败,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历史,把握现在,赢得未来具有重要意义。
一、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外交政策及其策略的实施
1840年鸦片战争打破中国国门后,清政府的外交政策与策略不断嬗变,逐渐融入近代外交的潮流中。
(一)甲午战争前后晚清的外交政策及其策略
鸦片战争前,中国沉浸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中,维护着华夷秩序,坚守着以朝贡为特征的宗藩外交政策。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炮火,西方列强接踵而来。他们依仗强大武力,一脚踢翻传统的宗藩外交,压服清政府不得不将外交政策调整为“和戎”外交,即尽量与列强交好,以求得国家的和平稳定。甲午前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秉持这一政策,只是针对不同国家略有变化而已。
甲午前后,清政府以“以夷制夷”的策略具体实施这一政策。“以夷制夷”是中原王朝对付周围少数民族的羁縻政策,即依靠一些强大民族去压制一些弱小民族。这一政策是中国历代君主制衡少数民族的一种手段。
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一些开明官僚意识到依靠自身实力无法与西方列强抗衡,但可利用列强矛盾互相牵制,以求得国家生存。因此“以夷制夷”得到了以奕 、李鸿章为首的开明官僚的推崇,成为晚清实践“和戎”外交政策的主要策略。
(二)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外交策略的实施
1.甲午战前的清政府外交:以夷制夷,无功而返。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国力与日俱增,其外交政策呈外向扩张型。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讨伐清国之策略》,意图灭亡中国。1893年5月,日本又公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等[1],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可苦于师出无名。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为日本的侵略提供了良机。为了实施其侵略计划,日本政府要求驻朝日使引诱清廷出兵朝鲜。因为朝鲜是中国藩属国,清政府有保护义务。日代理公使杉村和日译员郑永宁分别向清政府驻朝商办大臣袁世凯表示日本支持中国派兵平乱,保护商民,决无他意。而驻津日本领事会晤李鸿章也表达同样意见。他们的共同劝说,使李鸿章等人深信不疑,很快派兵入朝。
6月5日清军一入朝,日本政府借口保护商民出兵朝鲜。6月11日,东学党起义平息,李鸿章希望中日共同撤兵。而日本非但不撤,还“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韩政要求,转移国际视听,不树他敌,向中国挑战”[2]。
眼看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焦急地奔波于英、俄等大国间,幻想依靠“以夷制夷”,平息中日争端。西方大国在朝鲜的利益,以英、俄两国为大。英国表面答应劝阻,背地却支持日本,共同抵制俄国在远东扩张。日本看到英国不希望俄国在东北亚一家独大,因而向英政府表示:日清战后,立即缔结和约,以抵御俄国向南扩张。遏制俄国正中英国下怀,而且日本屡次向英国保证决无占领朝鲜之意,亦不损害英在华任何利益,于是日本发动战争得到了英国默许。
与此同时,李鸿章频频与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接触,请求俄国调停中日冲突。俄国向日本施压,要求中日两国同时撤出朝鲜,并与俄国一起商谈朝鲜问题。然而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对华作战,因此日本外相陆奥态度强硬,照会俄国,决不撤兵。俄国恼羞成怒,照会日本政府:“如果日本在与中国同时撤退驻朝军队一事上故意阻碍,则它应负严重责任。”[3]日本接到俄国照会,并未改变初衷,反而将俄国照会透露给英国。英国见俄国以强势压日本,更猜忌俄国在远东的祸心,因此“向俄建议对中、日之争,由各国共同行动,但不能用恐吓手段”[2],暗示自己对俄向日施压不满。最后,俄国一面受英国牵制,另一面因战争准备不足,不愿大规模派兵干涉,因此偃旗息鼓,对日本发动战争听之任之。清政府借助俄国避免战争的愿望落空。
其他欧美列强,一方面从朝鲜获利很少,对朝鲜纷争不感兴趣,另一方面被日本利益均沾的许诺所蛊惑[4],所以对中日纷争名为调停中立,实则襄助日本。譬如美国以偏居美洲一隅,与亚洲利益无涉为由,不愿参与中日纠纷。当清政府请求美国劝告日本撤兵时,美国国务卿葛礼山明确表示:“我们不可能与其他列强联合进行任何形式的干涉。”在日本拒不撤兵、肆意挑衅时,他还偏信日本一面之词,认为:“从谭恩(美国驻日公使)及其他方面收到的情报看来,我难立即相信日本将诉诸战争”。[5]可见,美国表面中立,暗中却偏袒日本。可见,以美国为代表的其他欧美列强在日本利益均沾的笼络下,更乐观中日战争的发生,以望从中分一杯羹。
由于李鸿章等人将大量精力投入在外交上,因而疏于军事准备。甲午海战前,丁汝昌曾电奏李鸿章:“各舰齐作整备,侯陆兵大队调齐,电到即率直往,并力拼战,决一雌雄。”[2]然而李鸿章只将北洋海军当作威慑日本的力量,不让其主动出击。7月4日,李鸿章甚电令丁汝昌,不准北洋海军“往巡大同江”。[2]淮军将领宋庆请援义州,李鸿章不准;朝鲜牙山的叶志超请战添兵,李鸿章训道:“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2]因此,李鸿章倾力于外交斡旋中,并未做好迎战准备。这一点袁世凯洞若观火,他提醒李鸿章:“朝鲜与日合作,徒恃调停有误军机”。[2]然而李鸿章不以为意,继续致力于“以夷制夷”。而西方列强的暗地倒戈,使李鸿章等人依靠“以夷制夷”避免战争的幻想毁于一旦。
2.甲午战争中的清政府外交:以夷制夷,处处碰壁。1894年7月25日,日本在朝鲜丰岛海面突袭北洋舰队“济远”等舰,丰岛海战爆发。日军击沉清军借来运兵的英国商轮“高升”号,造成“高升”号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后,李鸿章等人以为英国会迁怒日本,坐等英国介入战争。谁知日本买通剑桥、牛津两名国际法专家,指责中国违背国际法在先,日本击沉“高升”号无错。英国一些报纸也在日本收买下煽风点火,一时舆论都以中国为非。英国政府非但不责怪日本,反而要求中国赔偿。李鸿章等人依托英国制止日本的梦想化为泡影。
8月1日,中日互相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清政府仍未放弃“以夷制夷”幻想,试图借助列强力量,中止战争。然而各国均声称严守中立,不愿干预。“英国对中、日战争,宣布严守中立。俄国对中、日战争守普、法战时之局外中立。德国亦宣布中立。”[2]尤其是战前曾一度支持清政府的俄国,这时一反常态,不仅要求驻华公使不干涉中日战争,而且告诫其不要积极调停。俄外相格尔斯说:“积极调停,只上李鸿章的当,对中国有利。在中国狡狯的北洋大臣旗帜下,作日本公开的仇敌,而限制俄国的行动。”[2]俄国态度尚且如此,其他各国更为冷漠。
尤其是1894年9月,中日海军主力进行了黄海海战。北洋舰队损失惨重,被击沉或烧毁5艘军舰;而日本未失一舰,只有5舰受伤。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躲入威海港,还是期望通过外交来制止战争。据英国路透社报道:黄海海战后,清政府奔波求情于列国,恳请和解中日之 ,而“俄法两国未允为劝和中日之倡。德国且以为战事方殷,虽劝亦无益也”,因此“欧洲述及中国商请劝和之事,彼此各怀意见,不能询谋佥同”。[6]而英国,表面不偏不倚,答应帮助中国调停,背地却相助日本。中日开战后,本来清政府已在英国购买了一艘水雷船,准备开往中国,英国以“守局外之例”阻拦,不准出口。订购智利的两条舰也因英国阻挠而扣。[2]而不久,日本从英国购得一艘商船,战争期间购买商船用意十分明显,英国却听信日本牵强解释,将商船放行。[6]英国对中日的不同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至1895年2月初,日本进攻威海卫,包围北洋舰队基地刘公岛,眼看北洋舰队危在旦夕,各国仍见死不救。当时报纸都义愤填膺,“各国候日攻至北京,始可公论相助”[2]。西方列强的险恶用心一览无余。等到刘公岛尽失,清政府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到处求援,列强仍无动于衷。2月22日,李鸿章会晤英、俄、法三公使谈调停,各公使表示:“非得日本条件无从干涉,非各国利益受威胁不致干涉。”[2]可见,列强的干涉是建立在自己利益受损基础上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他们奉行利益法则,决不做赔本买卖。因此,清政府虽绞尽脑汁,也一筹莫展,处处碰壁。即使美国虽表示愿意调停,但只是牵线搭桥,为中日和谈做铺垫,并非以强力勒令日本停战。
3.甲午战争后的清政府外交:以夷制夷,三国干涉。1895年2月,中国实力最强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清政府万分绝望,只得屈膝求和。其实黄海海战后,慈禧就有议和之意。12月20日,清政府派张荫桓、邵友濂去日本议和,但日本借口他们非全权大臣,拒绝与其谈判。清政府只好改派李鸿章赴日议和。临行前,李鸿章“先有所商于各国公使,俄使喀西尼许以大力拒日,保全我国领土,转要求军防及交通上之利便,以为报酬”。[2]因此李鸿章赴日前,已与俄国有了秘密约定。
李鸿章到达日本后,立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谈判。日本自恃军事胜利,除要求赔偿3亿白银外,还要求割让台湾、辽东半岛等。李鸿章迅速将日本的苛刻条件告知各国,引起了俄、德、法等国的强烈反应。尤其是俄国,认为割让辽东半岛威胁到了自己在远东利益,因此不遗余力联合法德等国抵制。指出:“日本之占领远东半岛及旅顺,将使中、日永为世仇,威胁远东和平。”[2]法德也想通过帮助中国而取得一个不冻港的报酬,因此同意与俄共同干涉。在俄法德三国干涉下,日本被迫放弃辽东半岛,让清政府用三千万两白银赎回。由于事关俄国切身利益,因此这次“以夷制夷”得以成功。
二、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外交之评介
甲午战争前后的清政府外交看似轰轰烈烈,费尽周折,结果却一败涂地。其主要原因在于清政府外交系统存在诸多弊端:
(一)外交策略单一,未能与军事相结合
甲午战争前后,清政府单纯依赖“以夷制夷”的策略制止战争。虽然这种策略在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中有过成功,当时李鸿章利用“以夷制夷”,凭借俄、德、美、法等国干预,成功拒绝了英国的一些苛刻要求,被誉为“以夷制夷”的典范。但在甲午外交中,清政府运用这一策略却屡屡失当。原因何在?
一是因为当时纷纭复杂的国际局势下,清政府外交策略过于单一,根本不能应对复杂局势。当时英俄美德法等大国在华利益不同,对中日纠纷的态度也不同。倘若清政府能审时度势,不是一味请求列强帮助,“以夷制夷”,而是采用远交近攻、柔远笼络、各个击破等多策略的话,甲午外交格局可能为之一变。因为各国具体利益不同,其外交立场态度是取决于本国利益的。只有根据其利益需求点有的放矢外交,才能赢得它们的支持和帮助。可是清政府没有看清这一点,只是以《万国公法》为依据,请求各国主持公道正义,谴责日本。西方列强表面答应,实际敷衍塞责,不肯出力相助。以致李鸿章最后也绝望叹道:“天下熙熙攘攘,皆为利耳。我无利于人,谁肯助我。”[2]可惜悔之晚矣。反观日本,根据英俄等国的不同利益,纵横捭阖。日本的增兵最先引起了俄国的怀疑,俄国要求日本撤兵。日本一面婉言拒绝,一面将俄国态度透露给英国,利用英国牵制俄国。为了安抚英国,日本表面接受英国调停中日,背地却故意造成谈判破裂,还将责任推诿于中国。还向英国多次表示协助英国遏制俄国,于是日本发动战争得到了英国支持。对于其他欧美列强,日本则笼络人心,许以战后利益均沾,获得了他们支持。因此日本依靠灵活多样的外交策略为其创造了一个良好的开战环境,赢得了国际支持。
二是清政府未能将外交与军事相结合,“以夷制夷”。“以夷制夷”能否产生效果,关键还要看其背后的军事实力。只有依托军事后盾的“以夷制夷”,才有威力。日本之所以不惧俄国的恫吓威胁,坚持增兵开战,其根源在于明白俄国根本不会动用武力干涉。1894年6月25日,日本外相陆奥询问驻日俄使:“俄国致日觉书,谓日本不撤兵,日本将负完全责任,是否指俄国不仅以外交方式支持中国?”俄使支支吾吾,答曰:“须候训令再答”。[2]6月28日,俄国外相训令驻日俄使:“日本获得英、俄不协调,武力干涉将不可能之正确消息。”[2]可见日本通过多方刺探,已断定俄国不会武力干涉,因此对于俄方的恐吓威慑毫不畏惧,照样我行我素。倘若俄国真是大规模调用武力干涉,日本绝不敢置俄国警告于不顾。日本都已侦知俄国底牌,而李鸿章还如坠云雾中。虽然他迫切期望借助英俄力量扭转时局,但没有军事后盾的纯粹外交不可避免要失败。日本外相陆奥对于李鸿章的外交伎俩心知肚明,他向天皇及内阁报告道:“鸿章平素高傲,此次仅嘘声恫吓,实际上无准备。”[2]因此,日本甘愿承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也拒不撤兵,使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幻想化为泡影。可见,没有军事支撑的“以夷制夷”苍白无力,没有任何实效。
(二)外交人员过少,信息渠道不畅
晚清外交人员数量很少。据统计,从1876年清政府派出第一个驻外公使郭嵩焘始至1895年,清政府派出的常驻使节仅22人,出驻12个国家。出使日本的仅有何如璋、黎庶昌、徐承祖、李经方、汪凤藻、张斯桂6人。使馆内只有副使、翻译等几个随从人员。直到甲午战争爆发,李鸿章等清政府要员无一人到过日本,因此清政府对日本的战略意图根本不了解。有限的一点信息主要靠驻日公使汪凤藻收集。在朝鲜则依靠袁世凯。清政府不仅外交人员数量少,信息来源渠道单一,而且信息主要靠电报传递。寥寥数语,经常不能反映事情全貌,更何况中韩电讯还经常中断。因而袁世凯在朝鲜如同困兽,多次要求回天津面禀详情,因“日胁韩欺华,韩情日变,消息常阻,凯坐视无益。韩日情形,惟凯稔知,拟请调赴津禀商”。[2]对于如此合情合理的请求,清政府为了颜面和衅不先开的顾虑,谕令袁世凯仍留朝鲜,白白丧失了掌握更多信息,正确决策的时机。由于得不到足够准确的信息,以李鸿章为首的清政府根本不能正确判断日本意图,只能根据事态发展被动决策,因而处处落后。譬如清政府请俄国压服日本,逼迫其从朝鲜撤兵。日本通过情报洞悉俄国外强中干,无力干涉,因此坚决不撤。而总理衙门和李鸿章囿于情报信息少,凭主观臆断决策,不能及时调整外交政策,产生积极效果。1894年7月8日,对于日本增兵朝鲜,总理衙门告诉李鸿章,“日此番动作本起于忌俄”,而李鸿章回复说:“日此番动作实由该国自由党众横议生事,当轴俯徇,非起于忌俄”。[2]不管是总理衙门的分析还是李鸿章的纠正,都距事实太远。之所以判断失误,主要原因在于情报资料有限,使他们昧于时局,不能通盘考虑。因此情报资料的匮乏,使清政府在军事外交决策中,都处处落后,步步失算。反观日本,派出大量间谍在朝鲜和中国刺探军情政情。藤村道生的《日清战争》叙道:“当时,日本陆海军分别向清国派遣了情报官员”[1],其中海军大尉泷川具和与参谋本部所派的神尾少佐就是两个著名间谍,在甲午前后为日本军方提供了大量情报,与驻华外交官一起为日本政府做重大决策提供信息支持。日本不顾列强谴责,决不撤兵的重大决策,得益于其间谍探知了中国底细,因此有恃无恐。李鸿章对此痛心疾首:“日本有间谍,而中国无。”一有一无,双方信息资源的不对称一目了然,决策优劣不言而喻。
(三)外交理念天真幼稚,外交本质蒙昧不清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逼迫下,亦步亦趋地接受西方近代外交理念。随着中外交往的日益繁多和《万国公法》的传入,西方的外交习惯、外交礼节、外交体制逐步传入中国,为李鸿章、郭嵩焘等开明官僚所接受。但在接受过程中,他们只看到了近代外交理念光彩照人的表面,而对背后的实质缺乏正确了解。特别是李鸿章,迷信《万国公法》,以为各国应遵守平等、正义的原则。若一国破坏,必遭国际社会谴责或干涉,不得不修正自己行为。当日本照会中国出兵朝鲜时,李鸿章指示袁世凯邀请各国驻韩公使诘问日本,试图以国际舆论压服日本,不让出兵。袁世凯运用此法无效,看出“日出兵非口舌所能阻”,希望另设它法时,李鸿章训诫道:“日独调兵,各使当有公论,我宜处以镇静,若互调兵是自扰也,令向日使阻出兵。”[2]即使后来日本不听劝阻,依然增兵朝鲜,眼看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还训斥叶志超道:“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2]可见,李鸿章迷信《万国公法》的公平正义,以为自己信守公法,就可以获得国际社会支持,消弭战事。岂知这想法太天真幼稚?殊不知,西方近代外交本质是以武力为后盾的强权外交,各国“虽以亲睦礼仪相交,但皆是表面名义,于其阴私之处,则是强弱相凌,大小相欺”“万国公法,也是系于国力强弱,局外中立而唯守公法者,乃是小国之事,至于大国则无不以其国力来实现其权力”,因此以实力求强权才是近代外交的真谛。然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晚清决策者尚未意识这一点,为《万国公法》表面迷惑,寄予外交来解决中日争端,一再贻误军机,对甲午海战的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四)外交机构不完善,外交人员素质低下
晚清外交机构不完善,存在诸多弊端。晚清外交事务虽由总理衙门主管,但总理衙门并非专门的外交机构,而是负责所有洋务。而且总理衙门官员多是兼差,往往一人身兼数差,办事效率低下。即使就外交而言,总理衙门也未能总理其事。许多具体事务,由南、北洋大臣负责。无论是总理衙门官员,还是南、北洋大臣,都身兼数职,不能将全部精力集中于外交。而专门的外交人员数量很少,根本不能承担提供大量情报信息的重任。因此在信息匮乏且模糊的情况下,晚清决策者只能凭经验和有限信息做出一个个不切实际的决策,致使外交一再受制于人,步步失算。
晚清外交人员的素质十分低下。李鸿章号称“中国外交第一人”,尚且在外交中频频失误,显得幼稚可笑。其他外交人员更是昏庸愚昧,缺乏经验。1894年7月,在李鸿章的强力周旋下,英国出面调停,要求中日两国就朝鲜问题谈判。这本是甲午战前清政府扳回外交失利的最后机会。因为此时英国尚未完全倒向日本,若谈判顺利,中国或可推迟战争的爆发,甚至可将英国卷入中日漩涡,使英日生隙。然而清政府派出的庆亲王奕 ,不识时务,一味要求日本先撤兵,再商朝鲜改革。而日本反向要求,结果双方不欢而散。紧接着,“英公使欧格纳向奕 提出调停韩事四项方案”[2],奕 亦断然拒绝。奕 的行为,完全关闭了中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的大门,正中日本下怀。日本喜出望外,因为本不愿谈判,现可堂而皇之把谈判破裂归罪中国,获得英国支持。奕 笨拙僵化的外交,让中国白白丧失了避免甲午战争的最后机会。对于清外交人员的愚笨无能,美国公使论道:“总署大臣乞援,有如儿童之乞饶教师,愿无代价之和平,多问日本是否囚杀皇帝,彼等是否送家眷他往?从未见有如此腐败,如此无能而无希望之官吏。”[2]因此,清外交人员素质低下,不但未能有效发挥外交功能,反而使日本一石二鸟,获得了英国的支持。甲午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了。
三、余论
甲午外交虽已过去一百多年,但其中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正确把握军事与外交的关系,促进各种复杂国际纠纷的解决却极有教益。
灵活的外交策略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具有四两拨千斤的作用。甲午战前,日本凭借灵活周密的外交策略获得了西方列强的普遍支持,使清政府孤立无援,为甲午战争的失败埋下伏笔。其实,倘若清政府能及早认清日本侵略的本质,采用适宜的外交策略解决朝鲜问题,那么晚清外交的困境可迎刃而解,甲午战争或许能够避免。可见,外交的成败对国家危机问题解决有重大影响,它可化险为夷,避免或推迟战争发生。
外交应以军事为坚强后盾,齐头并进。虽然外交的长袖善舞可一定程度化解矛盾,但单纯依靠外交来解决领土争端,化解战争危机又不现实。甲午战前晚清外交就是因为没有军事实力的辅助,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外交人员虽殚精竭虑,疲于奔命,但依然未能避免战争爆发。因此,即使要运用外交化干戈为玉帛,也需以强大武力做后盾。这一点在经历甲午惨败后也为时人所认识,“从来言和必先言战,战者和之本,能战而后能和,未有不能战而能和者也”。[7]因此在当前各种国际争端解决中,我们既要灵活运用外交手段,又要辅以必要的军事手段。只有军事和外交相得益彰,才能达到管控危机、避免战争的目的。
注释:
(1)如崔萍:《李鸿章与晚清外交》,《华北电力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易振龙:《论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谭 :《试析李鸿章“以夷制夷”外交策略——缓兵之计》,《漳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朱婧:《甲午战前李鸿章与日本的外交之比较》,《江苏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1期;金佳博:《甲午战争前45天的晚清外交》,《辽宁工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