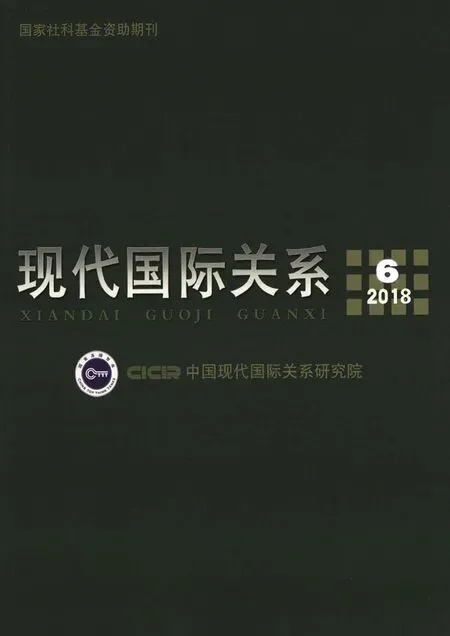从“新冷战论”看中美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
赵明昊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近一个时期以来,一些国际战略界人士在评析大国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时常常提及“新冷战”,甚至还有人提出中美已经陷入霸权国和崛起国激烈对抗的“修昔底德陷阱”。显然,这一看法夸大了中美两国之间存在的分歧和矛盾,某些政治势力似也有意借此竭力推动美国对华战略朝着更具“敌对性”的方向发展。即便如此,不应轻视“新冷战论”在舆论塑造、政策塑型等多个层面对中美关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冷静、深入地辨析这一论调,有助于更加警觉、审慎地把握当前中美关系发展面临的若干突出挑战,进而寻求中美关系的良性重塑之道。
很大程度上,“新冷战论”与中美双方对“新时代”的不同定义和认知是相互关联的。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未来30年中国将按照两步走的战略安排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此外,该报告还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进入“新时代”的中国势必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带来更多机遇。然而,部分西方人士却对中国的战略意图进行刻意曲解,错误地认为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意欲实施地缘扩张和意识形态输出,谋求用中国的“新时代”取代美国的“旧时代”。其中,尤以“另类右翼运动”旗手、白宫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散布的相关言论为甚,他以“儒家重商威权主义”描述中国模式,诬称中国借“一带一路”、《中国制造2025》等谋求全球霸权,并煽动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联合起来对抗中国。
2017年年底,特朗普政府推出执政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正面对全球竞争的“新时代”,将中国明确定义为“对手”和“修正主义国家”,认为过去数十年美国旨在通过“接触”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战略假设是错误的。显然,特朗普政府眼中的“新时代”与中国所说的“新时代”是截然不同的,前者强调的是竞争和对抗的一面。虽然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几位主笔人目前皆已离开白宫,但这一文件的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国战略界的共识,尤其是针对中国政策的共识。不仅很多共和党政界人士炒作新一轮“中国威胁论”,民主党人、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等近期也明确提出,中国而不是俄罗斯才是美国最大的对手。应看到,2010年前后启动、2015年前后逐步“白热化”的美国对华政策辩论,到了2017 年基本形成了一种新的共识,即中国已经成为美国“首要的、全面的、全球性的战略竞争者”。
无疑,美国对华战略定位的重大变化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虽然美国和中国对“新时代”的看法存在根本差异,但世界政治的确正进入一种大致以“后冷战、后(金融)危机、后西方”为特征的“新时代”。显然,国际秩序的深刻转型与中美关系的深刻转型正相互交织、相互影响,进而极大地增加了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困难程度,中美关系的良性重塑充满挑战、任重道远。概言之,世界政治的“新时代”意味着以下几点主要变化: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再平衡”正加快展开,特朗普政府矢志推行的“美国优先”政策不过是这种“再平衡”的剧烈表现形式,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问题则深化了全球化“再平衡”的复杂程度。二是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回归”,特朗普政府的《国防战略报告》明确提出大国之间爆发激烈冲突的概率在上升。三是在多国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交叠上升的背景下,威权主义和“强人政治”的影响力在国际舞台上日趋彰显,国家—社会、政府—市场关系以及族裔政治面临新的深度调整。意识形态和社会思潮越发难以用“左、右”概念予以区分,民族主义者与全球主义者、“无序世界”与“有序世界”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有关“新冷战”的讨论逐步推展,并且对涉及中美关系的“政策话语”(policy discourse)形成不容轻视的影响。讨论“新冷战”,首先需简要辨析何谓“冷战”。毋庸赘言,“冷战”主要是指二战后不久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的长达半个世纪的对抗关系(或对抗性的稳定态势),包含地缘扩张与遏制、“相互确保摧毁”、“代理人战争”、意识形态较量等因素。“冷战”的要素是大国对抗尤其是世界上实力最强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是以“阵营”为依托,具有全球性影响和“零和性”特征,与意识形态的深刻对立密切相关。在“冷战”体系中,大国之间的“安全困境”颇为凸显,相互极易做出误判,且常常反复“刺激”彼此,它们在“边缘地带”展开的争夺也很激烈,世界处于一种“冷和平”状态。
与“冷战”相比,“新冷战”也具有大国对抗、意识形态分歧等类似特征,但两者之间存在若干明显差异。一是“冷战”中的美苏分别处于两个不同的国际体系之中,美苏之间也几无经济联系;“新冷战”中的大国则处于同一个国际体系之中,且在经济上具有一定的相互依赖关系。二是“冷战”中的大国对抗更多体现在争夺“势力范围”,“新冷战”则以大国之间的地缘经济竞争为突出特点。三是“冷战”与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两大意识形态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密切相关,“新冷战”更多展现的则是不同发展模式之争,社交媒体等技术发展增强了大国向对手施加政治影响的能力。四是“冷战”中的两大阵营对立是分明的,“新冷战”则呈现出“亦敌亦友”的情况,即一国在安全领域的敌手同时也是其在经济领域的伙伴。此外,大国之间围绕海洋、网络、外空等“全球公域”的争夺越发激烈,很多情况下这种争夺针对的不是对“领地”(territory)而是对“联通”(connectivity)和“规则”的控制。
毫无疑问,从中美关系的现状看,远难以认定两国已经陷入“新冷战”状态。虽然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进攻性”的对华经贸政策并在台海、南海等问题上采取一系列消极举动,但至今中美关系仍维持总体稳定,而且双方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等方面还进行了深度协调。然而,“新冷战论”对于中美关系的长远发展而言可谓一种重要的警示,双方需要高度重视和共同应对两国关系面临的一些新的突出挑战。
第一,特朗普政府对华不仅打贸易战也打技术战,不断收紧对中国在美投资的限制,将中美经济相互依赖作为开展大国竞争的筹码,中美经贸博弈对两国关系、全球经济治理的长期性、全局性影响不容轻视。正如美国学者刘易斯(James Lewis)所言,贸易战不仅关乎贸易赤字、技术优势等问题,或将演变为一场更广泛的战略对抗。当然,中美贸易战实际上也是政治战,其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因素密切相关,需要更多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思考和应对中美经贸摩擦,切实防范台海、南海等战略安全问题与之形成负面共振。
第二, 中美需要加紧寻求在印太地区开展良性互动之道,尤其是处理好“一带一路”与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之间的关系。美方在阐释其“印太战略”时强调,所谓“自由”的重要含义之一是指该地区国家不受他国胁迫,所谓“开放”强调的是印太地区海上交通线以及贸易和投资的开放性。显然,“印太战略”绝非美国的独创,但它也有“旧瓶装新酒”的意味,“新”在更加重视印度的作用以及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战略性影响。2017年11月特朗普政府正式提出“印太战略”以来,美方以低调的方式不断推动该战略的细化和操作化,包括将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与日本、澳大利亚等在地区基础设施和能源安全方面采取实质性的“联动”举措。
第三, 美国方面部分人士炒作“中国政治渗透论”,指责中国针对西方民主国家使用“锐实力”扩大政治影响,借助“一带一路”对相关国家输出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争成为美国战略界关注的焦点之一。“锐实力”这一颇具煽动力的概念的出现,实际上是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国内热议中国“国家资本主义”问题的延续,反映出西方对中国意识形态自信的忧虑,也势将带来现实的政策影响。鲁比奥(Marco Rubio)、科顿(Tom Cotton)等美国国会议员要求清查中国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限制中国旨在对美国媒体、智库、大学等施加政治影响的“长臂”。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德国等美国盟国也明显提升了对所谓“中国政治渗透”的戒备和应对,在美国的大力动员之下,“大西方”联手应对中国的“政治崛起”的态势不可低估。
总之,“新冷战论”由来有自,美国对华政策的大转向也并非始自特朗普政府,中美关系的战略转型正渐次铺展,需要大力维护和巩固经济、安全、外交和人文交流等支撑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正如二战后一道“铁幕”很快将世界划分为对立的阵营,当下,一些政治势力也试图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构筑“玻璃幕墙”。纵观历史,大国常以一种“梦游者”的状态走向对抗、走向战争,当年美苏陷入“冷战”也多少有一种不自知、不自主的意味。影响中美关系走向的核心因素既包括“实力对比”也涉及“互动方式”,如果说前者不易扭转,那么中美双方需要更加细致地审视过去几年来的互动历程,保持战略克制,及时做出调整,避免在不自知、不自主的情况下真的陷入“新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