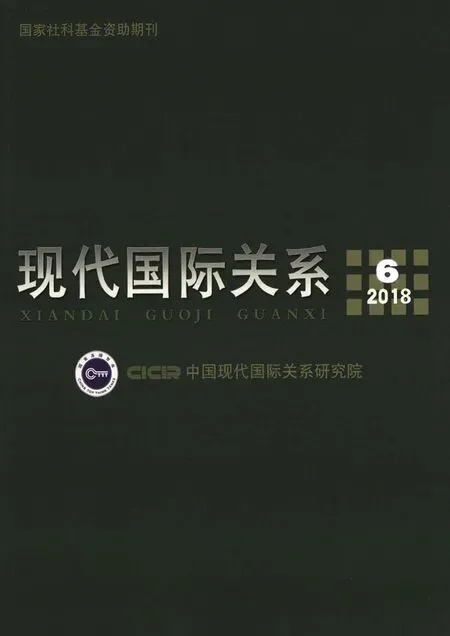国内结构变革与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
王勇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中美两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近年来均发生影响深远的国内结构变革与调整,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国内基础。与此同时,两国相互依赖关系与共同利益在不断扩大的同时,竞争性也在加大。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是美国国内结构变革的重要表现。中美贸易战不仅局限于经贸关系,也涉及到双方对彼此的认知。由于两国经贸关系竞争性的加强,技术与战略竞争提前到来。经济竞争加上意识形态与社会制度的差异,有可能推动中美两国进入“新冷战”。
一、国内结构变革改变了中美关系的基础。苏联解体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中美两国经济均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同时形成了高度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美国有学者称之为“中美国”经济)。在全球化高歌猛进的20年,中美均采取了开放市场、拥抱全球化的政策,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
经济全球化促进两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国内贫富悬殊的扩大。美国成为发达经济体中基尼指数最高的经济体,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早已意识到发展不平衡问题并采取了建立普遍社会保障体系等政策。可以说近些年中美两国发生的重大政治经济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经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回应,只是由于政治体制不同,两国国内结构性变革调整的方式不同。美国通过2016年大选选举出民粹主义、保护主义思想强烈的总统特朗普,中国则在习近平主席的带领下强力反腐,推动党和国家机构的改革,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精准扶贫、经济转型与环境保护事业。
特朗普的当选与执政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首先,支配美国全球化政策多年的权力重心发生了转移,即从波士顿经纽约到华盛顿的东北权力带转向了中西部“铁锈州”与保守农业州构成的权力地带。特朗普更关注支持其上台的中西部“摇摆州”的选民支持率,通过发动全面的贸易战等做法,使他在这些地区的支持率超过了同期的奥巴马。
其次,特朗普与中西部选民的结合推动美国采取了“逆全球化”的政策。在经贸政策上,特朗普扭转了过去20年政府支持金融虚拟经济与高科技发展的政策,转向注重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回流与贸易平衡的经贸政策。在对外政策上,特朗普改变了美国长期奉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对同盟国施加贸易保护主义压力,要求其提高国防开支,购买更多美国武器,减轻美国的财政压力。
再次,特朗普的当选与施政带来了价值观的激烈碰撞,美国社会政治共识遭受极大的削弱。特朗普及其支持者奉行的白人至上主义、保守主义政治理念与观点,与全球化精英们主张的自由主义、进步主义的理念格格不入,导致美国前所未有的分裂。故此,《时代》周刊称上台的特朗普为“美利坚分众国”总统。
在中国方面,通过过去五年来的变革,中国领导核心重新确立了权威,构建了新的政策框架,制定了更加明确的国家中长期发展战略。尽管中国国家发展目标与战略保持了很强的连续性,但实现战略的手段与路径发生了变化,即通过党与国家体制的重大改革,强化了中央权威,同时加强了对于公权力运营的监督。
中美国内结构性变革调整,堪称不同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政治革命,但它们带来的各自结果却是不同的。在美国选举人团制度下,特朗普当选制造了更多的政治与社会对立,破坏了美国内外政策的连续性,对于美国长期引以为傲的软实力造成了很大的破坏与冲击。而中国体制下的变革保证了政策的延续性,凝聚力量,克服过去的权力分散、缺乏统一协调、容易滋生腐败等弊端,同时中国对外政策的国内基础也更加坚强有力。中美两国国内结构变革调整构成了新时期中美关系的国内基础,必将对中美关系产生重要影响。
二、国内结构调整下中美关系的变化与连续性。从国内结构变革的角度看,中美关系的冲突性在特朗普时期上升有必然性:特朗普及其执政团队与选民基础反对全球化,要求大幅调整美国与全球经济的关系,中美经济关系自然首当其冲。当前中美经贸关系是过去20年经济全球化飞速发展的产物,美国存在巨量贸易逆差,这种状况与特朗普“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理念格格不入。在国际力量平衡方面,中美的差距在缩小,中国的相对国际地位大大上升。随着中国实力的崛起,特别是军事实力的上升,中国自保及可能对美国造成伤害的能力在上升,限制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行动能力。
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经济全球化时代形成的复杂相互依赖网络仍将制约当前与今后一段时间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关系仍然保持共同利益与合作性的一面。首先,中美双边贸易额达到近6000亿美元,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美方一些人士提出中美经济“脱钩论”,对于双方的代价太大,在当前环境下不具有实际操作性。此外,中美货币金融关系同样十分密切,形成了一种所谓“金融恐怖平衡”(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语)的关系。中国继续购买美国国债对于支撑美国经济包括美元的地位仍然十分重要。反过来,中国要想在国际金融货币市场有更大的影响力,也离不开美元与美国市场。其次,两国关系经过4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紧密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各种性质的对话渠道构成的紧密关系网络。人际关系的联系遍布学术界、财经界以及普通家庭,这也是对中美“脱钩论”的重要制约。再次,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的引领在目前尤显重要。两国政治领导人之间互动良好,已经形成较顺畅的沟通管道。最后,中国的战略目标与实际战略并不挑战美国的霸权。中国的目标在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中长期目标,中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以国际经济合作为主的、维持并促进现有国际机制改革的温和改良政策,国防政策主要是以自卫为目的的防御政策。在现阶段,中国的战略、政策与行动并不对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构成实质性的挑战。美国不少人认为,中国发展模式与发展理念对美国构成挑战,这种说法也没有太多道理,因为中国不主张输出意识形态,强调尊重不同国家对于自身发展道路选择的权力。
三、加强沟通,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与全球治理合作。我们必须警惕,如果中美信任不能恢复和提升,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科技产业竞争等可能将中国推向“新冷战”,重蹈过去美苏尖锐对抗的覆辙。
中美关系的未来面临两个前景的选择,一是两国加强在全球治理框架下的合作。中美可在全球治理框架、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等方面达成诸多共识,维护共同利益。中美作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对于保持全球和平稳定、维护全球开放贸易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稳定负有特殊的责任。中美在过去较好地处理了彼此的关系,利害关系与共识都在不断加强,中美在G20框架内开展的合作取得不小的进展,美国也表现出一定的弹性让中国发挥更大的国际作用。另一个前景是所谓的中美经济逐步“脱钩”,各自构筑自己的体系,最终迎头相撞,包括“新冷战”的发生。“脱钩”代价巨大,并非中美现实的选择。
要避免中美走上“脱钩”、对抗、“新冷战”的道路,首先要加强沟通。中美当前最重要的是进行有效对话沟通,取得战略信任,减少“信任赤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美国不少学术、舆论与智库人士对中国发展模式存在不少误解,过去主张与中国接触的温和派学者专家的对华态度也在发生变化。中方需要向美国精英人士多做解释说明的工作,以降低美方对中国政治变化的误读。其次,要坚持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对美政策思路。习主席2012年曾向美国领导人提出致力于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对美战略思路。在当前形势下,面对中国快速崛起的现实,美国上下焦虑感严重,对外信心下降,坚持并落实这一对美战略思想显得更有必要。再次,妥善处理中美经贸摩擦。面对美国政府与企业的不满与抱怨,中方应看到,这恰恰是美国方面看中中国市场的表现。根据2017年统计,中国已经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消费市场。上海美国商会最新调查数据也表明,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显著盈利,60%以上美国企业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经贸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地位并未动摇。在经贸谈判中,中国既要坚持原则,以实力应对美方无理要挟,同时要通过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巩固中美关系的共同利益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