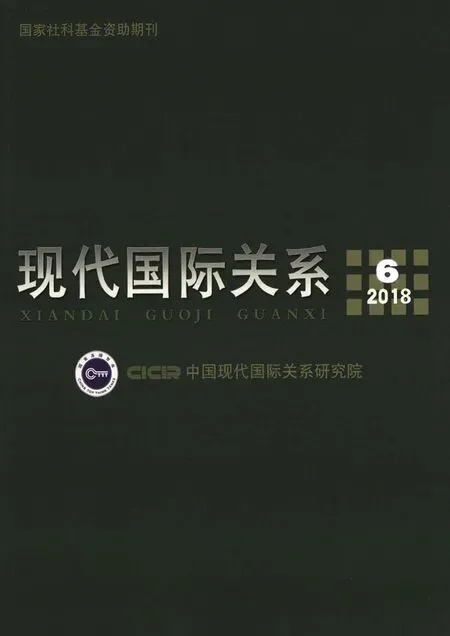警惕麦卡锡主义在美国沉渣泛起
赵梅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美国研究》执行主编)
麦卡锡主义特指1950年到1954年间,美国威斯康星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美国国内掀起的一股极端反共、反民主的政治逆流。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波及美国政治、外交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近2000万美国人遭受迫害,麦卡锡主义因而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而麦卡锡主义时代则成为美国历史上极其黑暗的历史时期。
1950年2月9日,时任威斯康星州参议员麦卡锡发表演说,称他握有一份美国国务院中的205名共产党员名单,“这些人全都是共产党和间谍网的成员”,“国务卿知道名单上的人都是共产党员,但这些人至今仍在草拟和制定国务院的政策” 。麦卡锡的这番演说令全美哗然,紧接着,麦卡锡在美国参议院掀起“揭露和清查美国政府中的共产党活动”的恶浪。朝鲜战争爆发后,麦卡锡称杜鲁门政府中有人“私通苏联”。1951年6月14日,麦卡锡发表长达6万字的长篇演说,将矛头直指杜鲁门政府对外政策重要制定者乔治·马歇尔将军。他把马歇尔将军说成是“叛徒”,说他在国务院任职期间 “帮助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同时,受到麦卡锡无端指责的还有参与美国对华事务的外交官和中国问题专家,如欧文·拉铁摩尔、费正清、谢伟思等。1953年4月,麦卡锡开始对美国设在海外的大使馆藏书目录进行清查,将左翼作家威廉·福斯特、白劳德、史沫特莱等75位作家的书籍列为禁书,历史学家小阿瑟·史莱辛格和作家马克·吐温的作品也被列入“危险书籍”之列,近200万册书籍被下架。
在麦卡锡主义肆虐不到五年的时间里,美国国务院、国防部、大学等都未能逃脱“非美活动委员会”的调查,近2000万名美国进步人士遭到恶意诽谤和迫害,其中最著名的有:美国共产党人罗森堡夫妇因被控为苏联做间谍被处以死刑;著名物理学家“曼哈顿计划”主要领导人罗伯特·奥本海默被忠诚调查委员会认定有罪,被迫切断与核机密的联系;以对中国革命的报道而著称的左翼记者史沫特莱被污蔑为苏联间谍而被迫流亡;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被麦卡锡公开斥责为“美国的敌人”; 曾在抗战期间访华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因报道中的左翼倾向而被解雇;喜剧演员卓别林被指责从事“非美行为”、倾向共产党而被迫离开美国;核物理学家钱学森被指控参加美国共产党的活动,受到联邦调查局的传讯;曾撰写《红星照耀中国》的左翼记者埃德加·斯诺遭受政治迫害,不得不偕夫人离开美国远走瑞士。
美苏冷战是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出现并横行一时的重要历史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后的美国,战争的阴影还没有消失,冷战的恐怖气氛又接踵而至。美国一方面在国际上与苏联对抗,另一方面在国内恐惧共产主义。反共、反民主及无端的政治迫害,是麦卡锡主义的主要特征。
麦卡锡时代距今已逾70年,但阴魂始终未散。进入21世纪以来,面对恐怖主义和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衰落等新问题,麦卡锡主义不断以新的形式在美国社会出现。
首先是对不同文明的恐惧。“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社会弥漫着一股较为强烈的反穆斯林情绪。在2016年大选期间及选后,特朗普在多个场合发表反移民、反穆斯林言论,誓言“禁止所有穆斯林进入美国”,主张杀戮恐怖分子的家人,誓言要用沾满猪血的子弹对付恐怖分子。2018年1月,特朗普签署了被称为“穆斯林禁令”的总统行政令,宣布在未来90天内,禁止向伊拉克、叙利亚、伊朗、苏丹、索马里、也门和利比亚七个伊斯兰国家的普通公民发放签证,以防止从这些特朗普所称的“高危地区”输入恐怖主义。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及执政后针对穆斯林的言论和政策,以及“9·11”后美国社会弥漫的反穆斯林情绪,引发了美国有识之士的关注。他们把当前美国社会弥漫的反穆斯林情绪、美国政府出台的特别针对伊斯兰国家的政策称为“新麦卡锡主义”。
早在2009年,美国“右翼观察”的研究注意到了麦卡锡主义在美国回潮的现象。2015年初,《大西洋月刊》发表彼得·贝哈特的评论文章,认为特朗普的“新麦卡锡主义”,不仅对共和党内部造成很大的破坏,而且将危及美国民主。美国专栏评论家理查德·科恩在《华盛顿邮报》连续发文称,特朗普是当代麦卡锡,特朗普主义将很快取代麦卡锡主义。他说,特朗普曾提议禁止世界上16亿穆斯林进入美国,这不切实际。麦卡锡指责美国政府内部有听从苏联政府的共产党人,这点和特朗普很像。美国的移民法有问题,确实需要修改,也确实存在伊斯兰威胁,但这种威胁是来源于反社会的疯狂分子,而不是整个穆斯林群体。
其次是对中国发展速度和发展模式的恐惧。近期,中美关系发生逆转。一直强调和中国最高领导人有良好个人关系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突然 “变脸”,2018年3月,在中国两会刚刚结束的一周内在三个领域对中国接连发难,严重干扰了中美关系,中美关系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冲突一触即发之势。在经贸领域,中美贸易摩擦日益升温;在军事安全领域,启动“印太战略”;在政治外交领域,美国参众两院无异议通过《台湾旅行法》,并由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2018年5月10日,美国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以60票赞成、1票反对通过《2019年度国防授权法》,称中国大陆通过长期战略、军事现代化、掠夺性经济压迫邻国,美国应协助台湾提升防卫能力,与台湾安全机构合作以期作为抗衡中国的战略之一;支持对台军售;支持依据《台湾旅行法》进行的美台军事人员交流;禁用华为、中兴产品。2018年6月6日,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公布参议院版本的《2019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草案,其中包括支持强化美台安全合作及军事交流条文,以“意见”方式要求美军参加台湾 “汉光” 年度军演;美方考虑派遣军事医疗船赴台,执行“太平洋伙伴”任务,扩大美台人道救援等。
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变化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背景。除了中期选举、中美贸易逆差等因素外,美国对华疑虑总体上升是近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重大逆转的主要原因。自20世纪70年代初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启动以来,中美关系尽管历经曲折,但总体上保持平稳的发展势头。在过去40年间,两国力量对比的总体态势是美强中弱。然而,这一态势近年加速酝酿根本性转折。随着两国力量的日益接近,中国在对美交往中变得越来越自信,美国则越来越焦虑,这种焦虑感在美国战略界、政界正成为较为普遍的情绪。
2015年前后,美国战略学界曾经展开过一次对华政策大讨论,前美国驻印度大使、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布莱克威尔与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一份报告认为,过去数十年的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即将中国的经济与政治整合并融入“自由国际秩序”以改造中国的政策,是以损害美国在全球的优势地位与长远的战略利益为代价的,未来数十年中国是美国“最值得警惕的竞争者”,因而主张美国应该实质性地修改现行的对华大战略。2015年2月,白邦瑞在《百年马拉松:中国取代美国成为全球霸权的秘密武器》一书中指出,在长达40年的时间里,中国领导人一直“忽悠”美国总统和决策者,让他们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值得美国支持的“良性强权”。这一秘密的“忽悠战略”是基于中国古代的治国理政艺术,利用大量的金钱、技术和支持军队的专家进行运作,中国共产党中的强硬派正采取这些措施赶上并最终超越美国。当时这部著作遭到了美国战略研究界不少学者的批评。
然而,时隔几年,美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变得似乎不再有那么多派系,认为中美关系竞争性将上升的人居主流,质疑的声音几乎没有。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前助理国务卿坎贝尔与前副总统拜登的副国家安全顾问雷特纳,在美国《外交事务》发表的《中国重估算:北京如何让美国的期望落空》一文最具代表性。该文虽不像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那样的“咄咄逼人”,但同样以美国视角审视中国的发展道路,并表达出对此的“失望”。特朗普对华示强,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美国国内的这股思潮。
美国对华政策的急剧转向,对中美关系产生了极为负面的影响。有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中美关系面临着比1989年更为严峻的考验和挑战。
在对中国崛起的疑虑总体上升的大背景下,美国学界、政界及美国社会出现一种以“恐中”“反中”为主要特征的新的“政治正确”,主张对华接触的学者被指责、被“抹红”,甚至被污蔑为被中国收买,为中国办事,误导美国政策;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访问学者,被认为是中国派到美国的间谍,甚至一些中国访美学者、学生遭到美国有关部门的骚扰和羁押;美国媒体上出现一些中国 “红色资本”进入美国学界、校园的负面报道;美国政府加强对中美科技交流的管制,如严格限制科技、生物等领域的中国学者、学生赴美深造。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并且都是中国政府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
凡此种种,令人不禁想起20世纪50年代麦卡锡主义肆虐的那个黑暗年代,因而有评论把后“9·11”时代的反穆斯林情绪和这一波“中国威胁论”称为“新麦卡锡主义”。历史悲剧不应重演。以史为鉴,防患于未然,才能更好地面向未来,应对更为严峻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