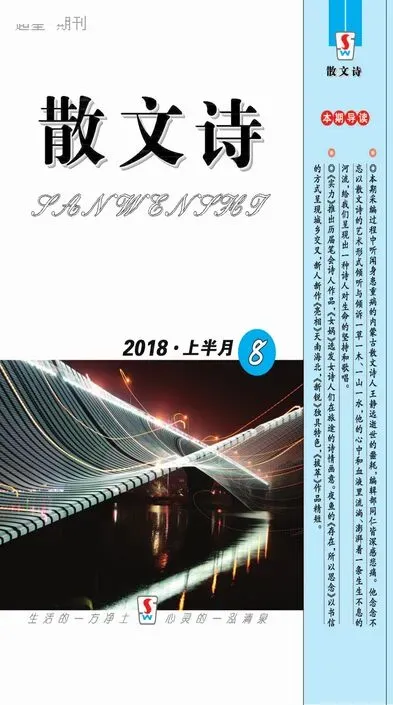麦克阿尔蒙的散文诗
◎董继平 译
乡 村
现在酒吧全都关闭了。木板交叉地钉在它们的门口。蛛网越过一块块破玻璃而悬挂着。
然而,阿尔·威尔森可能不会在乎他是否今天还活着。早在考虑禁酒令之前,他的妻子就在所有的酒吧把他拉上了黑名单,还告诉杂货店老板不要卖给他任何种类的蒸馏物,实际上就是不要买给他任何东西。她迫使他到玉米筒仓去住。
可怜的异教徒威尔森太太!她没有玉米筒仓来让自己忘记困境。她是一个孤单寂寞的人物,也并非生来就孤单寂寞。到最后,她会戴上打着整洁的补丁的手套,每个礼拜天都会前往教堂,满怀尊严走上过道,在唱诗班中用她那颤声的女高音歌唱。到最后,她会给女士们打电话,要她们来拜访她。如果阿尔弗雷德是镇子中的人物,那么她就至少能做正确的事情。
其他人——从长椅上对着车马出租所吐出烟叶的咀嚼烟草的人,教堂执事戴维斯——他的回家过程颇具仪式性:举起帽子,一副细心谨慎的风度,谈到新牧师,因为从来就没有新牧师的时候——其他人,那些不会“上瘾”的饮酒者,在台球游戏之间,谈到为镇子获得一个新邮局,回忆起威尔森夫妇最初结婚的时候。每个人都清楚阿尔弗雷德适合进入国会——一个多好的绅士,一个多么杰出的年轻律师,“很有前途,哈哈哈,但诺言不会被始终保持下去。”马蹄铁匠古斯会把鼻烟在舌头上吹出来。可怜的阿尔!没有规避这样一个事实:威尔森太太是一个魅力十足的女人,是一个声音柔和、如此富有成就的音乐家——如此和蔼,阿尔的祸根!
现在威尔森夫妇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五个孩子,其中一个孩子不那么正常。据说,阿尔弗雷德喝醉之际——是啊,伤心的例子,伤心的例子。
现在酒吧关闭了。去年夏天,一个年轻律师开枪自杀身亡,因为老镇上的生活如此单调、枯燥,也如此难以维持生计。“哎哟,跟阿尔·威尔森在年轻的时候相比,他可没有烈酒让自己欢乐。”古斯一边告诉我,一边一如既往地咀嚼哥本哈根鼻烟。
可能还有其他不安的人。一个男孩曾经常常告诉我说我是唯一“理解”的人。理解吗?我能明白他正在变成又一个不安的人——未来的结局是什么?——一种结局的结局是什么?
在这个老镇上,那么多废弃的建筑物中都有蜘蛛网和尘封的破窗玻璃。即便是我曾经学会游泳的那个泥坑也干涸了,生活如此枯燥,在那里覆满灰尘,枯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