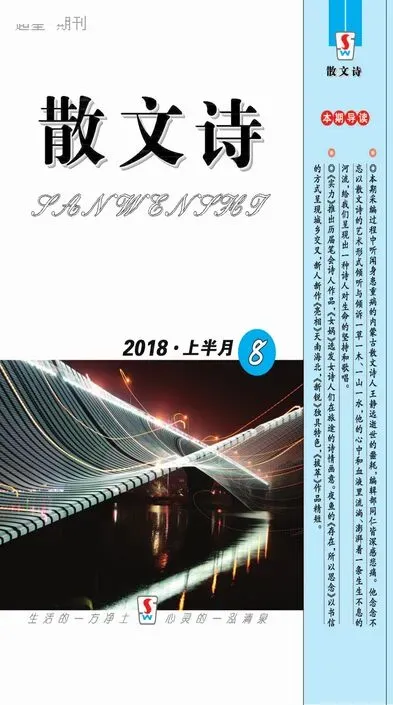低低地语
甘肃◎张 筱
命运放生的鱼
鱼不上岸,鱼不知有岸。上岸后的鱼有两个结局,一种是被人收养,一种是上了餐桌,当然还有第三种结果:被放生。
我,就是被放生的鱼,一次又一次被命运放生的鱼。这是我的生存命运,不是宿命。
我讲不好人类的故事,也写不好自己的命运,只能听一听鸟鸣,看一场又一场花开花落。
梨花是孤独千年的白
倚栏,晒太阳,看一树梨花,白得彻骨。
天空,不是惯常的蓝,是满天的浮云。浮云,也是一种灰灰白白白白灰灰的样子。
远处是山,山下是城。城边上也闪耀着一抹白花花的光景,那是一条河。
风吹着,梨花簌簌而动。此时我看到的是千年的白、孤独的白。原来,我一直打探的孤独,竟然是一树梨花的白。
热爱时间
时间是一枚锁扣,它锁过青春,也锁过爱情。它锁过欢悦,也锁过神魂颠倒的快乐。在它的锁眼里,所有被锁过的东西节节溃败,唯有锁链紧坚滑腻如髓。
时间也是无情之吻,被它吻过的东西,都在变老。
时间或者是一匹种兽,它和每一个人都在不停地交配,把我们的生活孵化。
时间也是一位情人,在不经意间,我们一一被它打败,没有人能够幸免。
我热爱着时间这个怪物,甚至超过了热爱自己。
被装饰与装点的生活
遮蔽,敞开,隔断,分流。风从敞开的窗吹进来,巨大的喧嚣也一块跟着进来。
喁喁私语者,占据三个角,我是其中一小撮之一。询问,或坦白,之后说着些不着边际的话,时光就这样一丝丝斜了过去。
这是在城市的心腔地带,繁华暂时被隔开。坐在条桌前的条凳上,喝着一杯不酽不淡的茶,若彼此间的友谊,这一晃就过去了十数年。
这是在实实在在的光阴中,空洞有物,有人,有被装饰与装点的生活。
区域空空荡荡,几个活物,也似成为装饰一般。几个人,各自装饰了彼此的生活。
滑 过
如一个重音符,反反复复滑落在一场梦或一场场酒醉中。时在白天,时在子夜。
如一个低音符,在四月的弦上滑落。从南方到素园,从素园到这个西北的小城。
如一个休止符,在时间的琴弦上滑落,沉醉、忧郁、枯寂的光阴,轻轻卷起一角。
一场沙尘暴后,我看到一幢巨大的楼影昂然在昏黄中,森森如一枚导弹,又形似如一棵阳具立于天地之间。
巨大而坚挺的表象与意象,正是世界的形貌,而人类却越来越委琐不堪,越来越失意落魄,尽管没有谁愿意承认失败。
另外的地方
天气暧昧,心情也暧昧肿胀。边喝茶边翻书,冯唐这厮写道:“什么样的文字/能穿越时间的流水/不停地转世?”瞬间,有种被击穿胸腔的感觉,肿胀如溃脓散了一地。
四月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心绪泛动,藏着些慌张与期待。我不能笃定地说见与不见。
时间的流水,带走了落花,也带走了宅在半坡居的时光。背倚书墙,只想这样坐着,不思不想,一杯又一杯喝到地老天荒。当然,这只是千念之后的一念。
还要走,还要路过,还要去另外要到的一个个地方。
出离与摇摆
天灰地苍,在距地两米的高度奔驰。此种莽苍,只有身临其境、深入其中,才能感受到天地间的浩然。
喜欢西部,这是其中因素之一。
穿越隧道时,点点灯光划成几道弧线,暗黑中,我携带一颗出离的心,沉郁而又柔肠百结。生活,也许就是如此这般逃离现场又进入下一个现场。
天昏地暗,就是沟壑那些正在盛开的梨花,似乎也不能将一颗摇摆之心的热情点燃。
无聊中,我取出朋友给我的印章,望着那刀刻的被朱砂染红的凹陷处,我仿佛看到一个又一个人性的陷阱。“士心日月”,由名而拆分的这方印章,我心仪已久。
前面的小城,一个朋友等着我,连同一场夜话。
半坡居呆呆的煤炉子
城市的人世,已经越来越远离炉火的柔暖,而靠近别的暖。没有火的世界,不敢想象。
半坡居,闲置一冬的煤炉在暮春的某一天被点燃,因为夜雨突来,因为春暮仍寒,因为怀念或许是某个情结所致。
以往,炉子都是冬天架装,春暮拆除,年复一年。自去年始炉子没有拆除,过了两个冬天又两个春天。此次离开,不知何时归,就让它如以前一样,呆呆地守着半坡居吧。
走上去
我决定走上去。这次来,晚上都是在醉意中乘车上山,今晚我要走一走。
这是我下午看过白云的山径,是我走过多年的捷径。爬着台阶,就看见了星星。星星还是那年那夜的星星,只是径上没有积雪,没有脚下咯吱咯吱的声音。夜,一如那年的幽静,只是雪径上少了几个勾肩搭背的人。风,走着走着就散了。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走丢了,只剩下自己,只有自己。
走着走着,想要再晚一点,山头上的洋槐花会开,走到半道,老远就会闻到飘过来的香,让夜迷人醉。走着走着,一些影子,从心底慢慢爬出来……
这样的夜,这样的星空,这样的小径,我把自己化成了一首诗的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