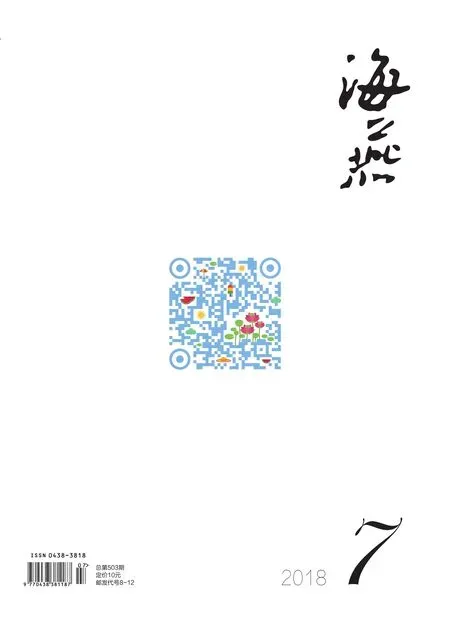梁遇春散记
□苏枕月
一
大学三年级,我们继续学习现当代文学。我的可爱的皇甫老师似乎尤其钟情钱钟书,也害得我们每天跟着他一起在“学贯中西”和“打通”这些词语中挣扎。
因为太年轻。所以每天除了翻看钱先生的《围城》或者《写在人生边上》之外,就是死背皇甫老师布置下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条了。
至于《管锥编》,我们视它为深海。虽偶而也会鼓足勇气扎个猛子进去,但一定是被呛得连呼吸也不得,钻出水面,偏又觉得不甘,透口气之后再进去,就又被呛得半死。
这样被折磨几个回合之后,我们再没有勇气进去。以至现在一看到图书馆里排着的《管锥编》,便要不自觉地深呼吸,然后望而却步。想是大学时候落下的病根了。
只是不明白,我的皇甫老师为什么只字不曾提过梁遇春?同样是作为叶公超的得意门生,我的导师何以如此地钟情钱钟书,又何以如此的冷落梁遇春。
所以,我是在很久很久之后才逢着他的。
带学生做各省的高考卷子,福建卷的现代文阅读即是做了删改的《泪与笑》。
我一向不喜欢把文学作为试题来做的,文字透露出的信息该是思想和心灵的一种接轨,而不是简单的分析什么手法或者观点。
所以,在遇到阅读题的时候,我宁可先带着我的学生欣赏文字的美丽,然后再去支离破碎地分析它。
于《泪与笑》也是。
微笑是我们承认了失败的表现,微笑是我们心灵的堡垒下面刺目的降幡。而眼泪流尽,我们的心里就都像苏东坡所说的“存亡惯见浑无泪”那样的冷淡了。
我沉醉在这样的句子中。
在寻常百姓的理解中,刑事案件通常是与“人命”挂钩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命案”。所以法院的法官在面对“命案”时,往往都是慎之又慎,而且对当事双方的调解工作也十分重视。但是俗话说得好:“人命大于天。”“命案”的调解工作却不是那么好做的。
文章末了,加了关于作者的注解。梁遇春:(1906-1932)现代散文家。
心又开始丢了。26年,仅仅是26年。
那时,我尚不知他的更多的文字,尚不知他在翻译方面的成就,尚不知他在五四时期的声名。只是慨叹,又一个如蜉蝣一样华美的生命。
看到废名给他的挽联: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花招魂。
很多人喜欢用“彩笔成梦”为题为他写文字,我则更喜欢后半句。
昙花招去了他的魂魄,留下那么多思念着他的人,我是其中的一个。
二
再一次逢着梁遇春,是半个月前的一个周日了。
大寓市场是以卖旧货为主的,自然也少不了一些古玩、字画和旧书籍。所以,周六、周日每有闲暇,我都会去逛一逛。
有时去看看绿锈斑驳的古钱币,有时去听听卖琴老人拉的二胡,更多时候是去逛旧书摊。
大寓市场的书较东山街的贵些,书种类不够多,书摊规模也都不大。很多时候,我是无甚收获的。
那天是个例外。卖书的大姐不像是书商,地上摆的书籍也很杂。书都很新,看不到什么印记,不像是图书馆下架的,也不像个人的收藏,但书的品位还都可以。在一番挑一番选一番筛了之后,我选了七本书。这其中,就有梁遇春的《春醪集》。
书竟是全新的,没有一丁点儿磨损。在一堆凌乱的书籍中,它就如一片寂寞而美丽的叶子,在静静地等我。
绿蚁新醅酒。这是我看到它第一眼的感受。不知道是那“春醪”散发的浓香醉了我,还是封皮那浓浓的绿色迷惑了我。
书的定价是22元,可这本全新的《春醪集》我却只用了2元。有一刹那,我百感交集:是为自己可以节省下几个大洋而暗自庆幸,还是为一种思想一种文化竟然贬值如斯而悲哀?我说不清楚。
有人说,梁遇春的这本书是给知音读的,因为除了封皮上“五四最美的散文”外,再无别的介绍性文字。
我知道自己并不是他的知音,所以,我看他简短的自序,看封皮里侧钟磬声的评价,甚至希望可以看到更多的那个时期那一群人写给梁的文字,废名的,钱钟书的,等等。
缩小心的距离也许不单单只是直视。我喜欢透过洒满阳光的窗子,悄悄注视那个懒在床上读书的青年。
钟磬声的评价是他的《读梁遇春〈春雨〉》中的一段文字。
钟磬声犯了一个错误,1906-1932,他竟算出了28岁。不知是作家无心的笔误,还是他有心地期求那个生命可以长一点,再长一点。
编辑犯了一个错误,将《读梁遇春〈春雨〉》中的话复制粘贴过来作为对《春醪集》的评价,终究有些不妥。
“在文中,他谈读书,论学问,聊爱情,议朋友,引经据典,而毫不迂腐造作;侃侃而谈,却无琐屑唠叨,是纯粹文学的议论,也属于文人的清谈。在小册子中,我们看到作者是如此热爱生命,赞美人生的,他对待这个美与丑、善与恶、正与邪交织在一起的世界并没有用“拍案而起“的态度来批判,而是以一种冷漠而鄙夷的方式揭露。”
终是喜欢钟磬声给他的这段评价,让我们看到这个昙花般美丽且短暂的生命是如何旺盛而饱满地绽放。
我可以走进他的文字吗?我可以走进他的心里吗?
梁遇春是最喜欢毛姆的。有人说,梁遇春就是中国的毛姆。
我开始迷上了这个中国的毛姆,这本《春醪集》将是这个季节里我最可口的甜酒。
走路时抱着它,休息时枕着它,醒着时想着它,睡着时梦着它。
醉去,深深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