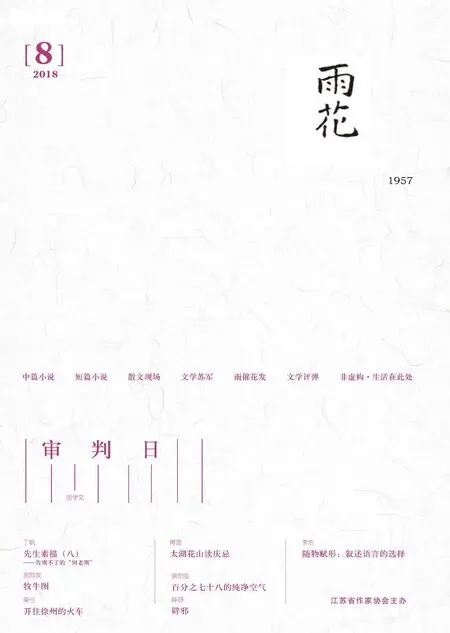喝喝茶
一
在面馆里,自然会说起各种各样的面食。刀削面,拉面,哨子面,杂酱面,拌面,闷面,炒面,烩面,面片,面疙瘩,牛肉面,羊肉面,排骨面,鸡丝面,鸡蛋西红杮面,青菜肉丝面,凉拌面,砂锅面,长寿面,香菇炖鸡面,桃花面,龙须面,担担面,口水面……
我和远道而来的黑陶兄,吃面,说话,喝酒。之后,去对面的咖啡馆里喝咖啡。
咖啡的好是前同事张舸告诉我的。我不知道她一共对多少人说过那里的咖啡好,但对我说过以后,我已经告诉过无数的人。我觉得,我像风,我喜欢赞美一些物事。
咖啡馆照例有很多人。靠窗的位置尚存一枚,坐下,继续在路上的话语。谈论的人多是从旧时的某个缝隙里突然迎面而来,我们谈论了:李白,汪伦,苏东坡,李贺,杜甫,鲁迅,沈从文,周作人,胡兰成,张爱玲,萧红,郁达夫,徐志摩,张承志,韩少功,阿炳,习习,雷平阳,孔见,李少君,赵荔红,薛原,牛汉,杨健,阿贝尔,周实,卡夫卡,里尔克,茨维塔也娃,帕斯捷尔纳克,项丽敏,蒋子丹,耿占春,福柯,萨特,德里达,南陶秃兄,周洁茹,赵瑜(山西),史铁生,刘亮程,谢宗玉,葛亮,张炜,迟子建,王国华。每一个人的名字都是一个地址,一个场域,一个色彩斑斓的世界。我们用交集的方式把这些人当作面食,充饥,填充时间给予我们的一部分空白。
咖啡馆是一个喜悦的所在,窗外是白龙南路,不远有一个公交车站牌。下车的人分别是:匆忙回家的人,步履蹒跚的老人,背着卡通造型书包的孩子,表情忧郁的中年女子,晕车后蹲在路边呕吐的穿米黄色外套的女子,三两个进入咖啡厅的时髦女人,打电话时掉了手提袋又匆匆捡起的男子,手拉着手亲昵交谈的情侣……我数不过来,所有这些人,是路灯刚刚亮起时我看到的人。每一个公交车站牌,都是让我畏惧的所在。不同的面孔从同一辆公交车上下来,却奔往不同的方向,他们有不同的人生方向,他们占据不同的社会职位,操持着不同的社会专业,甚至在内心里埋藏着不同的阴谋,这些,我都一无所知。咖啡馆里的人有不同的声音,拥挤的,愉快的,暧昧的,宽敞的,狭窄的,透明的,模糊的,饥饿的,苗条的,甜蜜的,忧郁的,曲折的,婉约的,木质的,金属的,柔软的,夜晚的,疼痛的,绵密的,朦胧的,寒冷的,易碎的,清脆的,芳香的,躲避的,廉价的,喘息的,疲倦的,陌生的,客套的,潮湿的,干燥的,尴尬的,沉默的,遥远的,虚伪的,哲学的,虚无的,后悔的,绿色的……是的,我也无法列举那咖啡馆的声音,每一个人的声音都是一条路径,是一个没有开端也没有结束的故事,是可以猜测的舞台剧,也是可以忽略的饮食男女。
咖啡依旧是要加炼乳的,那炼乳的白将咖啡的黄中和,成为灰色,成为一个模糊的红,成微笑,成香气袭人的夜。色彩常常给心情以莫名的暗示,过于黑了不好,容易陷入,过于白了也不好,容易污染。我喜欢黑和白的交合。这种嗜好,多少有些古旧,中庸,后退式的中庸,往遥远歌声里逃遁的中庸,对美好的东西不抵触,见了污浊的东西不清高的中庸。色彩的中庸常常消解一切,它完全可以沉默。
面对一杯已经搅拌均匀的咖啡,我常常觉得那是陷阱。色彩暧昧的陷阱。往前一步是洁白,冬天,甚至是初恋。往后一步是夜晚,泥泞,甚至是失意。人生的满与亏和万物的生长没有区别,平静和诗意往往得益于经历,是浓后的淡,是染了白的黑,是沾满了灰尘的清洁。
一杯咖啡的色泽,我喜欢加了炼乳的,是粉黄,是玫瑰灰,是绛紫,是青红,是土黄,是亚蓝,是灰暗的光泽,是骄傲的陷入,是风吹过的温热,是被赞美过的颓废,是值得收藏的破旧,是吞食了蜂蜜的黄莲,是唱过了歌的哑女,是难以描述的一部电影。
夜晚,入睡前翻黑陶的《漆蓝书简》,被一卷突然打开的江南震撼。所有的地方,我都想去,所有的过往,我都珍惜。我要一一念出那些村镇的名字:石门湾,河姆渡镇,新市,千岛湖镇,西屏,灵溪,斯宅,俞源,石塘,柳城,皤滩,方岩,安昌,龙游镇,报福,泗安,鄣吴,陈村,伏岭镇,建平,查济,梅山,天堂寨镇,章渡,齐云山镇,黄田,宏潭,唐模,蕲州,九资河,五祖镇,浙源,岭底,鹅湖镇,戴埠,严家桥,宝华镇,鸿声,深溪,大塍,阳山,马地村,大浮,宜城,祝塘,屺亭,万石,南方泉,淹城,丁蜀镇。
在万石镇,黑陶抄写了一种石头的红色,我觉得,那不是石头的红,那是世事的红,是爱情的红,是女人经血的红,是男人生殖器性事过后的红,是秋雨吹落秋叶的红,是第一次遇到你喜欢的人,从内心里泛起的红。那些红姿态万千,如下:
将军红,杜鹃红,贵妃红,桃红,秋枫红,石岛红,平邑红,岑溪红,少林红,太行红,雪枫红,砾红,安吉红,云花红,东方红,一品红,樱花红,龙泉红,红玉红,古山红,安溪红,西丽红,连州红,崖州红,和龙红,奶油红,玛瑙红,雪花红,万山红,芙蓉红,鸡血红,凤凰红,荷花红,灵红,广州红,龙胜红,南江红,海底红,秋景红,天山红,双井红,托里红,博乐红,乌苏红,天池红,宜昌红,三峡红,西陵红,玫瑰红,湘红,咖啡红,映山红,大悟红。
二
若是在大雨声里喝咖啡,窗外的人皆打着伞,被雨水追赶。坐在安静的咖啡馆里,便多了一份从容,这个时间,端起那杯已经调匀了的咖啡,呷一口,苦涩中的甜和世事中挣扎的自己偶有的小收获雷同,内心所想的情形一时间变得模糊,不是眼前的人和事,而是另外的风物。
小溪的机票是特价的,从很早的时候就在网上订,她天天在特价网上看。上海至海口,南京至海口,郑州至海口,上午至海口,下午至海口,晚上至海口;机票订好以后,又规划行程,需要去一个旧书院,还要看黎族的山寨,最后,要去一个咖啡园喝咖啡。
在想象里,咖啡园里开着红色的,或者紫色的花朵,结出果实如石榴般大小,里面的籽便是咖啡豆。这只是想象,我没有见过咖啡树。在书店里看到过一册关于咖啡的介绍书,图片上咖啡树色泽华丽,没有泥土,像假花一样。在那本书里,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咖啡被煮熟以后的花式:巴西咖啡,哥伦比亚咖啡,危地马拉咖啡,萨尔瓦多咖啡,乞利马扎罗咖啡,摩卡咖啡,罗布斯塔咖啡,曼特宁咖啡,蓝山咖啡,夏威夷可那咖啡。
若再往后翻,那咖啡的名称如同男女在一起亲吻之后的气息,有些甜腻,甚至有些荷尔蒙的香甜。若你在音乐里读出那咖啡的名字,你会听到钢琴乐洗过水杯,过于晶莹的杯子将生活的尘埃衬托得狼狈,只有到这些杯明几净的咖啡馆里,你才会发现自己的头皮屑,指甲里的泥,或者袜子上的一个小洞。这些生活的窘迫,使我常常鄙视咖啡馆、音乐厅、艺术馆、电影院、商场一楼高档化妆品柜台、汽车销售大厅、酒吧、会所、KTV……我常常对过于精致的生活产生怀疑,甚至厌倦、戒掉处于此种生活氛围中的朋友。但生活像一块积木,一块一块垒积成塔,成为粗俗的人,成为合群的人,成为孤独的人,成为洁净的人。
积木。在一间咖啡馆里,我突然被这个词语击中。我觉得我们所有的现在,都和过去某个瞬间开始的积木相关。是因为一张机票,小溪才会和我坐在一起喝咖啡。往后退,擦拭时间淹没的真实,觉得,委屈和寂寞也显得温暖。跋涉,常常有悲剧感,若是渡过曲折的一段,看到风景的旖旎处,便会舒心地放下,安静地看着奔跑着的他们,觉得一切都那么值得。
我喜欢在一个咖啡馆里看到别人那么热烈地活着。我喜欢那些耐住寂寞的人,矫情的人,他们制造这个世界诸多庸俗的情节,但也正是他们,让世界的颜色变得斑斓多姿。
在书店里,我被那些咖啡的名字吸引,每一杯咖啡的后面都像积木一样,或曲折,或柔软:黑色奥菲斯,66号公路,枯叶蓓蕾,梦,偷闲,伤,砌,情人,唇,香甜小品,印象主义,出走,蔷薇之恋,日出墨西哥,飞扬的滋味,诗,片断,虚荣,百老汇,情书,蔓延,声景,贝壳沙滩,迷雾,延迟,吻,浓情,小歇,大胡子,远航日志,傲慢与偏见,舞动华尔滋,马车……
我常常觉得生活被一些追逐意义的人撕开、拉长,甚而延伸。
在饥饿的20世纪初,刚刚进入海南岛的咖啡,被当作充饥的食物之一,那些贫穷的乡下人,用舂米的工具将咖啡豆捣碎,煮沸,加一把盐巴,当作早餐。这种习惯一直维持到现在,电视镜头里,那个朴实长相的农民对着镜头说:天天都喝,天天都喝,不喝没有力气。
他们的牙齿很黑,像是一个比喻句,那沉淀物,与其说是时间和污垢,不如说是对一种食物的尊重。
香水最初是治疗脚气和皮肤病的,世界上最昂贵的香水的配方是路易十六日记里记载的某个配方,目前,此种香水的味道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表征。可是,这种配方,不过是路易十六当年治疗自己的皮肤病的。
坐在那个音乐适宜的咖啡馆里,看着窗外的大雨淋湿河流、绿树、花裙子、微笑、嘲笑、孩子的问询、村庄、街道上的牛、果树的歌唱、猜测与远道而来的疲倦……我突然觉得,咖啡是一个被人为抢走的食物,当城里人发现五谷杂粮的营养更均匀的时候,乡下人正在渴念馒头的白。这个时间,用一个精粉的白馒头换一个五谷杂粮的窝头,容易极了。然而,许多年以后,当乡下人也喜欢吃窝头的时候,窝头早已经被穿上了好看的衣裳,成了一个阶层的消费标志。
疏离。发现。断裂。推介。享用。生活常常被一群意义主义者无端地割破,他们制造概念,并获得利益。理智在生活的趣味面前常常如饥饿时遇到食物一般,我一直相信这一点,能抵御的,根本不是诱惑。在真正的诱惑面前,我们都是陷入者。
我就陷入进一杯咖啡里,福山咖啡,海南澄迈县福山镇,隐藏在果园里的咖啡,抽烟的人在四周说笑。浓咖啡的色泽更沉着,像一个中年人。有一个女服务员的嘴唇涂得很红,让我想起印章,或者更形而下的画面。淡咖啡的色泽偏于哀怨,像曲子弹奏完后仍然沉浸在音乐里的听众。
伞是湿的。刚刚被我们嘲笑过的人进来了,他也是湿的。昨天一整天都是湿的。小旅馆的名字是湿的。那个旅馆老板的小女儿,头发很长,她在外面的街道上叫另外一个人的名字,她也是湿的。我们在路上买的一份报纸是湿的。去一个小饭馆吃一份鱼香肉丝是湿的。那个饭馆老板找回来的钱是湿的。三轮摩托车的声音是湿的。扔到路边的烟蒂是湿的。在饭馆旁边打麻将的人的争吵是湿的。回到小旅馆以后,我和小溪脱下的鞋子是湿的。电视里正在哭泣的女演员是湿的。房间里的水龙头是湿的。从小旅馆到咖啡馆的那段路程是湿的,手机短信里的天气预报是湿的。停车场里的车是湿的。鸟叫声是湿的。我们把伞合上,觉得,在雨天里,生活的所有情节,都是湿的。
十五元每位。雨声免费,微笑免费,刚刚被我描述过的女服务员的口红免费,前面的河流免费,旁边嘈杂的谈话免费,可以触摸的失落与意外免费。在一个小镇里喝咖啡,我们所准备的情绪太多了,一切繁杂的程序,这里全没有。这里只有咖啡,浓的,淡的,两种,炼乳和沙糖两种。
花式的,充满诗意的名字,这里没有。福山镇,这里有大群的牛羊,和漫山的果树,有开怀的笑和肆意的争吵。这里是世俗生活的最为本真的剧场,不加任何广告,不收任何门票。这里的好,我差不多在喝下一杯咖啡以后,通通体味到了。那杯加了炼乳的咖啡告诉你一切秘密:一、苦涩的年代过去,会有香甜的回味;二、大雨淋湿的青春像一簇草,会被牛吃掉,也会铺满你未来的道路;三、微笑是甜的;四、走到远方去,如果不能,那么,请给远方的人写一封信;五、相信雨会停下来的,湿了的那一段青春总会被晒干;六、扔掉已经被雨淋湿的字条,那上面的号码已经模糊;七、把一杯咖啡趁热喝完,不要让一杯咖啡像青春一样荒废掉;八、傻一点,再傻一点,请不要计较一杯咖啡的苦,生活太甜了,我们需要这些苦味来中和一下;九、贫穷的时候请保持贞洁,富有的时候请不要贪婪;十、若是加了太多的糖,请不要告诉别人,你的咖啡太甜了。
三
那一日,在陶园,和南陶秃子喝苦丁茶,被那叶片瞬间绽放出的绿所惊吓。
那是一种有态度的茶叶,它主动出示的色泽暗暗注定了它有阴谋。果然,头遍茶,苦味太浓了,我不知深浅,欣喜地喝下一口,立即哑了言。光滑如微笑的绿,让我想到初夏刚刚打开的心事,可是,入口,吞咽后,我被那结实的苦带到一个不堪回首的童年里。
苦丁茶,是一个矛盾的比喻。
我自小便不是一个能吃苦的人,患病总是要吃药的,不论药丸的大小,我必须一片一片地吞咽,还要仰起头来,做几次滑稽的动作,方能完成。药的苦对比着疾病的痊愈,所以,自小,我总是一个不受大人待见的孩子。
如果药物的苦来自味觉的侵袭,那么,生活中的苦则更多地指向毅力或者品性,然而,自我有记忆起,尽管我敬畏身边所有有力气的长辈,但我依旧不是一个热爱劳作的孩子。万不得已的情形下,我表现出莫名其妙的聪明,我自小就有超出常人的记忆力,大约念到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会给身边的小伙伴讲几十万字的《薛刚反唐》。
我常常被我的个人史所困惑,一个乡下孩子,不能吃苦,在长长的一生里,怎么能够走得更远呢?
越是不能吃苦,父母亲便越会伺机锻炼我,至今想起,我仍然并不十分感激他们。因为,他们所刻意提供的活计全都是为了应付以后的生计。那时的乡下,逻辑十分地朴素,吃的苦最多的那个孩子一定是好孩子,能吃苦的孩子定能操持家庭,娶上漂亮的媳妇。
规律大致是这样。
我已记不得,我是如何挣脱父母亲的试验。大约念了初中以后,他们便不再逼迫我学习品样繁多的耕作。我十分感激我的哥哥,他在我人生最关键的时候做了我的反衬,他坚决不热爱学习,以致于父母亲很早便看上了他的力气,吃饭的时候赞美他能吃,夏天的时候赞美他黑黑的胳膊。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父母亲对我很是失望。他们知道,作为一个从小意志不好的孩子,以后很难有大的出息。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我离他们越远,他们越发现,自己的判断是错的。幼时的那些小机灵,并没有定性一个人的一生。
人总是在环境的烟雾里看清前途,在世事的高温里被铸成陶瓷。
我对苦味的理解,随着时间的稀释而稀释,少年时不喜欢的食物,现在已经离不开了。早些年做的勇敢的事情,现在觉得那么荒谬。
然而,唯有对一些色彩的执着经年不变,绿色便是其一。对一些味道的反感经年不改,苦涩便是其一。
那么,现实总会如此巧妙地给出问题,你喜欢绿色,那么,我给你一杯颜色如春天某个明媚下午的绿茶,你不喜欢苦涩,便巧,这杯茶是苦的。
人生大抵和这杯茶相似,一扇门打开的同时,另一扇门也会关闭。
为了能更好地体味这苦丁茶的后半程的风景,我喝了二道茶。色泽变淡了,仍然绿得像春天某个明媚的下午,但却是被稀释了的下午。有些失真。
我试图从这杯茶里喝出喜悦来,苦涩的却又明媚的绿,象征着我已经被时间偷去的青春,我喜欢的而又擦肩而过的女人,我的某一枝被风吹去的柳枝,我的1986年夏天的一场淹没我叫喊的大雨,我的一双露出脚趾的袜子,我的一段满是羞涩的骄傲,我的丢失了自信的某个上衣口袋,我的被几枝香烟燃烧完毕的星期六中午,我的沾满麦秸秆香味的寻找,我的无法言说却足以让我掉泪的青年时代。
青年时代。这样说真浅薄。我知道,我还年轻。几年前,我去一所民办高校代课,第一节课,讲书写对一个人的意义。我说到,我年轻的时候,以为书写就是讨好女人,现在,我变了,我认为,书写更多的是讨好自己。
我的那些个打扮得时髦的学生,他们,都莫名其妙地看着我,然后哈哈大笑,我是他们的老师中年纪最小的一个,学生中有胡须飘扬者,很是成熟。于是,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论是在他们交上来的作业里,还是在私下的交谈里。我的那句“我年轻的时候”成为流行语。的海水里,沉淀,深入,变成了不知所终的未知。
那杯茶水凉了。房间里的光线变暗,茶水仿佛分了两层,贴近茶叶的部分深一些,上面的浅一些。我喝了一口,入口的凉还夹杂着刚才我们所说话语的甜味,一点一点地品咂,那苦味便像线绳一样缠绕了上来。
温热时的苦是浓郁的,像偷情的人刚刚相见时的亲热,而凉茶的味道则接近于想念,有些淡远,又有些怅惘。
南陶秃子也好奇于我的描述,端起杯子,深深地尝了一口。反复对比后,认为:是很好的滋味。
把一杯浓郁的苦丁茶慢慢冷置,自然变凉以后,苦涩被时间稀释,茶水中会有一股饱含了世事况味的香甜弥漫开来。
安静地放一放,茶水如是。我们心事里的苦,跋涉路上的苦,也是如此。
南陶秃子又冲泡了一壶苦丁茶,热烈的香气扑鼻而来。我们彼此对望着,笑着说,要放一放,不急,不急。
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可以放一放。不是吗?
是啊,年轻不过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一杯茶水的温热与凉爽便解释了这一切。
那天下午,我和南陶秃子交谈了很多,大约都是从这一杯苦丁茶开始的,我发现,从这杯茶开始的交谈,就像一个断了线的风筝一般,我们越说越遥远,我们的话像一块重力很大的石头,我们把这块石头投入到浩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