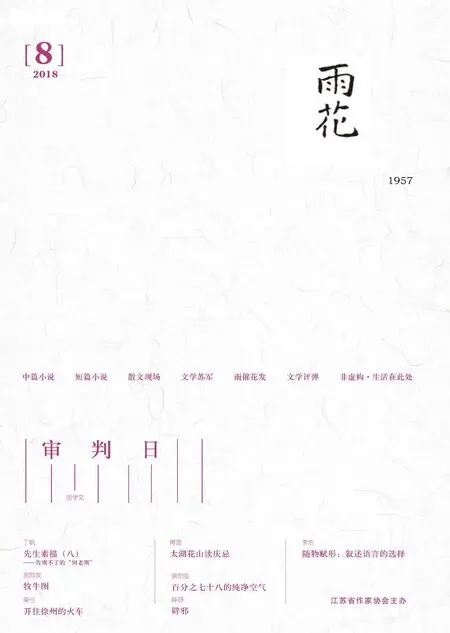我带你去个地方好吗
又闯了一个红灯。这是第三次了,她说,我今天是怎么了,魂不守舍。少顷,她又说,你真的让我很紧张。
她开得并不快,缓缓地接近斑马线。一拨行人匆匆穿越斑马线,已经过去了一大半,她往右打方向盘,绕过行人的尾巴,开了过去。你以为她要将车停到边上,其实不是。她继续往前开。刚才没变灯。红灯。你闯红灯了,你说。
第一次闯红灯,是过一个路口,前面的车抢了黄灯,轮到她时已经是红灯了,她仍然开了过去。
第二次闯红灯,是她根本就没意识到那儿会有灯,而且还是红灯。
这是第三次,她说的没错。
天空灰蒙蒙的。夜晚张开巨大的翅膀,遮盖整个城市。夜色和灯光融合在一起,给人以恍惚迷离之感。你们随意拐了几个路口,现在的道路是陌生的。你们不知道要往哪里去。她说,你不怕我把你卖了?你说,恐怕卖不出去,谁会要一个老男人呢?
然后是沉默,空气像绷紧的丝线。
又过了一个路口,前边的车少了许多,道路畅通。但她并没提速,还是不紧不慢地开着。后边的车一辆接一辆超了过去。
这样的天气,以前总是会烦躁,今天却觉得竟然有些诗意。你说。
她没有说话,但打开了天窗,让凉爽的空气灌进来。已经立冬了,但冷空气没来,还是深秋的感觉。她问你最喜欢什么季节,你说秋天。她说她也喜欢秋天,喜欢秋天的宁静。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不要想,直接说出来。绿色,你说。这是春天的颜色。你想问她喜欢什么颜色,但是却没问,你对颜色实在没有什么研究,这不是你擅长的话题。其实你说你喜欢绿色,也不是太确定。后来吃饭时,看到饭店的灰蓝色花边的碟子,你说你很喜欢这种花边。她说她知道你喜欢什么了。而你却不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颜色。从喜欢的颜色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性格,她说。你们没有将这个话题进行下去。
过了一个涵洞。车辆越发稀少。夜晚像大鸟腹部的羽毛一样恬静、安详、柔软。轿车如同摇篮,在温柔的夜色中缓缓漂浮。
我现在还很紧张,她说。
我也是。你确实也很紧张,心脏都不知道该怎么跳动了,好像有一只手在揉搓着它似的。你不善言辞,致使你们中间总是出现短暂的沉默。
看到你的第一眼,我心就乱了。她已经不再矜持了,心灵的门向你渐渐打开。
那天你去得最晚。
我下午处理点事,想着能准时赶到,可是路上堵车了。
那正是堵车的时候。
你完全和张冲介绍的不像。
他是怎么介绍我的?
不告诉你。
很难把一个真实的人与想象中的样子重合起来。
这倒也是,还记得聚会结束,在楼梯上……
我们看了一眼,那一眼很特别,仿佛不是用眼睛在看,而是用心灵在看,我相信我们彼此都读懂了对方的眼神。
是的,我好像看到了你心里。
一束光打进来,照亮了那辉煌的时刻。人生会有某些时候,你感觉被一束神奇的光所照亮,时间熠熠生辉,瞬间变成永恒。
这是第一次见面,在一个公开场合。张冲请客,一大桌子人,她是重点。其他人相互都认识,惟有她只与张冲认识。那天很热闹,每个人都非常兴奋,抢着说话。她却沉稳安静,只是听,偶尔说一两句,那也是别人问她问题,不得不回答。你们一个坐桌子这头,一个坐那头,离得最远。但是,正对着。你始终能看到她。她也能看到你。你们没让目光碰在一起。一次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聚会。
我以为我们不会再见面了,她说。
我也是。这种场合,一般都是吃个饭,聊会儿天,然后大家作鸟兽散,各忙各的,能不能再见面不好说。
可是,你们不但又见面了,而且还见了三次。上次,就是上次,你们谈到朋友这个话题时,产生了分歧。你认为你们可以做朋友,纯粹的朋友。她不相信有纯粹意义上的异性朋友。你说也许会有些好感或者有些暧昧,但这可能正是做朋友的基础,很难想象两个人没有一点儿好感没有一点儿暧昧还能做朋友。这是个灰色地带。她说自己是个绝缘的人,从没涉足过情感地带,因为怕受伤害。她用的词是防患于未然。她多次使用这个词。重复即强调。你当然明白这等于说Stop!Stop!Stop!你不是劝说她,也不是开导她,你说你只是说出心里的真实感觉。她可以将这看作是最高的赞美,一个不容易动心的人为她动心,足见她多么有魅力。你尊重她的选择。保持距离,给中间留下灰色地带。她那么理智,这也许是她事业成功的法宝吧。你显得幼稚,也有些尴尬,你选择了坦率,你对自己说没有人会去嘲笑一个如此坦露心迹的人。你很紧张,她也很紧张,你们都很紧张。空气也是紧张的。在车里,那么狭小的空间,你们能听到对方的呼吸和心跳。后来,她自嘲说她这是阿Q精神胜利法。这比喻并不是很恰当,但你听懂了,理解了,不再那么紧张。告别的时候,你握了一下她的手,并在她手背上印了一个吻。她的手背柔软得像一片新雪。
后来她说,那天我应该下车,那样会出现一个电影中的经典镜头。
拥抱。
是的,她说,我很想下去,可是没有,我很后悔。
车越来越慢,仿佛空气变成了黏稠的液体,影响了车速。这地方很陌生,我们都不知道是哪里,也不想知道。路上几乎没有车,说明这儿很偏僻。肯定是郊区,没有高楼大厦,甚至没有房子,周围是开阔地。夜的翅膀在这儿垂得更低。车停了下来。
时间能够静止该多好。
两颗心脏都在剧烈地跳动,你能够感觉得到。
她说她已做好准备,敞开自己,好好去爱一场。这应该感谢你,是你让我改变的,你让我看到了我身上还有另一个我,一个和以前的我很不一样的我。
伍尔芙说过人有四个层面:我,非我,内在的我,外在的我。你身上还有两个我有待发现。
我身上只有两个我。
我不知道我身上有几个我,你说,也许三个,也许四个,也许更多,认识自己是很难的,和认识世界一样难。
她说了解和理解是情感的基础,没有这“二解”,何谈爱情。而你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你说,一个人的经历和认知,世界观和价值观,都写在脸上,一眼就能看出。情感是非理性的,并不因知道得多或少而发生变化。爱,是当下——此刻——的心理状态,是心脏的狂跳,是喉咙发干,是肌肉绷紧。身体不会欺骗我们。你对她了解很少,仅限于个人简历,干巴巴,没有血肉。而她对你的了解则多得多,第一次见面之后,她回去立即上网查了你的资料。她还觉得了解得不够吗?她多少认同了一些你的观点,即情感是非理性的。
语言的表达有很大的局限性,你不满足于此。你想吻她。你这样做了,她没有退缩,也没有配合,但有些慌乱,发出了呻吟。她的嘴唇柔软灼热。你用力吻她。她受不了你的吻,张开嘴,又呻吟一声,把舌头给你。然后,她回应你的吻,她吻你。吻点燃了你们的血液,吻让你们饥渴。有一辆车经过,你们没有理会。接着,有几个工人经过,你们的嘴唇分开,但身体还倾斜着。这个姿势有些不自然,也不舒服,但你们没改变,因为这样便于随时开始下一轮接吻。空气更紧张了。你们心跳得厉害,你们不敢看对方,目光碰撞会火花四溅,你们怕引起火灾。几个工人走过去后,你们又吻到了一起。路灯的光洒下来,像暖色调的轻纱帷幔。时间消失了,空间无限地向外拓展。佛说,这是一个婆娑世界,婆娑即遗憾。此时你们跳出了婆娑世界。你们没有遗憾,此时此刻。不知过了多久,不知过了多久,不知过了多久,你们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有几个中学生(他们穿着校服)经过。这个时间,如此偏僻之处,几个中学生经过,他们要去哪里?你们看着他们走远。她说,我很怪的,晚上走过去的人,我总要看他们有没有影子。你不是要讲鬼故事吧?打住打住,千古别提鬼,我害怕。每个人都有影子,你说。的确如此。
她说,不能再吻了,我受不了。
我也是。
她深吸一口气,我带你去个地方好吗?
好。
我还没说去哪里你就说好。
我不管,天堂也去得,地狱也去得。
打火,挂挡,松手刹,宝马缓缓朝前滑行。
知道怎么走吗?
有导航。
过了一条河,等会儿又过了一条河,也许是同一条河,你不能确定。你不介意身在何处,也不介意去往哪里。你只知道你和她在一起,她开着车,带你去某个地方。什么地方?去干什么?她说,先不告诉你,保持点神秘。
没多久,上了高速,她踩下油门,风驰电掣。
高速上车不多,开车很爽。离城市越来越远,进入旷野之中。路两旁没什么灯光。夜色温柔。
第一个出口,她没出。
第二个出口,还没出。
第三个出口,仍没出。
会去哪里呢?你心里琢磨。笔直的道路像一支箭,射向大海,这是你头脑中的画面。这画面旋即生成动画:色彩绚烂,充满动感,道路是一个飞翔的箭,宝马在箭杆上飞驰。宝马获得了两个速度。
夜晚澎湃的大海该安静下来了吧,海面温柔地起伏,黝黑闪光如同劳动者的脊背。潮湿的空气中弥漫着盐的咸味。海那么平坦,却不能行走。这是一个著名女诗人说的。如果能行走,你们会在大海上散步吗?或者,此时就要去大海上散步?
想什么呢?
想大海,想我们会不会去海边,建个小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她笑了,喂马,劈柴,再生一堆孩子。
周游世界。
快成神仙了,她说。
其实这是一种简单的生活,也是不难实现的生活……
减速,下高速,钻过一个涵洞,开上一条乡村小道。令人吃惊的是小道上有这么多车,运土的,运钢筋的,运垃圾的,还有小面,等等,一派繁忙景象。道路只有两个车身那么宽,双向车都很多,错车得小心翼翼。超车就别想了,根本不可能。
这条路不可能通向大海。去哪儿?
学校。
你不明白这时候为什么要去学校,再说,如此偏僻的地方会有什么学校?
去看皮皮。
皮皮?
我的狗。
她说过她养了一条狗,是条杜宾犬。世界名犬。这条狗是她捡的。当时狗很小,可能生了病,被主人遗弃了。她看到小狗时,小狗可怜巴巴地看着她,意思是,救救我,救救我。于是她把小狗抱到宠物医院救治,竟然救活了。现在已经长成了一条大狗。四十多斤重。它叫皮皮。
狗学校?
是。
拐下这条路,停下来。前边没有路灯,是一片荒野。一条更小的路,不知通向哪里。肯定快到了,你想,这样的小路不会太长。
你们在车上接吻。你的吻有穿透力,这是她说的。可以吻得如此之好,是你所没有想到的。最棒的吻!可以和最棒的性相媲美。深入,融合,飞翔,陶醉,忘我,不知今夕何夕,不知身在何处……
吻了一阵,有人从车前经过,你们分开。她下车去给狗买吃的。拐角的地方有个小超市。你在车上,等着,恍恍惚惚,再次失去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她回到车上时,你还在发怔。想什么呢?什么也没想。你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只是存在着,此刻,当下,你感知到自己的存在。还有,爱的存在。她不再说话,打火,挂挡,松手刹,车缓缓启动,驶入黑暗之中。
一个很大的院子:宠物训练基地。这就是狗学校?你问。是,她说。院里一边种了很多菜,白菜和芥蓝。另一边是个果园,低矮的苹果树早落光了叶子,树枝也被修剪过。往前走,是训练场和大房子,大房子里灯火通明,房子前是一个小广场。车停下来,大房子里传来狗叫声。她拿了给狗买的吃食——火腿肠,还有一条烟。
进门。一个很空旷的大厅。有几个女人在逗一只小狗玩,小狗跑来跑去,叫得也很欢。小狗跑过来,到你们身边时,又突然折回去。其中一个肥胖得快将衣服扣子绷开的女人娇嗔地训小狗,萌萌,别闹!她朝你们笑笑,意思是小狗多可爱啊。一个小伙子过来接待你们。她与小伙子认识,叫出他的名字。我来看看皮皮。小伙子领你们到一个小屋里,里边有两个铁笼,每个笼子里关着一条狗。其中之一就是皮皮。她将那条烟给了小伙子。小伙子放出皮皮。
皮皮是一条黑色的杜宾犬,将近一米高,眼神忧郁,面无表情。如果将它放出去,你可以想象,它奔跑起来的样子:黑色的绸缎般光滑的皮毛与夜色摩擦产生火花,如一道耀眼的闪电,倏忽远去。
皮皮冲到大厅里,茫然地跑一阵,又折回来,然后又跑远。对它来说,大厅显然是太小了,到处是边界。它跑向那只小狗。那只小狗和皮皮相比简直就是个小不点儿。它狗仗人势,很凶地冲着皮皮吠叫着。皮皮跑到它跟前站住了,不明白小狗为什么叫得那么凶。皮皮跑开了。
她叫皮皮,皮皮不理她。
它是故意的,她说。
皮皮扑向小伙子,小伙子叫它站住,它站住了。但旋即又跑开了。
皮皮扑向你,你有些害怕,但保持着镇定。小伙子是驯狗的,有他在,不会有危险的。他既然敢把狗放出来,说明没有危险。尽管如此,你心中还是忐忑。皮皮有些烦躁。一条烦躁的狗,你能不害怕吗?
她看皮皮扑到你身上,呵斥皮皮。皮皮跳开了。也许是听到了她的呵斥,也许皮皮就是这样子。
她想摸皮皮的头,皮皮躲开,不让她摸。
皮皮不往她身上扑,与她保持着距离。皮皮甚至不看她。
她有些难过。皮皮被遗弃过,心灵受过伤,它是不是觉得又被遗弃了?
她的眼睛湿润了,她控制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她剥一根火腿肠,递给皮皮。皮皮犹豫一下,走过来,将火腿肠叼走,转过身去,一口吞下。她又给皮皮喂了几根火腿肠。在皮皮吃的时候,她挠挠皮皮的脖子,这次皮皮没有躲开。皮皮像一个委屈的孩子,抬起头看着她,眼睛也分明是湿润的。她让皮皮趴下,皮皮仿佛没听到指令。来,握个手,她说。她伸出手,皮皮也没理睬。皮皮和她还有些生分。看上去皮皮的状态不是很好。它一岁多,个儿大,瘦,腿长。她对小伙子说,我想带它出去走走。小伙子说,没事儿,去吧。
皮皮出门后,就朝果园里跑去。它跑起来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快,身子还有些摇晃,有几次差一点儿摔倒。它突然蹿到你跟前,朝你身上扑,你还是很紧张,但没有躲避。
你不怕?她问。
不怕,你说。
它不往我身上扑,她说,它还在生我的气。
狗学校,它住不惯。
我想也是。
她喊:皮皮,过来。
皮皮跑过来,到她跟前又跑开了。
你看——
还需要时间。
她打了个哆嗦。毕竟入冬了,夜晚还是很冷的。
别感冒了。
好吧,她说。
她喊皮皮过来,可是皮皮不听她的话。她将小伙子叫出来,让他将皮皮弄回屋。
小伙子喊:皮皮,过来!
他的声音很严厉,皮皮不敢违抗,乖乖过来了。小伙子抓住皮皮的项圈,将皮皮连拉带拽弄进屋里。你和她跟到门口,隔着玻璃门,看着皮皮。皮皮也看着你们。小伙子与她告别。你一走就好了,他说。
她有些落寞。
回到车上,她一句话也不说,缓缓将车子开出狗学校。穿过一片寂静的田野,走上车流如织的狭窄土路。这条路让你产生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是在梦中。右侧有大片的晕黄的光线,好像那边此时黄昏刚刚降临。正前方,很远的地方,则透出一些青色的光,好像那里正在展露曙光。多么不真实啊,你想。过了一会儿,开上高速,道路空旷,你同样感到不真实。起了雾霭。车灯照去,你看到雾像一群受惊的鹿。
人的一生中,难免会有些时段你感到像是生活在梦中,时间显得荒谬,空间也是扭曲的,一切都是虚幻的。你现在就处于这样的时段。这夜晚,这道路,这雾,你,她,亲吻……这一切是真实的吗?
你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她问。
我不知道。
不知道?
因为不切合实际。
说说。
我想在喜马拉雅山上盖一个小屋,和心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每天看日出,呼吸新鲜空气,爬山,还有——
还有什么?
还有……做我们想做的,一切。
你和我?
对,我和你,我们!
她笑了,说,这想法不错。
她打开CD,里边飘出舒缓的音乐。你沉浸在音乐中,想象你和她,站在白雪皑皑的山头,看着白象似的群山,轻风拂面,阳光洒落。你抓起一把雪抛向她,她头一歪,雪落在她身后,头发上沾了几朵雪花。她马上回击,也向你抛了一把雪。你们打起了雪仗,欢声笑语飞向高空。一只鹰在空中盘旋,是唯一的观众……
我们这是到哪儿了?她问。
你看看窗外,雾茫茫,你们仿佛在云海之上。不知道,你说,往前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