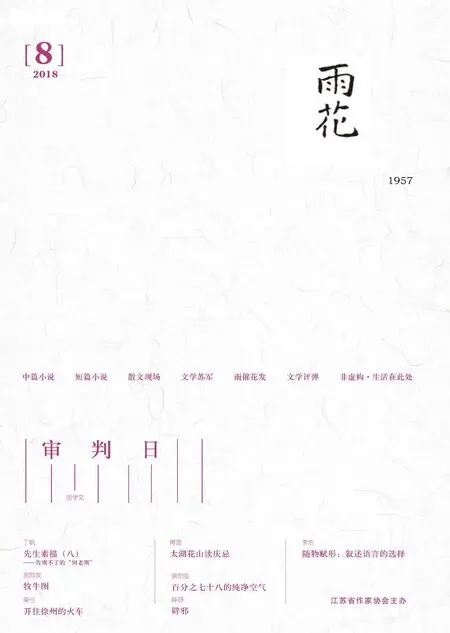先生素描(八)
——告别不了的“何老别”
正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新文学史料》主编郭娟女士电告: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鲁迅、冯雪峰研究专家陈早春先生今晨逝世了。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也不胜感慨。身边的老一代知识分子一个个离世,我在思索一个时代的叩问:他们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他们都是带着一段非同寻常的历史和故事离开了我们,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我追随叶子铭先生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编纂《茅盾全集》的时候,与社里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王仰晨先生、陈早春先生和张伯海先生了。他们对待工作的认真态度和严谨作风,让我一辈子感动和受用,同时他们具有独特个性的行事风格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的心中树起了一个做人为文的标杆。像陈早春那样不畏强权、坚持真理的学者让我崇敬有加。
在北京,有两个让我终生忘不了的单位:一个是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另一个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那里面先生们的人品和学问深深地影响了我26岁以后的学术生涯。在唏嘘不已的悲痛中,我想为他们写下一点文字,不仅仅是寄托我的哀思,更重要的是,我要让我的学生们也了解到先辈学者在做人为文时的价值观念和始终如一的定力,千万不能让知识分子的人格在这个诡异的消费文化时代里消失殆尽。
因为许志英和徐兆淮的关系(他俩都是1978年前后从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调回南京工作的),我与何西来先生认识得很早。那是上个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何西来风尘仆仆地从北京坐火车来到了南京,先到许志英先生家里落脚,许先生让兆淮和我一起到他家会合,口中嚷道:“何老别来了,何老别来了!”一脸兴奋的样子,可见他们之间的友情是多么深厚了。我从平日许志英与徐兆淮的言谈之中获知,文学所但凡经历了那场轰轰烈烈运动的中青年人都有绰号,我寻思,这个人的绰号怎么会叫“何老别”呢?后来才知道这个外号的来历,这在杜书瀛先生的悼念文章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张炯曾写过一篇批判你们的大字报,里面说的那个‘个别别有用心的人’就是指你。憨厚的蒙古族同事仁钦·道尔吉汉语水平差点劲儿,总是念成‘个别别’而迷惑不解,大家当成笑话,从此你就有了‘何老别’的外号。”
还没有进许老师的家门,就听见屋里有朗朗的笑声,进门一看,只见一位大汉端坐在小桌前吃着面条,其海碗如小脸盆般大,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大口吞食,吸溜有声,连蠕动的喉结里发出的声响仿佛都掷地有声,煞是豪气。仔细端详,但见大汉浓眉大眼,二目炯炯有神,眼光咄咄逼人,眉间那道川字型皱纹,透出的是凛凛威风,初一见面让人顿生畏惧,我立马想到了一个电影演员的模样——中叔皇,英气之中的威严,让人肃然起敬。
用高大威猛、声如洪钟来形容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似乎不太合适,但是,当我历经四十年的人生沧桑以后,我顿悟到的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正是缺少了何西来那样可以肩起闸门的身板骨吗?
其实何先生是一个十分和睦可亲的人,谈吐诙谐幽默,性情随和,但是遇上大事却自有主张,是关中大汉中的标准偶像。常常听许志英和徐兆淮先生在聊天中谈及他们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离奇诡谲的故事,也是第一次知道了文学所“狄遐水”这个笔名的来历,知道了文学所那时候林林总总的许多趣闻逸事背后的人品表现,尤其是后期在“五七干校”发生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那是一段不可磨灭的辉煌苦难岁月。作为那时冲锋陷阵的领军人物,“何老别”同志的故事也是大家口中念念不忘的谈资,而与之交往并不深的人,似乎只能看到他严谨治学的一面,而看不到他那种刚勇坚毅的强大内心。
何西来的口才甚好,如果说声若洪钟、激情四射是其天生的基因条件所致,那么他那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恐怕是后天读书训练所致吧。1985年,首期文学研究所和《文学评论》编辑部举办的进修班(俗称“黄埔一期”)上,何西来先生口若悬河的演讲迷倒了许多学员,让许多人成了他的粉丝。说实话,今天看来,他当时的文学观念并不是很新,但其让人念念不忘的是他那大段大段背诵古诗词和伟人名言语录的功夫和本领,可谓是出口成章,滔滔不绝。所谓“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强调的就是童年记忆的重要性,而何西来五岁就入村塾发蒙,记忆功能从小就受到了训练,其“童子功”让他在后来的读书生涯中受益匪浅。亦如老舍先生所云:“只有‘入口成章’,才能‘开口成章’。”显然,他的出口成章是从小到大入口成章训练而得,可惜吾辈只能望其项背,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文学教育更多的是那种教化式的理念灌输,大有吾生晚矣之憾。作家马步升这样描述他的授课:“先生博闻强识,授诗词鉴赏课从不看讲稿,从《诗经》《楚辞》到毛泽东诗词,仅记在我课堂笔记上的就多达六百多首。”是的,后来有许多人都听过他的课,让人牢牢记住的是他背诵的本领,却忽略了他文章的犀利与老辣。
何西来195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留校任助教一年。1959-1963年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研究生班,师从何其芳。1963年研究生毕业即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生院文学系主任、《文学评论》主编。著有《新时期文学思潮论》《文艺大趋势》《论艺术风格》《文学的理性与良知》《文格与人格》《探寻者的心踪》《新时期文学与道德》《横坑思缕》《艺文六品》《绝活的魅力》等专著。我不敢说何西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是中国20世纪至21世纪初不可或缺的著述,但是,我可以这样断言:他在某一时期的文学理论和文学评论著述是引领着中国文学朝着正确方向前行的航标灯,是拨乱反正的先锋,是倡扬改革的号角。仅一部《新时期文学思潮论》就影响了当时的许多理论家、评论家和作家的思想观念,这是可以入史的著述,虽然它并不臻善至美,但是,它带着历史的年轮,成为文学思潮史上的一部典范之作,连作家王蒙也认为:“他的热情、才华、学问永在人间。”
记得1986年为纪念新时期文学走过了十年,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在北京国谊宾馆召开了“新时期文学十年研讨会”,原定80多人的规模,哪知道后来竟涌来了400多人。那是一次文学评论、文学理论、文学思潮、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研讨的盛会,作为文学所的副所长和《文学评论》的副主编,何西来天天钉在会议上,主管一切会务,正是由于他和所长刘再复先生的宽容,那次会议才开得生动活泼,各种各样的观点都释放出来,各路“黑马”都奔腾呼啸而来,才使得那次会议载入史册,成为新时期以来许许多多思潮、现象和作品的滥觞。“刘何搭档”一时成为文坛的佳话,他们包容开放的胸怀和对文学的责任与担当亦让今人久久怀念。
何西来去世后,刘再复先生撰写的挽联令人深思,其联除足以证明这对“黄金搭档”在当时文坛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外,更说明了再复先生对何西来先生的倚重:“华夏赤子,明之极,正之极。品学兼隆。满身侠骨顶天立。往矣往矣,痛哭西来兄竟永别远走。人文清光,诚亦最,真亦最。慧善双就。一腔热血照我行。惜哉惜哉,淘尽东流水犹难洗伤悲。”我认为,这幅挽联虽然不是很工整,但是作者的心境却表达得十分到位。
“光明正大”是对何西来先生人品的最高褒奖,文坛口碑极好的何西来先生一生之中给许多学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的刚直不阿的人品,许多人将其归于先生的性格特征,我却认为,这种性格是在知识分子经历了许多次大风大浪的考验后才得以大彻大悟的一种品性与良知,有了这样的人文底色,何愁不能唱出一曲士子铁板铜琶大江东去的壮歌呢。可惜吾辈之中,能有多少像他这样守护自身人文道德的洁癖者呢?当年文学所还有中国现代文学的大儒樊骏在,还有“狄遐水”在,我们还是能够从阴霾的天空中窥见一片云霓的。
“品学兼隆”是说,只有具备一流人品的学者,才能拥有治学的本钱,才能获得“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意志”的学问境界,否则,知识积累再多也枉然,只能做一个书蠹而已,因为他不能产生思想,没有思想的学者,如同行尸走肉。
“侠骨柔情”是说,在治学的大节上,先生明志致远,对文坛的种种事件保持着自己独立的看法,尊崇一个知识分子的法则和底线,敢于对非理性的文学和批评坚持批判的态度,敢于仗义执言,有侠义风骨;在生活的小节上,对待他人和亲属,这个关中大汉,却有着鲜为人知的柔情的一面:何西来先生在外乐观开朗,家中却有不幸的生活,因为女儿的病,这个关中大汉暗自神伤了大半辈子。我亲眼见过他和许志英先生谈及家累时说的那句话:我走了无所谓,就是放心不下女儿。说到这里,他的眼圈红了,晶莹的泪珠在眼眶里滚动……我们曾一道去过句容宝华寺,他静默在佛像前,双手合十,我想,他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一个无神论者,而当内心的痛苦无法排解的时候,他也无奈地求助于菩萨了。
“真诚率直”是说,作为一个在京的“陕西帮”的文学批评圈内人,他的真诚和率直感动过许许多多的陕西作家,在“陕军东征”中,他和雷达先生一直扮演着中坚人物的角色,对陕西作家作品的进步做出了很大的贡献。除了自己动手写评论文章外,还在各种场合为之鼓与呼。
1986年的新时期十年研讨会结束之后,一帮陕西的评论家在一起喝酒,当然也是祝贺何西来主持的这次会议圆满成功,那个时任《小说评论》主编、酷似鲁迅先生样貌的小老头王愚兴奋不已,一下就喝高了,不小心摔在地下,把脑袋磕碰破了,去医院缝了好几针,可把何西来先生吓得不轻,关中大汉与西安小老头都是性情中人,后者其父是大名鼎鼎的武昌起义的领袖人物王一山。我想,王愚父辈的事迹和故事在文学作品中已经被写过很多了,我们在《白鹿原》那样的作品中似乎也能找到王一山的身影。其子也是一个真诚率直的汉子,虽然个头不像何西来先生那样高大威猛,却也是个内心十分强大的真好汉。与何西来先生对我的教诲和帮助一样,王愚也是一直扶持我学术成长的前辈批评家。我时常想,陕西的作家为什么如此被我另眼相看,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秦人重气节,率直耿介,秦人的风骨就在于兹!
“慧善双就”,就是用自己的智慧去行善积德。何西来先生晚年受邀加入了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作为资深会员,为保护野生动物呐喊助威,曾亲临自然保护区,考察野生动物保护,撰写保护野生动物、关注生态环境的文章。我有一个亲戚L君是北京化工大学的老师,也是一个环境保护主义者,他得知我与何西来先生熟络,就让我介绍他们相识,后来我每次去北京,L君都对何西来先生的为人为文赞誉有加,他们一起为环境保护做了许多公益活动,用智慧和善良去面对世界,这也许就是何西来先生晚境的人生追求吧。
也许,我们的前辈知识分子永远活在他们过去的世界之中,他们纵有千千万万种不同的迂腐和执拗性格,也有少数的政治投机分子以出卖灵魂活着,但这毕竟是少数人,而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品格:光明正大做人,认认真真办事。这就是作为后辈知识分子的我们应该汲取的人格养分。
我没有赶去北京参加何西来的追悼会,只因这些年来经受了太多前辈的离世,总是不能忍受去火葬场的那种精神痛苦的煎熬。我以为用文字来为他们送行应该是一个好的方式,这就是我为什么只为逝者撰文的缘由。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然而积习却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凑成了这样的几句……‘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我又能写下什么来呢?
“何老别”,我们总是向你挥手告别,但是我们却永远告别不了你!
2018年7月2日
匆匆于南京仙林依云溪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