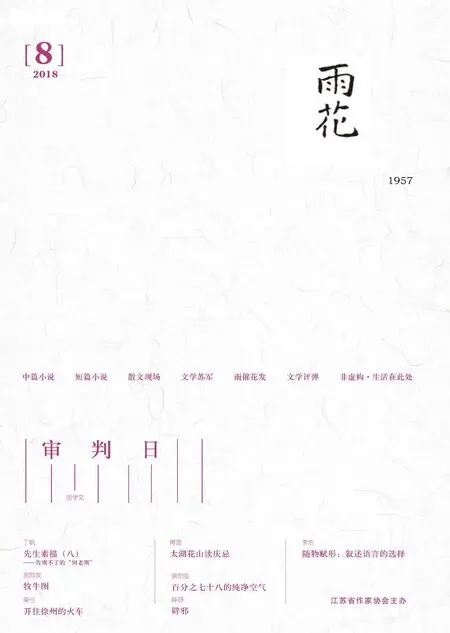克利:宇宙与抒情的幻想(外一篇)
一
每次面对克利的画,我心里总是忍不住产生他是一个孩子的错觉。但没有人会永远是一个孩子,尤其是时代在其身上打下一个个烙印之际。从时间角度来说,也不可能出现永远停留在儿童期的个人。时间的功能之一,就是改变人的年龄、相貌、体格以及各种各样的欲望。人在时间中长大,从童年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和晚年。没有谁能从时间中逃出。有时候我们又总会感觉,某个人虽然到了一定的年龄,其想法和内心,始终没有和年龄形成对称——他长大的是身体,内心却没有跟上来。
觉得克利始终是个孩子,就在于他的作品不给人成熟之感。
但什么又是成熟?
很大程度上,成熟不过是一种社会衡量,不是人的内心衡量。社会衡量一个人的外在,内心衡量一个人的思想。外在与思想,总不可避免地有这样那样的冲突。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写过这么一段话:“诗意地理解生活,理解我们周围的一切,是我们从童年时代得到的最可贵的礼物。要是一个人在成年之后的漫长的冷静的岁月中,没有丢失这件礼物,那么他就是个诗人或者是个作家。”
这段话隐含另外一个意思,那就是当一个人不再诗意地理解生活,就说明他已服从社会的种种规则,成为了一个可以用社会尺度来衡量的成熟之人。
克利不是诗人和作家。从本质上看,画家和诗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前者以画笔描绘世界,后者以文字解读世界。只要对象的客体不变,他们就可以在表达的领域里统称为艺术家。克利描绘的世界始终像诗歌一样迷人,这保证了克利在今天拥有一个无可争议的大师地位。
得到一个地位,取决于得到地位的人究竟有什么思想。
人长大就会知道,我们置身其间的世界异常复杂。复杂来自人为,也来自人与生活的纠缠。一个人的成长过程,就是不断地和自己进行抗争的过程,其结果将决定行为人将成为一个社会人还是一个诗人。
二
决意当个画家时,克利刚刚十八岁。这个年龄也恰好是社会规定的成人之龄。克利在这个年龄上的选择令人惊异,好像这个年龄注定要成为他生命的播种之年。人在这个年龄长大,世界在这个年龄打开。年轻的克利和所有人一样,内心充满新奇和求知欲带来的种种冲动。似乎从那时开始,克利就不再有什么改变。他选择了绘画,就把一生都献给了绘画;他发现天真对艺术的重要,就维持并最终实现他毕生追求的梦想——老到天真。
少年时拥有天真,可以说是一个人的天性。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天真对一生和艺术的重要性,几乎可以说克利有超越同龄人的老成。但生活中的克利从不老成。或许,在克利的天才质素中,发现天真的重要是体现其天才的最直接证明。
要当一个艺术家,仅有天真显然不够。确定自己的艺术选择之后,出生瑞士的克利在巴黎和德国之间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选择了德国。不过,三年的慕尼黑学习生涯给克利带来的失望多于收获,于是意大利成为他艺术事业的下一站。在对那不勒斯、罗马、佛罗伦萨以及对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等名画的欣赏中,克利逐渐形成他的美学观念,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艺术使他明白真诚与谨慎的必要性。
1903年,克利完成他最初为世人所知的版画作品,如《树上的少女》和《两位相互比谦恭的绅士》等。尤其那幅《两位相互比谦恭的绅士》,为克利日后的创作奠定了方向。画面是两个面对面弯腰行礼的裸体。画家笔法质朴,两人的身体都弯曲得像两头山羊。在克利简洁的勾勒之下,画中人呈现出一股特别稚嫩的神态,尽管两人年龄不小,尤其是画面右边的那个人,胡须浓密,他们的眼神却都流露出一股儿童似的纯朴,因而画面在幽默和荒诞中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天真之感。
在克利毕生的创作中,除了这么寥寥几幅作品,我们能够看出完整的人形,随后的创作就很难再看到如此近乎怪诞的人物画了,也可以说,在克利早期,他和所有投身绘画的人一样,没有彻底摆脱视觉所要求的完整。从那之后,克利的追求无论怎样变化,都再也没有离开儿童似的质朴和天真。
表现儿童似的质朴和天真,当然不一定就得在画面上画一个儿童。克利全力以赴所做的,是将自己的眼光培养成一种儿童的打量——面对世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眼光,儿童的眼光不过是其中一种,它保证了打量者内心的纯粹,保证了打量者不肯舍弃的单纯。一个真正儿童的单纯当然不等于一个成年人的单纯。儿童的单纯仅仅让人喜爱,成年人的单纯却有儿童不具备的深度,在成年之后,一个人依然用儿童的眼光来面对世界,至少说明这个人已超越了一些生活的限制和规则。一言以蔽之,成年守住的单纯是付出过代价的单纯。
克利付出过什么代价?
表面上看,克利没有忍受过贫穷,在情感上也一帆风顺,从其一生来看,他始终没有融合群体,甚至可以说,自献身绘画以来,克利从未操心过自我的声名是否蓬勃,也没操心过自己属于哪个流派,更没计较自己的作品能产生出什么样的经济效应。克利始终关注的是世界最本质的模样。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值得他去关心。所以他不像达利,总要喋喋不休地告诉世人自己是谁,也不像毕加索,在市场中游刃有余地获取自己认为该得到的一切。
说到底,也许仅仅除了米罗,克利与同时代的所有画家都不一样——对绘画之外的一切都无动于衷,仅仅沉浸在个人的世界,用孩子的眼光来面对世界。孩子会发现什么,他也发现什么;孩子想怎么表达,他也怎么表达。唯一不同的,克利毕竟是用艺术的手法来表达。因而在克利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大部分作品几乎都是线条与色块的渲染。在他对印象主义还陌生之时,已主动走向了色彩、光线和空间的表达之路。就空间而言,克利远远超过印象派,而且绝不同于印象派。
克利成熟期画作所呈现的,几乎都是成块成块的暖色,似乎是无数儿童没有借助尺和三角板等工具所画出的不规整的四边形、三角形等,那些不规整的造型图案却给人一种隐秘的时空之感,似乎克利要透过那些造型,看到另外一个深远的空间,哪怕在一件命名为《花朵盛开》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也是无数拼贴在一起的各色四边形,但没有哪个四边形称得上规矩,它们似乎拼贴在一起,只是想完成某种飘动。睁眼望去,也可以说是一块由无数方块色涂成的布料在不经意地打开,好像有一个多维空间出现在里面。这既是克利的拿手好戏,也是克利对空间的自我认识。通过这些色块的抖动,克利似乎将画家的眼光延伸到了无人揭开其隐秘的宇宙空间。
三
宇宙是科学的研究领域,在进入知识的研究领域之前,宇宙其实是孩子最感兴趣的地方——谁能忘记自己在童年时对星空的遥望?谁能忘记自己童年时对宇宙的惊奇?这些遥望与惊奇,恰恰构成我们对世界的最初感受。只是,当生活来临,人几乎就将这些感受遗忘甚至于嘲弄。但总有人将这些遥望与惊奇安置在内心的珍贵位置。对他们来说,这是人之所以是人的基本要素。也可以说,维持对宇宙的新鲜,也就是维持住自己内心的途径。对克利来说,内心就是一个人的最真挚之处。他的一切都从真挚出发,从最初的打量出发。在克利的画布上,无处不是对世界的惊讶和惊奇,无处不是他表达这一惊讶惊奇的儿童般的几何造型,无处不是这造型所体现出来的温暖和明净。
克利令世人着迷之处,就在于克利的世界充满没被玷污过的成人单纯。
只是世界复杂,维持内心的人总是会碰到种种阻碍。
克利创作最成熟的年代,正是纳粹上台的年代。克利被迫中止了任教工作,大量作品被封存,名字也被印在慕尼黑“堕落艺术”展览的画册目录上。但即便置身暴力,克利也始终没改变自己的创作风格。从这点来看,克利的单纯几乎称得上强硬。最令人震惊的是,在画家去世前一年,也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39年,年已六十的克利不可思议地画下数量惊人的一千二百余幅画作。其中那幅《探手的天使》尤其令人难忘。画面虽不再是他习惯的色块造型,手法却一如既往,如同一个孩子的随性涂鸦,在不成比例、也不对称的画面上,一个大眼金发的女孩伸开双手,微笑着,似乎在和世界打招呼。在橙色上涂有黑色斑迹的背景中,小女孩仿佛就是一首童年的诗歌,在属于自己的空间里驰骋想象。画面的抒情感很少会使人想到画下这幅画的画家其实是在沧桑中走过一生。
最易改变人的便是沧桑,但总有连沧桑也无法改变的人存在。这类人的心灵感受总是令人惊异。除了绘画,克利也在文字中表达过自己,“我无法了解世俗的事情,或许我跟死亡与尚未诞生的人在一起比较快乐,也可能是我比一般人更接近创造的心灵。”这句话的令人震动之处,是克利以自己的一生,告诉世人什么才是属于他的创造。他画布上的抒情也好,展现的宇宙奇观也好,都是他用毕生的寻找来获取——没有谁的人生不是寻找。唯独克利的寻找始终从他的童稚出发,进而形成其延续一生的幻想王国。幻想对任何人而言都弥足珍贵,尤其在一个艺术家那里。借助幻想,克利造就出非同一般的艺术。在今天来看,克利的艺术似乎仍然在告诉我们,保留一颗童心,会接近最本真的艺术,但用童心来深涉人生会不会太冒风险?那就看走上艺术之路的人是不是把艺术本身看成自己的最高荣誉了。
劳特累克:在角落征服巴黎和时代
一
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法国巴士底狱被摧毁一百周年之际的1889年,有两件事引起巴黎人注目。一件是成为巴黎象征的埃菲尔铁塔竣工,另一件是一家命名为“红磨坊”的夜总会开店。前者在今天,无时无刻不出现在关于法国文化的构成深处,后者则在当时造就了蒙马特尔区的辉煌。从晚上十点到午夜,成群结队的巴黎人涌向红磨坊。该处提供的大胆表演节目,征服了整座巴黎。
19世纪的法国,尤其是有拿破仑这样白手起家的榜样,使得所有稍具各种才能的青年都渴望对巴黎进行征服,这点只消读读巴尔扎克的小说就可以知道个大概。只是巴尔扎克没有活到红磨坊时代,否则必将用新的巨著来填充他未完成的《人间喜剧》。虽没有文坛巨擘生花之笔的描写,但也有其他艺术家在全神贯注地打量,以期留下一个时代的风貌。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只要想起和说起红磨坊,就一定会想起和谈起劳特累克。
从劳特累克的传记来看,除母语法文之外,他九岁就懂得希腊文、拉丁文和英文等多种语言,家庭的艺术熏陶也使他自幼开始习画,十一岁就具有相当纯熟的速写能力。不论放在何时,未来的画家都堪称出类拔萃的法国神童。
二
到红磨坊开业的1889年,劳特累克正值25岁的青春之年。作为具有贵族血统的后裔,劳特累克似乎很早就辨识出19世纪天翻地覆的改变。在其早期画作中,除了对家庭的描绘,劳特累克从未像萨金特那样专心致志于上流社会富丽堂皇的场景。或许,那个在历史中退潮的阶层不具有劳特累克所以为的时代性和代表性。在劳特累克眼里,被社会激发到突出位置的平民更有值得描述的价值。画于1885至1886年的《洗衣妇》是劳特累克最初吸引我的画作,也是画家早年的一幅代表作。
画面上一个侧身而立的金发女人,头发略微凌乱,遮住了额头和眼睛。女人穿一件普普通通的白衬衫,衣袖挽起,手掌按住桌沿,桌上有件未洗的衣服。就人物神态来看,似乎有点疲惫,于是在劳作间隙里站起,无目的地望向窗外。这幅画吸引我,是因为它让我很自然地想起左拉在《小酒店》里塑造的洗衣妇绮尔维丝。该部名著的起笔就是女主角在窗口站立。当我看到劳特累克这幅画时,感觉画家画下的就是左拉的小说开头。在发誓要留下第二帝国每个阶层的自然主义作家那里,选择一个洗衣妇为主角,本身就意味着平民阶级在社会中的登场,并逐渐成为时代突出的生活现象。劳特累克选择这一角色,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底层人物已成为无法绕开的重要社会构成,另一方面,它也说明劳特累克的目光和感受都深入社会的种种变更当中,即便画家的朋友都是富家子弟,但唤起他创作欲望和热情的,还是更广阔同时更有代表性的身边事物。
从这里来看,其实就决定了劳特累克和同时代画家的不同。譬如在柯尔蒙画室当学生之际,成为劳特累克朋友的梵·高便以激烈的内心渴望来表达个人的极致情绪。劳特累克截然相反,哪怕在绘画技巧上下过非凡苦功,画风上也吸收了不少印象派特点,但画家最终选择的还是通过画面去表达什么,而不是将作品如何进行表达。对创作来说,表达什么和如何表达,从来就是纠缠不清的问题。只有不去纠缠的人,才能从容不迫地开辟自己的道路。
不知道劳特累克选择直观表达是不是因为少年时两次骨折引起的残疾所致。或许因为腿瘸,劳特累克才更信任自己的眼睛和手?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们看见的事实是,作为画家的劳特累克,选择的是在画布上表现他亲眼目睹的画面。另外可以肯定的是,因为不愿旁人将自己当残疾人或侏儒看待,画家对仪表颇为注重,总是夹一根樱桃木制手杖,身穿黑白方格裤子,礼帽总在头上,冬天多半是蓝色外套,偶尔也系根绿色领带。仅看外表,与其说劳特累克的身份是画家,不如说是地道的绅士。
这个绅士每晚的出入之所便是红磨坊。
三
在当时热衷红磨坊的,多半是寻欢作乐之人。既有来此观光的国外游客,也有不少王公贵族里的遗老遗少,它同时还是无数初出茅庐的作家、音乐家及诗人们的聚会之所。在那里,音乐厅主持人定期主办艺术化妆舞会,节目中少不了裸体模特的大胆登场和一些奇装异服的艺人们为观众提供别出心裁的各种表演。
在1885年便依靠为杂志提供插图作品而已然成名的劳特累克,像其他人一样喜爱上红磨坊。但他出入红磨坊并非寻求刺激。对年轻的画家来说,红磨坊已在事实上代表了巴黎。代表巴黎便代表了法国,代表法国则无疑代表了当时的整个欧洲。在劳特累克那里,作品的目标从来都是现实生活和寻常大众,因此画家像小说家一样,悉心捕捉人物形象,着力刻画他们的性格和悲喜,刻画生活带给他们的种种,刻画在人与人之间不断游走的时代身影。对劳特累克而言,绘画不仅是艺术的目标,还是生活的手段。在这方面,劳特累克的确和同时代的作家左拉类似——后者为写教皇到罗马,为写金融界跑交易所,为写工人亲往矿区。劳特累克为画出一个时代的缩影,选择了当时极具代表性的红磨坊。
在具有代表性的寻欢之地,女人当然不少。红磨坊的女人身份各异,她们有的是画家们的模特,有的是音乐厅的舞女,有的是非专职的裁缝,有的是各阶层名人的情妇。劳特累克的画笔也很自然地指向了这些被命运抛来抛去的女人。在那一时期,劳特累克画遍了蒙马特尔的所有舞女。它们一幅幅构成画家举世闻名的“红磨坊系列”画作,也铸就了劳特累克绘画生涯的鼎盛期。
在劳特累克的画中,不少女人通过其画作成名。其中一个叫珍妮·雅芙丽的女人出现较多。按照劳特累克所画对象必须是引起其兴趣和受其仰慕的原则来看,画家从珍妮·雅芙丽身上当然会发现不少值得关注的东西。在一系列含有珍妮·雅芙丽名字的作品中,有两幅形成对称的画作格外引人注目。一幅是《走进红磨坊的珍妮·雅芙丽》,一幅是《走出红磨坊的珍妮·雅芙丽》。两幅画都完成于1892年。在《走进》中,雅芙丽身裹一件蓝色外套,戴蓝色手套和绿色顶花扁平帽,画面背景模糊。在《走出》中,雅芙丽则身着黑色外套,穿黑色尖皮鞋,头上的顶花扁平帽也变成了黑色,双手插在衣兜,背景全部为橙色,有以一中年男人为主体的数人和她反向而行。
据称,劳特累克首次看见她时,珍妮·雅芙丽还是红磨坊的小舞女,眼睛迷人,脸色苍白,被形容为“虚无缥缈的女孩”。劳特累克和艺术界的朋友们经常为其捧场喝彩。在1890年后,画家和她发展成亲密的关系,后者对画家的作品也极感兴趣,经常为他摆姿势,走进他的各类画作。雅芙丽对劳特累克的回报是自称情人不少,却只有一位专属画家。
有点奇怪的是,在劳特累克这两幅画中,读者既看不出她的虚无缥缈,也看不出她的保守和温柔。两幅画中的雅芙丽表情类似。在《走进》中,脸型瘦削,下巴很尖的雅芙丽眼睛低垂,好像被某种很深的无奈所控制。给读者的感觉是,她一走进红磨坊,就顿时感到自己将被某种东西所压抑,原本的内心平和在忽然间消失。在《走出》中,雅芙丽仍是眼睛低垂,仿佛陷在某种沉思当中。她的沉思不是因为偶然遇上某个问题,而是因为刚刚出来,感到一股难以忍受的疲惫。简言之,走进红磨坊的雅芙丽感到压抑,走出红磨坊的雅芙丽又流露出虚脱样的疲乏。但无论压抑,还是疲乏,雅芙丽都像所有女人一样,决定把生活继续下去,也忍受下去。
四
对一个能征服巴黎的场所而言,红磨坊似乎就是最美好的所在;对流连红磨坊的红男绿女而言,那也是一个理所当然的欢娱之所。偏偏在此,一个被画家爱恋、被诗人献诗、被不断有专人撰文捧场的当红女伶,毫无周遭人所具有的兴奋,就好像她厌倦那个巴黎人纵情声色的场所。事实上可以想象,在走进和走出之间,雅芙丽一定在红磨坊受到了众星捧月般地追逐。不仅对女人,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被众星捧月,都会感到在充分的享受中实现了自我。
劳特累克虽然没有避开雅芙丽在红磨坊受追捧的画面表现,但画笔能够落在雅芙丽刚刚走进的时刻和曲终人散后的走出时分,就表明劳特累克的目光不仅仅只锁定在红磨坊之内。红磨坊的象征喻意会令一个将时光消磨其中的人有更多感受。这些感受不会在红磨坊的热闹中出现。熟悉红磨坊的人一定是身在红磨坊的人,身在红磨坊的人也一定会比其他人更加懂得红磨坊带给人的是何种现实。
未尝不能说,这种现实也就是时代带给普通人的现实。
劳特累克通过这两幅画,十分细致地将当时人的内心世界打开。所有人的内心世界都不可能不和他的生活挂钩,他的生活又不可能不和他的时代挂钩。在一个能代表时代生活的场所里,该场所的代表人物也应能反映一个时代的样子。在喧腾与繁华之下,人究竟能从时代中得到什么?这不仅是劳特累克,也是那一代艺术家不断追问的问题。很少有人能及时得到答案,劳特累克也未必能告诉我们,当他呈现出当时的人物内心,至少说明了劳特累克对时代的敏感一面。把喧腾与繁华揭开,我们看到的仍然是人无法掩饰的失落。与其同时代的版画家杜米埃,习惯用夸张的手法来针砭时弊和讽刺社会,乃至抨击伦理道德,劳特累克只简单地呈现生活本身,反而在今天具有更强的时代表现力和艺术感染力。如果我们认真打量画家全部的“红磨坊系列”,会发现那些画中人很少有笑容流露。或许,在一个物质时代即将掀开大幕之时,所有的人性都在发生激烈地碰撞?这些碰撞更让我们从那些细微处看到更强烈的社会风貌。
在劳特累克笔下,充满种种细微感的“红磨坊系列”将其带到个人的艺术顶峰,这个顶峰却来源于一个小小夜总会,让我们在惊讶劳特累克非凡表现力的同时,还真可以发现,一个人要征服他的时代,不一定就非得对时代的所有覆盖面进行亲身体验和条缕分明的辨析。生活在哪里都一样,就看是否有一种能够深入生活的眼光。面对劳特累克的不朽之作,值得我们深思的不仅是他的技巧,还能在技巧之下,看到他给予的提醒——我们该以什么样的眼光来面对和认识今天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