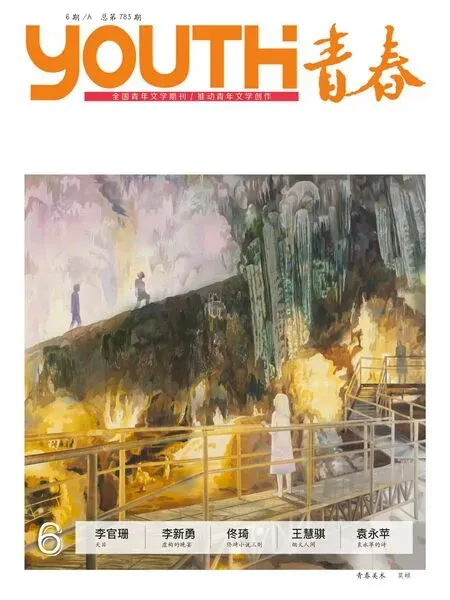佟琦小说三则
口 佟琦
小儿女
我其实是很喜欢苗蕾的。实际上,我刚一上初中就喜欢上了她。她确实是我喜欢的类型:猫脸、短发、身材匀称,活泼开朗又喜欢运动。她当时还是我们班女生的体育委员,每次上体育课作热身时我都能看到她领着一队女生一颠一颠地跑在最前面,那小短发在她头上时而蓬起,时而落下,她的小脸因为跑动变得红扑扑的,红得像个苹果。
后来我才发现,每个男人喜欢的女人都有固定的类型,不过这已经是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事了。而我无疑就是喜欢苗蕾这种类型的。
总之吧,我很喜欢她。
但是,也只是喜欢而已。我从没有更进一步的行动,顶多是课间时多跟她说几句话,偶尔有些小小的语言挑逗,偶尔有些小幻想,而已。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只是个小男生,可能连少先队还没退呢,脑子里大部分时间还在想着“学习为重”之类的东西。我既没觉得有行动的必要,也没感到有行动的冲动。只是单纯的喜欢吧。
我觉得我属于发育比较晚的那种,相比较我来说我班同学有的就已经相当成熟了。
初二那年从上一年级蹲下来一个同学,名叫刘玥,就是典型的流氓。此人身体健壮,体毛俱全,时而在盯着一个小妞看时会流露出一副色眯眯的表情。后来我跟他混得挺熟,他就多次怂恿我:
“你为什么还不行动呢!”
我说,我没觉得有什么必要啊。
“上啊!”
这他妈流氓。
那时我们年级在教学楼三楼,每到课间我们都会来到楼道外的消防梯,趴在栏杆上透口气,顺便向下看看。那天我和刘玥照例呆在那里。我们随便说着话,眼前是几棵大树和空旷的校园。这时,我看到二楼和我们同样的位置,我们学校的一个痞子正把一个小妞抱在怀里!两人冲着同一个方向,一齐靠在栏杆上。我的心脏顿时没出息地狂跳起来,赶紧缩回了脑袋,但又抑制不住地再次探出来看。那个小妞我认识,是我们隔壁班的,叫孙冉。而那个痞子是我们上一年级的,估计刘玥认识。我扭头看看刘玥,只见他也在往下看,笑眯眯的,小眯缝眼里直放光。
刘玥叫了那个痞子一声,那人和孙冉同时仰起头来。那个痞子坏笑着,再次把头仰了一下用下巴颏跟刘玥打了个招呼,而孙冉只露出一点点的羞怯,她冲我笑了笑就把头低回去了。
两人依旧抱着,靠在栏杆上。
事后刘玥告诉我,他说他怎么觉得孙冉的胸最近明显大了呢,屁股也翘了,走路还一扭一扭的,原来都是被那孙子摸的。
我不记得当时听刘玥这么说时自己是不是听傻了。不过孙冉的胸确实是大了一圈,因为,这是非常明显的。
孙冉有一个同班同学名叫王圆,那时王圆狂追我。而且这事她也不避人,弄得许多人都知道。她让别的女生给我带信(包括孙冉),上我们班门口找我,还经常给我们家打电话,诸如此类。
有一天我刚回家电话就响了,是一个陌生的女声。
她先问了我的名字,然后又躲躲闪闪地不告诉我她的名字,说到最后我也不知道这人是谁。
“你知不知道王圆特别喜欢你?”说完那边就一片笑声,看来还不止一个女生。
“知道啊,”我说。
“那你喜欢她吗?”又是一片笑声,其中还夹杂着“哎哟!哎哟!”之类喊疼的声音,看来是有人不好意思了。
说实话,我根本就不喜欢王圆。因为王圆太胖了,圆圆的,充其量也就是个可爱型,而非我喜欢的短发运动型。就像苗蕾那样的。
因此,我对王圆的反应冷淡。加之我又属于在开窍没开窍之间,结果可想而知。
后来有一次我好像说了什么重话伤了王圆,她还哭了。结果第二天上学,我刚走出车棚,一个高年级的痞子就把我叫住了。
“你,过来!”那痞子用手一指,我随即就像一块被他吸住的铁块一样来到他的跟前。
他的旁边站着王圆,一副又生气又悲伤的样子。
“有什么事吗……”我嗫嚅着说,心里当然明镜似的了。
“你欺负她?”他用大拇指向旁边指了指王圆。
“没有啊……”
我看了看这个痞子,此人瘦高、细目,面色铁青,不是上初三就是上了高中,一副很能打的样子,以前在实验楼的厕所里我还见过他和别人抽烟。
“看什么看!滚蛋!”
他上次就是这么和我打招呼的,可谓和蔼可亲。
这一回,这痞子告诉我,王圆是他表妹,我要再敢欺负她就小心点儿。
“听见没有!”他最后吼了一句。
王圆在一边小声地劝,“哥,行了,没事了……”她脸上一副挂着泪痕的样子,就像我们是两口子,就像她是那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
“听见了……”我说。
遇到这种事我一般都是唯唯诺诺,巴不得事情赶紧过去,于是事情就过去了。
事后王圆觉得不合适,还找我道歉,不过似乎也没什么必要。我对她没有变得更好,也没变得更坏。
我想对于我和王圆的事苗蕾应该是知道的,她好像还微微表现出一点儿不高兴。不过,当然了,我依然只是对她情有独钟。
有时我和苗蕾在一起走,她会因我的某些话而低下头抿着嘴笑,脸上既有害羞又有高兴。这让我兴奋。不过那时她总是和一个戴着眼镜的胖乎乎的女生走在一起,还经常手挽着手,结果她作这番表情时都是我和那个胖乎乎的女生把她夹在中间,样子有些怪异。
那一年的圣诞节快到了。
我通过刘玥打听到苗蕾希望我送给她一种蓝色式样的贺年卡,还有一个小熊样子的钥匙链。苗蕾并且说道,那两样东西在她家门口的一个小商店里都有。
于是那天一早我就骑车到那家小商店,天气极冷,老板刚开门,我顺利地买到了那两样东西。回到家写废了好几张纸才写出几笔好看的字填到贺年卡上。
我想写的无非是些“圣诞快乐,预祝新年也快乐”之类的话。
据说效果很好,苗蕾很喜欢,似乎也感动了。她感动于我大冷天的,冒着寒风,骑车去给她买礼物。她再见到我时脸上洋溢着一种幸福,好像不自觉地就红了。
但是,接下来我该干什么呢?我还真不知道。我只是满足于她高兴就好。而至于她高兴了我应该趁热打铁再干点什么……难道必须这样做吗?
“上啊!”刘玥说。
“我要是你,”他又说,“这事早成了!”
刘玥确实经验丰富,我记得有几个周末他还跟我借过山地车,他说我那辆车好看,把小妞带在大梁上可以随时亲一下。我不知道那小妞是谁,可能是他原来那个年级的吧。
在刘玥多次的鼓动下,我最终还是决定有进一步的行动。
那一年的元旦,我们年级组织去科技馆参观。由学生自行前往。我忘了我是通过刘玥还是通过经常和苗蕾在一起的那个胖乎乎的女生,反正最后我是约了和苗蕾一起去。她告诉我她认识科技馆,到时我到她家小区门口等她即可。
那天早晨,我换好衣服,然后直接骑车到了苗蕾家所在的友谊宾馆附近。
我坐在车上,单腿着地等在路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街上开始出现上班的人潮。那时绝大多数人还在骑自行车,我听到车铃声阵阵,响在我的四面八方。间或会有一两个穿我们学校校服的学生从我身边骑过去,有男有女,也有成对儿出现的。我看看时间,已经不早了;我沿着马路前后地兜了一圈,我还骑上了马路牙子在那一长排的店铺前找了一遍,都没有苗蕾的影子。我想想没错啊,怎么没人呢?我想苗蕾此刻也一定在某个地方等我,她肯定急得望眼欲穿——一想到这个可真让我受不了。于是我又来回来去地兜了好几圈,但依然没有。我放弃了,最后直接把车骑进了人民大学,骑到了刘玥家楼下。此时人大的家属区大人都去上班孩子都去上学,因此十分安静。
“刘玥!刘玥!”我冲着楼上高喊,希望他还没走然后我跟他一起去科技馆。
但一点动静也没有。连不怎么上班的刘玥他妈妈也没把头从窗户里伸出来。
我骑上车,原地绕了一圈,然后就回家了。
就是这样,那天所有人都在参观科技馆的时候,我终因泡小妞未遂一个人留在了家里。
事后我得知,苗蕾在另外一个地方也等了我半天,最后不得不一个人去了科技馆。
我脑中不断回放着那天早晨的情景:苗蕾站在自己的自行车旁边,向着马路的一头望着,她希望我能脱颖而出,她的眼睛在不断地搜寻,嘴巴因焦急而微微地张开……
四周车铃乱响。
初二那年很快就过去了。
暑假的时候刘玥他妈妈给刘玥报了个提高班,刘玥问我想不想也去,我说可以,于是我们就在那个假期里一起上了半个多月的课。
说是“提高班”,其实就是把下学期的课提前讲一遍。那里大部分同学我都认识,其中好多都是我们学校的。
我发现,居然王圆也在。
刘玥告诉我,王圆是听说我去她才决定去的,我说她也没有那么爱学习嘛。
上课时,王圆总是坐在后面,我一般看不到她。平常她也不会过来找我,只是见面时打个招呼而已。
暑假闷热难当,课程上到后半段我们难免都有些松懈,这期间我和刘玥逃过半天的课,专门跑到海淀剧院门口的游戏厅打游戏。平常我都是跟我的邻居李博去,没少在这种地方挨劫。那天和我们同去的一个哥们儿刚到那儿不到半个钟头就被几个痞子暴揍了一顿,据说是他跟别人“照眼儿”来着,在回答对方“你丫跟谁照眼儿呢!”时还表现出不服,于是就被暴揍了一顿。我还和刘玥一起跑到北大的游泳馆游泳。刚换好泳裤要下水,就看到王圆正规规矩矩地坐在岸边的椅子上,也换了一身泳衣。
“又是你跟她说的吧?”我问刘玥。
“我也是没办法啊!”他说。
当时的王圆依然处于对我的穷追猛打之中,我经常就会在某地与其不期而遇。当然,这都有赖于刘玥的帮忙。
见到我王圆也不说话,只是安静地坐着,我也没理她。
老实说,王圆是怎么想的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整天想着学习上的事和怎样练一手好字,而王圆呢,却把这些时间全花在给我叠千纸鹤上了。她曾经送给我一大罐子他用各种彩纸折的千纸鹤,有999只吧?就像原始妇女在旷野里挑选浆果一样耐心,也不知道她家里人看到这一幕会怎么想,而我收到这些千纸鹤也没太往心里去。我就像那些原始的男人一样,脑子里始终在想着打猎或怎样攻击一头猛犸象。
新学期开始了。
我对王圆依然是爱答不理。
一天下课,我听到楼道里一阵嘈杂,夹杂着有人喊叫的声音。我跑出去看,只见王圆带着孙冉和另外两个女生把苗蕾围在了女厕所门口。然后又是一阵乱,好像动手了。
我赶紧跑过去,那里已经围了许多人。
王圆怒目圆睁,怒视着苗蕾,她旁边孙冉那几个也都是一副气呼呼的样子。
“你他妈是不是有病啊!”王圆骂道,“要成就成,老抻人家干吗!”
苗蕾完全被这阵势吓傻了。
“我没有……”她嗫嚅着说,声音小得我几乎听不见。
她的话还没说完,王圆抬手就扇了过去。一切都是那么猝不及防,我看到苗蕾的小脸一瞬间变得通红,两行眼泪瞬间流了下来。她调转身子想跑,但别人死死地围着她。有人把她推来搡去,有人又伸手过去扇她。
“我让你丫犯贱!”我听到王圆一边打一边喊。
我简直都认不出王圆来了。那个一直很沉默的、脸上挂着悲伤表情的、规规矩矩坐在游泳池边上的王圆,今天这是她么。
“我操!别这样啊!”只见刘玥从人群中冲了出来,他过去护住了苗蕾,隔开了众人。
“圆姐圆姐,”刘玥继续说,“有话好好说,干嘛这样啊!”
王圆停下手,胸脯剧烈地上下起伏,我觉得她真是压抑太长时间,今天终于爆发了。
我也回过了神儿,走到近前。
我只是一脸怨气地看着王圆,不知道该说点儿什么。看我过来,王圆死死地盯着我,表情就像个陌生人。
“王圆……”
“去你妈的!”
我刚要开口,就被她打断了。
王圆转身,分开众人,跑了出去。
就因为这件事,王圆以及孙冉等几个女生,被学校不同程度地给了处分。
从那儿以后,王圆就再不理我了,看到我如同看到了空气。后来初中毕业,我就再没了她的消息。
苗蕾则一直在躲我,看到我,脸上的表情有些异样,然后就会赶快扭过头去。她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初三的时候,我和苗蕾依然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我仍然处于那个老状态——在开窍和半开窍之间。老实说我对我自己也很失望,但是没办法,我就是这德行。
我们只是圣诞时互送贺卡、生日时互送礼物,偶尔地我会“挑逗”一下,每每这时苗蕾仍然会把头低下去害羞地抿嘴笑起来,仅此而已。
初三下半学期为了应付体育考试每天下午放学全年级要去操场跑圈。那天跑完圈,我和苗蕾在上楼时碰见了。
“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吧。”我说。
“……好吧。”她犹豫了一下,说。
不过那天最终有什么事耽搁了,我还是没有送她回家。
中考时苗蕾正好坐在我旁边,我们之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中考结束之后我们就各自上了不同的高中,也就分开了。
倒是高中时有一天我骑车路过人大门口时碰见了苗蕾。她当时也骑着一辆车,与我相向而行。
“苗蕾!”我叫了她一声,她一开始没看见我,这时已错开好远。
我没停车,一直向前骑了,扭头看时,见苗蕾已经下了车,身子正处于落地时的晃动中。
在这之后我们就一连十几年没见过对方。
前两年初中同学聚会我又看到了苗蕾,她已经结婚了,那天是她先生开车送她来的。
她穿着入时,甚至有点暴露,我都快认不出来了。
游戏厅
我小时候的海淀还是有许多痞子的。大部分是我们那片中学的学生,也有些小学生,作为喽啰。也有少数退了学在社会里混的,那是更高级的痞子了。只是对我来说,我从没有接触过这些高级的痞子,我觉得他们可怕得要命,总是躲得远远的。所以对当时的我来说,“社会”这个词也是十分可怕的。我从小胆子就不大。
我总是招各种痞子。我想这是因为我面善,看着好下手。有一次,我都上中学了,一天骑车回家,突然感到车后轮被蹭了一下。我扭头一看,一个大孩子心怀鬼胎地骑了上来。一看他那揍性我就知道这是个痞子,段位在中等偏下,给某些大痞子提鞋的料。我心下一慌,随即又镇定住了。你怎么骑车的,他倒先质问我。我十分本能地来了一句,对不起啊。我看到他也愣了一下,没想到我认错态度这么好。同时我也有意无意地装出一副不想惹事的可怜相——相信我,如果有足够时间的话,我还真能挤出两滴眼泪来。他从上到下打量了我一番,随即露出真面目,有钱么?他突然问我。没钱,我答。我真没钱,在痞子面前我总是非常诚实,我想要不是我现在骑着车,我非得把全身上下所有的兜都掏出来给他瞧个究竟不可。我多诚恳啊!他又瞥了我一眼,目光停在了我车后架上夹的外套上。他伸手过来摸。显然那里没有钱包之类鼓囊囊的东西。我们一起向前骑了一段,我觉得时间长极了。他收回了手,道,下回注意!他倒有脸教育我,不过我倒觉得他更像是给自己找了个台阶。我说,好。他用力一蹬,骑到我前面去了。我长出一口气,但同时又觉得有必要向他表示一下客气,慢…慢走。他扭回头来瞪了我一眼,去你妈的!我的脸上七扭八歪。他一左一右地晃着身体,很快骑远了。
还有一次,我和一个同学在校食堂吃饭。这时有两个高年级的坐了过来。绝对的痞子。我们那天去的食堂专供小炒,所以没什么人。那俩放着许多空桌子不坐专坐在我们旁边,一坐下来就说,你俩那边坐去。我那哥们儿勇,顶了一句,为什么?再看看我,已经端起盘子要走了。为什么?那俩其中的一个说,你过来我告诉你为什么。我忙拉我那哥们儿,走吧,我小声说。于是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到旁边坐去了。
又有一次,中午的时候我骑车在学校里转悠。远远我就看见一个痞子在花园的小路边上吃烤白薯。我心里顿时一紧,但是无法,我已不可救药地向他驶去。如果我这时掉头就跑未免太夸张了,于是只得向他驶去。从我出现的一刻那孙子就一直盯着我,目光凶狠似狼。我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我已作好了最坏的准备,他会把我一脚从车上踹下去。就在我们交汇的一刹那,他抬起手给了我后背一掌,那“啪”的一响震动着我的后背和鼓膜,至今犹在。我当时的感觉是,丫肯定把那吃剩的烤白薯全贴我后背上了,让我像踩了狗屎一样。我落荒而逃,几乎撅起屁股骑起来。别再让我看见你!他冲我逃跑的背影喊了一句。等到了安全地带,我脱下外套查看,上面什么也没有,他还算对得起我。
就是这样,我和诸多痞子的遭遇都如出一辙。我从没有试图做出一些英勇的行为,哪怕连想都没有想过。我悲哀地发现,即使我读到再多的英雄故事,即使别人告诉我勇敢是一种多么可贵的品质,结局恐怕还是一样。
就我经验来说,海淀这一带的痞子还算客气,他劫你的钱,你掏兜说没有,他顶多骂你两句就让你滚蛋。西苑的痞子就不一样了。他劫你的钱,你照例掏兜说没有,然后他骂你两句让你滚蛋,在你转身要走掉的时候,他会朝你的后背扔过去一板砖,以示失望和愤怒。如果没有板砖还可以补上一脚,让你来个狗啃泥。我的邻居李博就挨过这么一下子,从那儿以后他就再不到西苑那边玩了。
当时正是游戏厅最火的时候,几乎每一片都有两三家。店面都不大,里面十几台机子,每一台不是充斥着和流氓搏斗的惨叫声就是机关枪的突突声,偶尔也会有威力很大的爆炸声。币不算太贵,一块钱两个或三个。在里面玩的,绝大多数都是中小学生,同样,那也是痞子最扎堆的地方。
我的邻居李博比我高一个年级,他最爱去游戏厅玩“街头霸王”。他把一个接一个的“波”发向对手,那个“波”飘飘悠悠地飘过去,对手如果敢跳过来他就会迅速晃动操纵杆,里面的角色就会挥舞着拳头向天上冲去,将对方击个人仰马翻。李博很喜欢去游戏厅发“波”,显然这会有被劫的危险,于是他就拉着我一块去,于是这种危险就成倍地增加了。
我其实对游戏厅一般,绝大多数都是李博拉着我我才去的。去的时候他也会给我买两个币,省得我无聊,于是我也发几个“波”,搓两个大招,不过成功率极低,那台机子被我搓得直晃悠,手柄撞得当当响,而里面的人则只是胡乱地挥拳,没有一次他能像李博手下的人一样攥着拳头飞上天,因此一会功夫我就被暴徒揍死了。偶尔我也玩个开飞机或是“三国志”什么的,结果不是被迅速击落就是被一群小卒群殴致死。于是剩下的时间我就在里面瞎转悠,或是站在李博的机子旁边看他发“波”。
那天我们刚进去一会儿就发现里面有几个痞子。他们不时地向我们这边看,偶尔嘀嘀咕咕。我心想不好,于是换了个位置,站在李博旁边只用后背对着他们。好在一直没事。李博终于玩完了最后一个币,当我们俩一起走出游戏厅的时候,这伙人跟了出来。
为首的是一个戴着黑色檐帽的孩子,那帽子当时挺流行,像是日本学生戴的,有的人还会在帽子上别个银色的小五角星,显得很痞。此时这孩子坐在一辆自行车的后座上,一只腿蜷着蹬在车上,一只腿支地。
“有钱么?”他问李博。
“没有。”李博说,“都买币了。”
那孩子轻蔑地看着李博,半张着嘴,是个龅牙。他已经很大了,应该上了中学,他身边晃悠着的那几个喽啰还是小学生的模样,其中有一个还穿着校服。我往下看了看,他穿着和我们一样的“京字”牌足球鞋,鞋底有疙瘩的那种。
“看他妈什么看!”大孩子冲我吼,像老师在训学生,我赶紧收回目光。
“你不服?”他扬扬下巴,用下巴尖点着李博。
“不服。”李博道,头也扬着。我紧张地看着他,心想这小子的倔脾气上来了。
“上!”大孩子从容说道。于是那几个喽啰一哄而上,瞬间把李博围在中间。他们有的用拳头打,有的用膝盖顶,动作估计都是跟“双截龙”里学的。李博只是躬身、护头,看不清他的表情。那个穿校服的孩子一副憨样,此刻他嘴努着,正用“铁肘”猛硌李博的后背,一下一下的,这让李博的身子躬得更深了。那个大孩子还是原来那个姿势坐在车后座上,洋洋得意。众人散开,都累得直喘,像是完成了一件什么工作,李博也终于直起了身子,他怒视着那个大孩子,泪光闪闪……他被打哭了。
回家路上我和李博都没怎么说话,李博一直气鼓鼓的,我则为自己刚才没能挺身而出而感到惭愧。到了家门口,我们只简单说了再见便分开了,之后我们就很少一起去游戏厅了,也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
过了一段时间,有几个小学同学约我,我又来到了游戏厅。我照例不怎么玩,只在里面四处转转。游戏厅里依旧一片喧嚣,乌烟瘴气,众人聚精会神地搓着大招,机器则滋哇乱叫。就在这时,我看到了那天打李博的那个小喽啰。他还穿着那身校服,脸上挂着那副憨样,我发现他居然是浓眉大眼。他像所有的人一样聚精会神,此刻正在发“波”。我担心他会认出我来,但他都没抬头看我一眼。一个大孩子过来了,站在他的机子旁边。他斜倚着身子,一边看着他玩一边吊儿郎当地和他说话。我站得稍远,听不太清,估计是问他要钱之类的。他们似乎认识。那个憨小子很紧张,只是偶尔答一两句,都不敢看那人一眼。那人说完一句话就盯着他看,“嗯?”他说,问憨小子的反应,憨小子只是发着“波”,显然已经分心了。一会儿我又看到那大孩子点了根烟,不断地往他脸上喷,憨小子微微侧过头去躲,但是眼睛却还看着屏幕。一会儿大孩子走了,憨小子却哭了。他一边发着“波”一边用一只胳膊擦着眼泪,很委屈的样子。我走近了看他,见他的睫毛很长,眼睛黑,挂着泪水。看着他现在的样子,再回想那天他给李博使出标准的“双截龙”式的铁肘,我当时就明白了一个很朴素的道理——谁他妈都不容易。
这之后我就上中学了。那是我们那片最牛掰的一个学校。初一的时候,各班轮流值周,每天早晨七点半之后派几个人在各个楼梯口执勤,以记录那些不按时到校上早读者。那个星期轮到我,于是我就在各个班传出的朗朗读书声中安静地站在一处楼梯口,随时恭候违规者的到来。那天我一共记录了两个人,第一个是四班的一个小妞,她留着小短发,按我的要求在我的记录本上签上她的名字后她还冲我嫣然一笑,这令我心旌荡漾,好一阵都没缓过来。第二个——我又听到楼梯上有脚步声传来,等上来一看,居然是那个憨小子。
他还是那副憨样,挺着胸脯,目光炯炯,一副随时都会咧嘴笑起来的样子。他显然已经不认识我了。他不知道,我已见过他两面,一次是他使出“铁肘”,一次是他被人弄哭,他还让我体会到“谁都不容易”这个朴素的道理。可是他已经不记得我了。也对。谁会记住一个小角色呢?何况,我连一个喽啰都不是,既不会被某些痞子控制指哪儿打哪儿,也不会和他们认识最后让他用烟往我脸上喷,像调戏一个小媳妇一样把我弄哭,我只会把所有的兜都掏出来让痞子检阅,好像自己的身上耷拉出舌头一样。是的,这就是我,一个小角色。
他签完名之后就回教室了,我看到他是七班的,名叫凌霄。
我们班同学有和凌霄认识的,据说他们曾在一个奥数班上课,老师都说凌霄很聪明。不过后来因为父母离婚,他被耽误了。凌霄退出了奥数班,再没有特别优异的表现。
我对凌霄大体就知道这么多,后来我们也认识了,每次见面他都会冲我一笑,小胸脯挺得鼓鼓的,像个小勇士。
那天放学,我碰到了李博。他正和我们那片的几个孩子在路边聊天。那几个孩子我都认识,不是我的邻居就是我的小学同学。那时我们那片的孩子真多啊。而李博无疑有点孩子王的意思。我下车跟他们聊了一会儿,老实说,我当时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想的,聊了点儿闲篇之后我突然对李博说,那次打你的那个孩子跟我是同学,他就在我们学校。
一听这话李博来了神,他说,是吗?我非找人打丫的!还用找别人?其中的一个孩子说,咱们几个就弄他了。
李博问了我些具体情况,我都一一说了,到此时我已后悔说出这件事,我甚至开始担心起凌霄来。但是覆水难收,我还是一一说了。
此后又过了几天,一直没动静,我以为这件事会过去,直到有一天李博找到我。明天放学,他说,我在你们学校门口等你,我带几个人,然后一起捂那孩子。
我支支吾吾地说,好……
那天上学我过得心神不宁,课间时也不想到外面活动,怕万一碰到凌霄。放学我们可就要揍丫的了!我觉得自己既对不起李博,又对不起凌霄,总之自己就像个叛徒一样。就这样一直熬到下午放学,我挪着脚步往车棚走,骑上车,来到校门口,李博他们已经在那儿等了。几个人基本我都认识,其中还有一个大孩子,是李博的表哥,据说能打。
“那孩子呢?”见我出来,李博问。
“我没看到。”我答。
“我不是让你盯着点儿吗!”
“我真没看到。”
于是我们就一起等。学生们呼呼啦啦地散着,间或李博会评论一下我们学校的小妞,我知道,他已经长了毛,发育了。
“是那天为首的那个孩子吗?”李博问。
“不是,是那天给你使铁肘的那个。”
这问题李博之前已问过我几遍,我也以同样的答案答之。“使铁肘的那个”,动作十分标准,就像“双截龙”里那哥们儿使出的一样。我像要不是身体条件的限制,当时的我们每个人都想抬起一条腿在空中转圈,使出“旋风腿”,横扫敌人。
凌霄最终还是出来了,看到他时我一愣。
“是他吧?”李博问。
“……是。”
我们把凌霄围了。
李博推了他一把,你还认识我么?
凌霄吓住了,看了看众人,又看了看我,我赶紧把眼睛垂下去。
“你跟我来一趟,”说着李博的表哥揪住凌霄的衣领就往一边的树丛里带,凌霄很老实地跟着,走的时候李博还从背后踹了他一脚,他只是身体一歪,但还继续走着,连头都没回。
那天我没有跟过去,我骑上车,一路骑回了家。我不知道后来我是如何平复心理的,反正过一段时间也就好了。
第二天,我同样在楼梯口执勤。楼梯上传来脚步声,我再次看到了凌霄。他不再目光炯炯,也不再挺着胸脯。他的眼睛红红的,显然哭过……
上到初三的那年,我听说凌霄退学了,整天跟一帮痞子在社会里混。我有一次在学校门口看到了他,见他穿着一条牛仔裤,双腿显得又细又长,他已然长成了一个大小伙子。
再后来,我听说他在一个乐队里打鼓,这之后就再没有他的任何消息了。
长河
我小时候住的地方西面有一条大河。从我记事的时候起那里每年夏天都会淹死几个人。因此我从小就被告知那里很危险。但即使这样,也阻挡不了炎炎夏日成群结队过去游泳的人们。他们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还有像我一样大的许多孩子。人们拿着卡车轮子内胎做成的游泳圈,一路欢声笑语而去,然后钻入水中,畅游起来。水面上一片嬉戏玩耍的声音。那时每到傍晚,这一幕便会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上演。
这条大河有许多名字,有的名字是从它的起点、终点各取一个字,有的是按照它的功能命名为某某引水渠,但我们当地人却一直叫它——长河。
长河淹死人是常事。多是一些半大小子。他们自以为会水,结果却酿成了悲剧。有时岸边正玩得热闹,那游到河中间的人却没了踪影。想要再见到他们只得请潜水员下去捞,或是等他们自己漂上来。后来人们分析,这些淹死的人不是游泳时抽了筋,就是被河内的水草缠住了脚。可按我那迷信的奶奶的说法,河里有水鬼,他们全是被拉下去的。任凭怎么挣扎也没用。因此,我从小便对长河充满了恐惧。
每当我游到河中间的时候便特别紧张。双手赶紧划水,同时双腿乱踹,就像真有鬼在下面拉我一样——一想到这个我就更紧张了,连扑腾带刨地游到了对岸。在外人看来,也不知道我是游泳呢还是逃命呢。但是我也像众人一样,每到夏天依然抑制不住地要来长河游上几趟。
我最早关于长河淹死人的记忆来自老何。老何,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那时她迷上了某大师的气功。她鼓动别人也练,还叫他们买书。我记得她来我家找我奶奶就不下三次,一来就坐半天,说得神乎其神,把我奶奶聊得眼睛越来越亮。
最后的结果是,我奶奶就像得了癫痫病一样每天定时定点地摆动身体。有的动作就像怀抱婴儿正在夸张地哄其入睡,有的则双手合十在胸前画圈,活像一个白痴。
“对!就是这个动作!”坐在一旁的老何说,“您必须得坚持下去,包治百病!”
那时我还很小,看到奶奶摆动着胖胖的身体,我一方面觉得十分好奇,一方面又感到一种莫名其妙的悲伤。
在老何的指导下,我奶奶还每晚八点准时面冲西南,接收那位大师发来的强大信号。只见我奶奶一边抬起双手作接收状,一边口内高喊:“收到啦!我收到啦!”
我问我奶奶收到了什么,我奶奶说她也不知道。
“人家让这么喊就这么喊呗!”我奶奶说。
我觉得我奶奶充分体现了我民族“什么都成”、“来者不拒”的特性。
练了大约几个月后我奶奶那风湿性关节炎也没好,估计臂力倒是见长了不少。后来我奶奶就不练了。老何又来过几次,又滔滔不绝地说,我奶奶只是无动于衷。
再后来我就听说老何失踪了。
人们一直在找,找了两天也没找到。最后有一天我奶奶告诉我,找到了。
“这个老何,”我奶奶说,“跳长河了。”
据说老何为了练功这事花了不少钱,许多混子都以练功为名到她家白吃白喝,最后发现那大师是个骗子,人们如鸟兽散,于是老何就彻底崩溃了。
有人回想起来,老何跳河那天行为就很反常。当时正是傍晚,天已渐渐地黑下来。那人看到老何穿着一身干净笔挺的新衣服,头发也梳得一丝不苟。她步履匆匆地向着长河的方向走去。那人跟她打招呼,她就像没听见,很快就消失了,就像个鬼影。
捞老何那天长河边聚集了许多人,只是我没有过去看。我奶奶后来告诉我,老何还穿着那身新衣服,湿漉漉的,她的头发凌乱不堪,已不成了样子……
我有一个发小名叫宝泉。
论起来他应该和老何还有些亲戚关系。
那时他、我还有李博经常一起玩。
我们在墙根捉蛐蛐、玩弹球、三角儿等,当然,我们也去长河钓鱼、游泳。
我们每人扛着一根竹子做的钓竿,额外还会带一张方形的网,像个篮子似的,下到河里。就这样我们一边钓鱼一边下网,收获总是很丰盛。
宝泉长得秀气,像个小姑娘似的。他钓鱼也很灵,每次都是他钓得最多。说实话,有时这让我嫉妒。
那天就我和宝泉两个人,我们又来到长河边钓鱼。我们分别下好竿子,很快,宝泉那边就有鱼上钩了。他一抬竿,只见银光一闪,一条小鱼就活蹦乱跳地被提了上来。他不慌不忙地把鱼从钩上摘下,放到脚边的小桶里,然后装饵,重新把钩下到水里。鱼漂平着在水面上漂了片刻,随即脚下生根,立了起来,新的一轮开始了。
那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上鱼上得很慢。我跑去起网,里面除几只田螺、几丛水草也没有什么上等的货色。我换了个地方,又把网重新扔下去。就在这时宝泉那边又上鱼了。这条鱼比哪条都大,通体泛着银光,而且身上还有一些五彩的斑点,十分好看。宝泉心满意足地把鱼摘下来,动作十分地小心翼翼。我过去趴到桶上看,见那条鱼明显比其它鱼大了一圈,而且更令我气愤的是宝泉桶里的鱼几乎个个都比我桶里的大。
我一直俯着头,羞愧使我感到脸上热热的,心脏也跳得快了起来。
我抬起头,看着宝泉,此刻他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水面上的鱼漂,是不是他想再钓上一条来然后把我彻底气死!?我想要不是今天我没打算游泳我非得现在就跳进水里来一个浪花翻滚给宝泉搅合了不可。
“宝泉。”我叫了他一声。
“嗯?”他答,眼睛依旧盯着鱼漂。
“把这条鱼送我吧。”话一出口我觉得我的声音怪怪的,因为我以前可从没说过这样的话。
宝泉一愣,看向我,随即说道:
“不成。”
说完他就扭过头去,不再搭理我。
他的拒绝也太快点儿了吧!我甚至怀疑他有没有仔细地考虑一下我的提议。
我的脸上又泛起一阵红。
“为什么?”我更加没趣地问。
“不为什么。”他答,依旧看向河面,我感到他的面目表情也变得僵硬起来。
我不再说什么,站起来,拿起我的鱼竿重新钓鱼。我分明感到我的心脏还在“嘣嘣”地跳着。
我们谁也没理谁。
之后为了缓和气氛我和宝泉扯了点别的,因为我可不想让人觉得我是个小气鬼。宝泉依旧很专注地钓鱼,对于我的闲聊他只是很简短地回答,老实说,这让我很烦。
“我去撒泡尿。”宝泉放下钓竿,转身走了。
我知道他要去哪儿,一个土坡后面,平常我们都是在那儿解决的。
宝泉走后,我放下鱼竿,终于可以不必装样子了。说实话从刚才到现在我的心思根本就没在钓鱼上。
我又来到宝泉的小桶前,蹲下去看他钓上的那些鱼。我把那条他刚刚钓上的我最喜欢的鱼用手捞了上来。我使劲地攥着,看它身上的银光闪闪,欣赏那些漂亮的五彩斑点。我越攥越紧,最后干脆掐了起来。那条鱼一开始还在我手中挣扎,渐渐地就不动了。我最后又使劲地攥了一把,就像扼住一个人的脖子,我看到鱼鳃张得大大的,这才把它放回桶里。
一放到桶里它就翻了个儿,就像一根木棍一样无知无觉。我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重新拿起鱼竿假装钓鱼。
这时宝泉回来了。
我斜眼瞅瞅他,他一回来就下了钓竿,完全没注意到小桶里的变化。
我心下还是不安,于是便假意休息一会儿,站起来溜溜达达,似无意间来到宝泉的小桶前。
“嘿,你的鱼死了!”我觉得我的演技还不是十分拙劣,就这么一句假冒透顶的话我居然还真能当真话一样的说出来。
一听这话宝泉的脸一沉,把头凑过来。他伸手把那条翻了个儿的鱼捞上来,托在手心里仔细地看着,从始至终一言不发。
“刚才还好好的呢,”我有几分胆怯地说,“可能是鱼太多憋死了。”
宝泉只低低地发出“嗯”的一声,然后又把鱼翻过来看了一遍——我感觉时间长极了——之后他才把鱼扔进了水里。
他重新开始钓鱼,不再和我说话。
实际上那天直到回家,宝泉也没再跟我说过一句话。
之后在路上碰到,他也不再理我,甚至连个招呼都不打了。
他不理我我当然也就不理他,我感到一股怨气开始在心中不断地膨胀。
有时我和李博一起上学,宝泉会主动地和李博打招呼,显出很热情的样子,而完全忽略我。作为回击,我也会如法炮制争取也把他气个半死。
有时我们仨并排一起走,李博走在中间,我会和李博兴高采烈地说笑,不好笑的地方我也笑得嘎嘎作响。偷眼瞅瞅另一旁的宝泉,他果然已气得脸上红一阵白一阵。见有空当,宝泉一下插进话来,随后也像我刚才一样兴高采烈,不好笑的地方也笑得嘎嘎的。这回就轮到我生闷气了。李博夹在中间很快发觉了不对,“你们没事吧?”有一天他问我。
“没事。”我说。
我和宝泉谁也没告诉他到底发生了什么。
夏天又到了。
人们又开始成群结队地奔向长河游泳,那里再次热闹了起来。
暑假的一天,我和李博以及我们那片的其他几个孩子过去游泳。
那天我们去了一个新地儿,那里有座铁桥,离水面的高度不高不低正好适合跳水。于是我们就玩得不亦乐乎、水花飞溅。
我们上了岸,换好衣服往回走时我看到宝泉和几个孩子也来到了这里。
他照例又和李博亲切地打了招呼,我瞥了他一眼,发现他也正在瞥我,于是我双眼一闭,同时把头扭到一边才睁开眼睛,就像用动作说出一个“切!”字,活像一个小娘儿们。
我们擦肩而过,终是谁也没理谁。
后来我就听说宝泉淹死了。
他好像在水里抽了筋,呛了水,就再也没上来。
据说和他同去的那几个孩子当时都在岸上玩,过了半天才发现异常,可是谁也没敢下去救他。
他们跑到别处呼救,那些在远处游泳的大人们也并没有过来。
事后这些大人说,以为是孩子在开玩笑。
我不记得有没有人说过,宝泉在水里挣扎的时候嘴里喊没喊过一声“救命”。
打捞宝泉的那天长河的岸边人头攒动。我也去了,站在一座石桥上远远地看着。
一个穿着一身黑皮戴着泳镜背着氧气罐的潜水员下去了半天才上来。他慢慢地从水底走出,一只手背在后面,像是拉着一件很沉的重物。
人们再次看到了宝泉。
他的身子在出水的一刻简直白得耀眼,已经完全僵硬了。双手举在胸前,两条腿也向上弯着,好像还是躺在水底的样子。
他的父母哭喊着扑了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