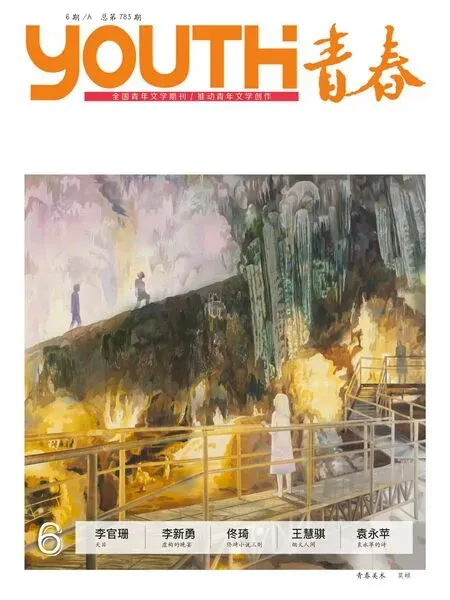胡鹏池小品五则
口 胡鹏池
做卫生的阿姨
人老了,不爱走动。宅居在城市小区,除了买菜烧饭就是趴在电脑前,对农村已经很陌生了,只剩一点割舍不下的感情。
我们家做卫生的(一周做半天)阿姨40多岁,远郊县人,人很和气。她一个月能赚四、五千,她男人在南京的建筑队当木匠,手艺很不错,工资七、八千。
这儿的农村,小麦亩产七、八百斤,棉花亩产五、六百斤(籽棉)。今年政府的收购价每斤籽棉四元二角。他们有四亩地,夏收小麦,夏收后间种西瓜与棉花。两行棉花,一行西瓜。西瓜败藤后,棉花长高了。西瓜收入一亩地五、六百元,而棉花收入比较高,一亩地三千元左右。
他们家七、八年前就盖了两层三间的楼房,每间房30多平米,每层高三尺六寸,还有顶楼,高处有二米多。整个楼房最高处将近十米,每层都有卫生间。院内有廂房、厨房和柴禾房,为给房前屋后的蔬菜地施肥,还另建了厕所。
盖房用了15万,装修用了10万,钱款早就还清了。现在的目标是给儿子娶媳妇。阿姨说:只要儿媳娶进门,心事就了了。
我说:哪能啊!然后又要抱孙子,带孙子。没完没了的事!
阿姨叹口气:我啊,一辈子劳碌命,不晓得哪天能享福?
我说:不要这样说。娶儿媳,就是在享福;抱孙子,带孙子,也是在享福;将来看着孙子每天去上学堂,更是在享福。
阿姨说:叔叔说的是,我以后也要这样看问题。
我说:其实你早就是这样看问题了,只不过嘴巴上没有说出来!
前几天,阿姨一边做卫生,一边与在另一家做卫生的老姐妹通电话,议论着要买什么牌子的汽车,什么牌子的汽车经济实惠能节能省油?
我惊奇,原来这些做卫生的阿姨家已将买汽车提上日程了。等她放下手机,我问:“你们家也买小汽车啦?”
她一下子站起身来,腰挺得笔笔直,扬起眉:“买啦!”
“用得到吗?”
“暂时用不着。”
“用不着买了做啥?”
“叔叔,话不是这个样子讲的。人家打麦场里都停着小汽车,我家就不能没有!”
我说:“买汽车也要攀比?”
阿姨说:“力量够得着,就要攀比;力量够不着,就不比。”
“你们队里有多少户?”
“33户。”
“多少车?”
“20多部,有奥迪、宝马,还有奔驰。”
“你买的什么牌子?”
“福田,15万多。马马虎虎,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两女斗七男
这母女俩,真的是很漂亮。尤其是女儿,二十一、二岁,个头儿高高的,脸模子像只桃儿,身材窈窕。母女俩在路边开了家食品店,什么都卖,粮油食品、蔬菜,还卖文蛤,一筐一筐的放在店门前。
城管领导真有眼光,招来的城管全都靓仔,没有一个歪瓜裂枣。那群男人穿着黑制服,戴着黑帽子。组长今年30多,长得更周正,他走在前面,后面还跟着7个城管兵。他们来到母女俩的小店前,用脚踢装文蛤的筐子:
“收回去,谁让你们放在外面的?”
“收回去!听见没有?”城管的声音一声比一声高。母女俩佯装忙着做生意,谁也不搭腔。
“收回去!听见没有?”
三声喊过,算是先礼后兵了。组长呶呶嘴,身后的小伙就将文蛤筐子往店内搬。
女儿站在门口不让搬:“你们什么意思,三天两头来找麻烦?”
小伙撞开她的身体,硬要往里搬。母亲上前,“你们是不是要小费?是不是没往你们口袋里塞钞票?”
“嘴巴放干净点,谁让你往口袋里塞钞票了?”组长一脸严肃。
搬筐子的城管兵挤不进门,就将筐子放在门框边。
母亲一脸凛然:“给我搬回去!从哪儿搬的还给我往哪儿搬回去!”
组长说:“反了你了!”
双方开始大骂起来。女人一旦骂起来,荤的素的全都有,不堪入耳。骂得城管落荒而逃,围观的群众直叫好。
城管兵在市场上所向披靡,几乎没有天敌。他们的天敌只有撒得开泼的娘们。
哎!糯米粉的香味道!
又到一年腊月里,总想吃汤圆。想吃汤圆还不简单吗,超市有的是。黑芝麻、豆沙、芝麻花生馅,随意挑。可我们家那口子不喜欢吃有馅儿的,只喜欢实心的。久而久之,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要吃实心圆子也很简单,买一袋水磨粉回来自己搓搓就行啊。可我讲究,一定要去买农民自个家做的米粉。前几年还要问是石舂子舂出来的,还是磨子磨出来的?问了几年也没问出名堂。这几年就问是大磨子还是小磨子?是机器磨还是手工磨?
问来问去,为的是惦念着那一口糯米粉的特殊香味儿。哎!
起码也是十多年前,丈母娘还在世的事了。
有一年春节前,丈母娘亲手做了几斤米粉送过来,我们吃到了这样的实心圆子,那种香,实在香,实在是一种说不出的香,真好吃啊!
我问丈母娘:你这个米粉怎么这样香?
丈母娘说:我也说不出。你觉得好吃,明年多做点。
第二年,丈母娘果然早早就做了十多斤送来,我却吃不出那种香味了。
再问丈母娘:今年不是去年的那种味道。
丈母娘说:你的嘴可真刁。今年稻子收成时,天气不老好,粒儿没有这样饱满。米粉磨好后,又接连是阴天。
我说:明白了,今年的米粉缺了太阳的味道。
第三年,丈母娘又送来十多斤,一样做一样吃,仍然吃不出第一年的味道来。三问丈母娘。丈母娘很扫兴,说你们意乖疯!(家乡话,有点不可理喻的意思)从前用石舂子木槌子舂出来的,现在是小磨子上磨出来的,味道当然不一样。
这以后,丈母娘就再也不做米粉送来了,我们也再也没有吃到那一年的香味儿。
果然是往事不可回味,连吃个圆子也是啊!
丈母娘的拿手菜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经过寻婚路上的七沟八坡,终于成了婚。
初为人婿的感觉真很好。第一次走进这另外一个家庭时,感觉与自己的家庭处处不一样。当然首先不一样的是人,老丈人与我的父亲是完全不一样的男人,丈母娘与我的母亲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母亲;其次是物,房子不一样,家俱、布置不一样,床褥不一样,连同扫把、抹布也全都不一样;但最直接的感受还是吃口不一样,印象深刻的还是丈母娘的拿手菜。
其实,丈母娘也并没有什么拿手菜,勉强算得上的就是一道大杂烩。
食材是肉圆、鱼肚、蹄筋、蛋饺、肉皮、炸鱼块、大虾、香菇、冬笋、菜心等,先后下锅,烩在一起,烧上高汤,配上调料,撤上香菜叶就大盆、大碗地端上来了。
这是家乡一道传统菜,婚寿大宴必备,冷盘过后上的第一道热菜,所以也叫“头菜”。通常以价格最昂贵的那道食材定档次:一鱼皮、二海参、三鱼肚。家家户户都会做,我们家也会做,我也吃过无数次。
但是丈母娘做的与我妈做的完全不一样,重油、重色、重味,又香又辣又酸,上面厚厚地铺了一层红红的菜籽油,油上点缀着几根翠得碧碧绿的香菜叶。全家人的眼睛盯着它,全家人的筷子都往这个碗里夹,太烫、太辣、太酸,总是不容易上得了嘴,几筷子菜下来,就忍不住大呼小叫:
好吃啊,好吃!
过瘾啊,过瘾!
解馋啊,解馋!
每个人都不会吝啬自己的夸奖,每个人都即时选取自己的表情包。爱要大声说出来!好吃,也要大声说出来,丈母娘觉得飘飘然,感觉好极了,精神抖擞地在锅台边为全家人操作下一道菜。
这个穷人是怎样炼成的?
我问:“你们队里还有没有穷人了?”
小陶说:“穷人当然还是有的,不过一般都还过得去,只有一个人比较特殊。”
“怎么个特殊法?”
“叔叔,你慢慢听我讲。这个人与我男人年纪一般大,都40多岁,在一个建筑公司打工,我男人做木工,他做瓦工,工资差不多。他娶了个贵州女人,生了儿子,儿子现在上初中。老婆和他离了婚,跑掉了。”
“老婆回贵州了?”
“没有,在苏州一家服装厂打工。两人刚结婚时,日子过得还可以的,家里已经盖了三间房,是平顶,盖房时就考虑日后加盖成楼房。后来这个男人不学好,染上赌博,越赌越上瘾。挣的工钱不够输的。老婆要和他离婚,他不肯。老婆说:你把房子加盖起来我就不与你离婚。男人说,婚不离,钱也没有。扯了几年,女人死活和他把婚离了,扔下孩子跑了。”
“去年他又得了肝病,还有胰臟病,全靠吃药维持,他这种人不穷,谁穷呢!”“是癌症吗?”
“听说还不是。”
“队里有没有对他救济?”
“正讨论呢!村长说要对他扶贫。好多人都不肯。说他是自找的,大家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挣来的辛苦钱,谁让他去‘作赌’呢!作赌就是作死,自作孽!”
“你是怎样表态的?”
“这种事情随大流,大家捐我也捐,看他与我家男人一起打工的情分,人家捐八百我就捐一千。”
“人家不捐呢?”
“人家不捐,我也不能捐。我要捐了,出钞票不说,还要挨大家背后骂。不过我看大家最后还是要捐一点的,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他去死。”
“你们现在队干部还贪污吗?”
“我看也没得贪,手上也没有多少权,大家各过各的日子,到哪儿去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