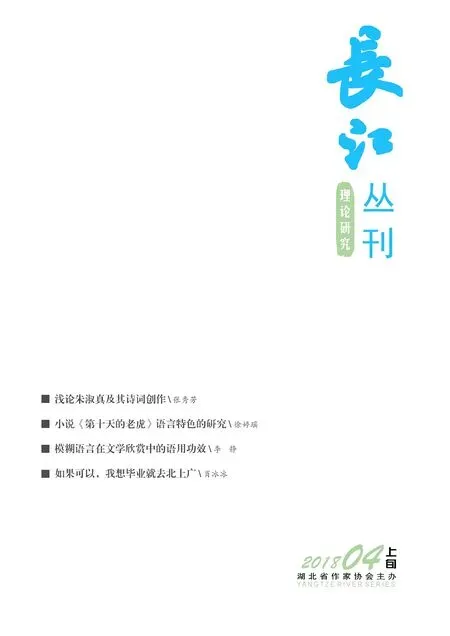别样的故土情缘与文明反思
——阿克日布散文集《温暖的火塘》述评
■/
《温暖的火塘》是彝族作家阿克日布继出版彝文长篇小说《雾中情缘》和文化散文集《翻阅生活的注脚》后,创作的又一部彝文散文作品集,全书共有31万余字,分别由“温暖的家园”、“多情的故土”、“多彩的文明”、“回顾与守望”、“情暖忧伤”等5个章节构成,其中许多文章是近年来作者发表在全国各类文学报刊杂志上的优秀作品。总的来说,阿克日布的散文主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一、倾心抒发故土乡情,表现故乡人情美与人性美,以别样的文人情怀抒写着家乡的真善美,追逐着生活中的光明
故土是作家和诗人的永恒家园,是滋养文学这棵大树的重要源泉,更是激发文学创作者取之不尽的创作灵感之本。作家在在序言里写道:“故乡,对中国人而言,是最清澈的记忆,最温暖的情怀;是心灵的归宿与思想的源泉,更是滋养着我们的最丰饶的一片土地;是这片土地上奇异的万物、多样的风俗民情链接和延续起了一个民族的记忆,人生百态、世事常情都在这片土地跃动、演绎。”因此,在这里,故乡的自然美、人文美、人情美与人性美都成了作家眷恋与讴歌的对象,也体现着作家对真善美孜孜不倦的艺术追求。
可以说阿克日布的散文基本都是写乡土情怀的。作家求学离家,参加工作后虽离家不远,但由于工作繁忙,也不能时常回到家乡,正式因为这种与故乡若即若离的距离反让作家产生了难以消解的思乡情结。对于更多的时候生活在城市,接受了现代文明洗礼的阿克日布来说,故乡是历史的和现实的,是带着理想色彩和梦幻情调的,是最理想的精神泊地和充满真善美的乐园。
在阿克日布的笔下,故乡的风清、月明、水甜、荞香、人纯都映射着自己对快节奏、物欲横流的现代文明和都市生活的倦怠。在《谁在唤我的小名》里,当我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听到老家人叫我的小名时,倍感温暖与亲切,不仅感叹道:“真的,在一个陌生的异乡城市,有人用亲切的乡音唤我一声小名,就像遇到亲人一样。虽然我的小名很普通,也叫得不响,但从山里出来的孩子,谁还没个小名呢?狗子、猪儿、羊子……山里的一切都可以成为孩子们的小名。”
在《寨子里的月亮》里,阿克日布这样写道:
“月亮是寨子里的月亮,只有寨子里的月亮是真正的月亮,城里的月亮,只能看做是挂在夜空的一盏灯,这盏灯发出来的光被城市高楼下闪烁的霓虹衬托得格外暗淡。走在流光溢彩的霓虹灯下的人们,谁会抬起头,看一眼夜空那一抹暗淡的‘灯光’呢?”而寨子里的月亮,尤其是春天的晚上,山民们与月亮的深情就愈发浓烈。炽烈的太阳释放完一天的热量悄悄地躲进山去了,月亮偷偷地从山后爬上来,院里有树的人家,会走出来坐在树下,赏望着挂在树梢的月亮,院里有竹的人家,也都走出来坐在竹下看着竹稍的月亮。
……
故乡,成了诗人疲惫的灵魂的栖息之地,也是诗人真善美的审美寄寓之地。但故乡许多珍贵的东西却在慢慢的变异和消失。诗人的忧伤与惆怅不言而喻。因此这又形成了阿克日布散文的又一个主题。
二、秉持一个少数民族作家的责任意识和使命当担,进行自觉的文化反思
阿克日布一方面以别样的文人情怀抒写着家乡的真善美,追逐着生活中的光明;如《醉人的山野清晨、《寨子里的月亮》、《山里人》、《温暖的火塘》、《温暖的家》、《谁在叫我小名、《思念故乡的炊烟》等等 ,另一方面却从不同的视角关注和思索着故乡在历史进程中那些不和谐的音符。换句话说,在作者的笔下,故乡是令人魂牵梦绕的,但故乡同时也是负重的,故乡虽然在不断前进,但并没有完全摆脱贫困、愚昧与落后,各种不良风气也残存或滋生着。因此作者的忧伤、焦虑与矛盾也体现在了作品中。故乡很美,却也孱弱;故乡有些变化令人欣喜,有些变化却令人遗憾;故乡拥有的东西似乎多了,人文却显出了肤浅与单薄;故乡人见的世面多了,人情却冷淡了。《衰老的村庄》、《与鬼同住》、《无力的火舌》、《即将消失的村庄》等作品都体现出了作者对故乡的历史、现实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深刻思索与严肃思考。这是难能可贵的文人精神。
在《故乡的炊烟》里,当电饭锅、电磁炉、电炒锅、电取暖器等现代科技产品给我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让我们远离了真实的人间烟火,远离了温馨的亲情、远离了烟气氤氲的文明。在《衰老的村庄》里,记忆中满目绿色、炊烟袅袅、虫鸣蛙叫、人欢马叫的景象已不再,眼前的村庄就像一位气数将尽的老人,再无往日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景象;在《废弃的老井》里,昔日泉水叮咚、热闹非凡的水井如今却只剩下颓废和寂寞。”;在《消失的村中小路》里,“我怕是永远也找不到留在那儿的足迹了。”故乡的面目全非让作家隐痛和焦虑,也促使作家对彝寨古老的文明有了更深刻的思考。
三、表现亲情和爱情,抒写母亲与女人,是阿克日布散文的另一重要内容
他写父亲母亲、家庭主妇,赞美她们勤劳、坚韧、善良、默默奉献的精神、写得情真意切、温馨纯美。在《能温暖一个冬天的女人》里,作者这样写道:
“冬天因为寒冷而不讨喜欢,女人们却用自己的智慧与浓情编织出了一个别样的冬天,她们的冬天甜蜜、温暖、幸福,那是属于她们自己的真正的冬天。”《没有男人的寨子》里,“寨子里没
有男人,女人们保护着男人和寨子的尊严;没有男人的寨子,似乎更像一个寨子,没有冲突,有的是和睦、勤劳、诚信和兴旺,寨子永不衰败。”
在《我母亲的手》里,母亲的手让人心痛不已:
“摩挲着母亲被岁月摧残的这双手,粗糙、瘦削、还有些干枯,这是一双衰老了的手,黑黄黑黄的、瘦削的骨架撑着一层粗糙的皮,毫无血色,只能看到凸起的蓝色血管。手掌布满老茧,一条条纵横交错的沟槽像刀刻似的。想当年,这是一双多么细嫩白皙的手呀!她牵着我稚嫩的小手不知行过多少路,跨过多少的沟坎,另外,不知有多少次,在我摔倒时,是这双手一次一次地扶起了我。是如今这双衰老的手,引着少不更事的我,一步一步走向了成熟。”
四、阿克日布也有大量描写彝族多姿多彩的文化的散文,这些散文感情真挚、亲切生动地向读者展现了彝乡丰富多彩、美丽质朴的人文景观
如《彝家披毡暖融融》、《寨子里的木匠》、《寨子里的篾匠》、《难以忘怀的推磨时光》、《老家晒粮的场坝》、《过年杀猪声声入耳》、《家门情》、《寨子里的媒人》、《口弦声声入梦来》等作品。这也成了阿克日布散文创作的一大特点、能满足读者对民俗风情的审美期待。
综观阿克日布的散文创作,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吸收和借鉴了一些小说及诗歌的创作手法。如一些象征性的抒情意象的运用,让散文有了些诗歌似的朦胧的色彩。在《即将消失的寨子》里,作者未提及寨子的衰败景象,而是从对一片懊丧的秋景的凝视中表现对“即将消失的寨子”的失落;另外,阿克日布除了写散文也写小说,他将小说创作中注重心理描写及摹景抒情等手法运用在散文创作中,通过对景物的细致描绘、人物心理、情绪的剖析和内心活动的挖掘把握散文的节奏及中心主题,散文结构较为多元。
其次,作品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作者通过对乡情、亲情、旅食、民居、地理、地方人文等描写,用朴素真切、向善向美的文风,刻画出了彝乡清新质朴、丰富多彩的人文风貌。例如,散文中对彝族木匠、篾匠、媒婆、彝族年、口弦、竹笛、披毡、火塘、炊烟等的抒写,将彝乡的节庆礼俗、传统技艺、居家习俗、音乐艺术等都展示给了读者,增强了散文的趣味性和知识性。
当然,阿克日布的母语散文也有些不足之处,如有的主题内容较为雷同、缺少新意;有的语言冗长拖沓,不够精炼。有的结构枝蔓过多、晦涩朦胧。虽其如此,阿克日布的散文所抒发的人文关怀和感伤感情怀却是难能可贵的,他所呼唤和追求的也是所有远离故乡的游子所向往的心灵归宿和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