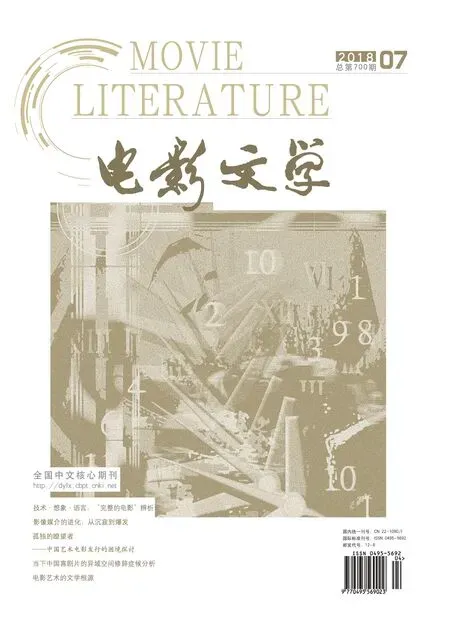中国儿童文学电影改编的美学策略
赵 燕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陕西 西安 710100)
儿童文学拥有着独特的、无可取代的叙事话语,并且能在思想上丰富低龄读者的心灵世界,帮助其得到更为灿烂优美的精神生命。电影这一艺术形式同样拥有着低龄接受者,它没有理由忽视儿童文学。数十年来,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大量中国儿童文学不断被搬上大银幕,为成年和儿童观众提供了一种新的叙事空间和艺术视野。如动画片中,常光希根据民间传说《劈山救母》改编的《宝莲灯》,真人电影中,王好为根据铁凝同名小说改编的《哦,香雪》,戚健改编自郁秀同名小说的《花季·雨季》等。而在改编过程中,电影人又必须考虑到艺术本身以及社会影响等方面的问题,对原著进行一次艺术再创造,展现出属于儿童文学改编电影的特殊的美学策略。
一、道德教化与审美妥协
对于由儿童文学改编而成的电影而言,其观众中必然有一部分儿童观众,电影有引导儿童观众道德品质发展的义务,这也就决定了其在改编过程中必须减少一些有可能出现的负面效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由于原著本身的成就,这样的改编依然是具有艺术支撑点的,但有时候,这种改编也会削弱原著的魅力。可以说,让道德教化影响电影改编,这是一种审美上功利性的体现,是电影在美学上的妥协。
以吴贻弓的《城南旧事》(1983)为例,电影改编自林海音的同名短篇小说,这是一部在中国儿童文学电影改编史上具有丰碑意义的作品。原著本身固然具有一定的艺术高度,但考虑到原著的容量和大量的“闲笔”,电影还是进行了大量改编,而其中有一部分改编,就是出于社会道德评价体系上的考量,对原著做出的裁剪。
例如,在原著中,父亲的形象是一个旧式文人。林海音曾写过自己的父亲和兰姨娘一起躺在床上烟雾缭绕地抽大烟:“我坐在小板凳上看兰姨娘的手看愣了,那烧烟的手法,真是熟巧。忽然,在喷云吐雾里,兰姨娘的手,被爸一把捉住了,爸说:‘你这是朱砂手,可有福气呢!’兰姨娘用另一只手把爸的手甩打了一下,抽回手去,笑瞪着爸爸:‘别胡闹!没看见孩子?’爸也许真的忘记我在屋里了,他侧抬起头,冲我不自然地一笑,爸的那副嘴脸!我打了一个冷战,不知怎么,立刻想到妈。我站起来,掀起布帘子,走出卧室,往外院的厨房跑。”而此时,“我”的母亲正在怀着孕忍辱负重地操持家务,“我”虽然对母亲充满同情,却完全不知道应该如何表达,而只是跟母亲说“我饿了”,结果反而被母亲误解为不心疼妈妈。除了抽鸦片以外,父亲还曾经在日本吃花酒,并且一吃就是沿着一整条街吃下去,从天黑一直浪荡到天亮,母亲则一直在家里等候自己这个荒唐的丈夫。而在电影中,类似的情节被完全删去,父亲的形象得到重塑,父亲在小英子看来是一个宽厚、顾家,和母亲恩爱有加的好男人,最终父亲英年早逝,留给了小英子一个永远完美的形象。由于父亲的形象被进行了改动,有关母亲的情节也显得更具温情。
尽管从表面上看,妥协于现实中的道德底线而不得不进行上述改编,是对原著一种审美上的损害,但是从传播效果来看,一则这样的改动促进了原著为更多人所熟知,二则就艺术性而言,人物的性格也因此而更加集中,即脸谱化,人物关系更少(虽然最后嫁给德先叔,但是与父亲有着暧昧不清关系的兰姨娘被删去)拥有着另外一种艺术效果。
反过来,弱化原著道德说教意味的改编同样是存在的。施祥生的《天上有个太阳》被张艺谋改编成了《一个也不能少》(1999),电影也同样做出了大量成功的改编。在原著中,王校长才是整个故事的主人公,小说也因此成为一曲对师德的赞歌,在小说的结尾,王校长因为心脏病突发而去世,小说完成了对一个道德楷模式人物的塑造。而在电影中,主人公变为懵懂的少女魏敏芝,魏敏芝答应担任代课老师和去寻找张慧科,其动机都是因为钱,导演并没有人为地将主人公的行为高尚化,甚至配角的言行也隐含着导演隐晦的批评,如电视台主持人在进行捐赠时问张慧科的话语带着不自觉流露的优越感等。导演完全以一种含蓄的方式,展现着人们在巨大城乡差异下的伤痛,但也正是这种成人世界的残酷,凸显着儿童美好的本性。也正是这样的改编,使得电影虽然脱胎于儿童文学,但是已经高于儿童电影,进入到了更为高级的境界中。遗憾的是,由于张艺谋给予了整个故事一个较为圆满、积极的结局,以至于其在《一个都不能少》中的审美品位和改编策略一度遭受人们的质疑。
二、游戏精神的发扬
如果说,基于道德教化而做出的改编更是一种针对社会影响的,略显不得已而为之的考虑,那么高举娱乐性则显然是一种面向大众市场做出的改编策略。电影本身就是一门拥有着娱乐功能的艺术。而部分儿童文学正是因为具有喜剧风格以及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先天地能满足观众的娱乐需要而得到电影人的偏爱。加上游戏又是儿童的天性,热闹、有趣、让人眼花缭乱的游戏性叙事极能获得儿童的欢迎,部分儿童电影在改编时高度重视游戏精神,以最终提供一个合格的娱乐产品。
在儿童文学中,不乏大量本身就具有游戏精神的作品,而部分电影则对此进行了继承与发扬。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以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1992)、《小英雄雨来》(2009)为代表的一系列以革命战争为题材的儿童电影。《小英雄雨来》改编自管桦的同名爱国主义作品,以晋察冀边区的少年,有“孩子王”之称的雨来面对日本侵略者时的英勇事迹为主要内容,雨来也以胆识过人、机智灵活而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小英雄。无论是在原著抑或电影中,原本雨来和日本军人都是处于完全不对等的强弱关系中,但是由于对手的非正义性,雨来必须是对决中的胜利者,他不仅能在残酷的战争中保全自己,还能戏耍敌人,只有儿童形象得到这样的拔高,儿童和其监护者才更加乐意接受叙事。电影忠实地继承了原著中的游戏精神,以雨来为日本军人设计的几个小把戏串联起了剧情。同时,又将这种游戏精神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扬,日本鬼子和宪兵队一干人在雨来面前完全成了智障者或小丑,面对雨来的弹弓无法招架,被打得落花流水。这种弱不禁风的敌人无疑大大地增强了电影本身的喜剧感,让观众获得了精神上的极大愉悦。但电影这种对娱乐性的妥协也使得电影遭受了过度弱化侵略者,在叙事逻辑上失真的诟病。
而还有一部分文学作品,其本身虽然具有一定的趣味性,但是游戏感并不强。电影则在改编中或根据时代审美而增加剧情,或利用现代技术而制造炫目的视觉效果,全方位地提升电影的娱乐性,让儿童观众在观影过程中犹如参与到一场狂欢游戏中来。例如,张天翼的《宝葫芦的秘密》曾经在1963年被杨小仲改编为同名电影,朱家欣和钟智行又在2007年进行了翻拍。两个版本之间的巨大差别,就非常能体现这种游戏精神的区别。虽然两部电影都继承了原著对儿童观众不要产生不劳而获念头的教育意义,但前者基本上完全遵循原著,电影所要体现的是一种符合前述道德教化要求的现实批判精神,而由中影集团与美国迪士尼联手打造的后者则无论是在叙事上,抑或在影像上,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对个性化娱乐的张扬。在1963年版中,宝葫芦是一个颇具邪气的宝物,它不断理所当然地、看热闹一般地陷王葆于麻烦中。而在2007版中,宝葫芦的性格则颇为呆萌,它不断地为王葆搬来他脑子里想要的东西,完全是出于想讨好小主人的单纯愿望。在叙事上,电影加入了王葆想成为像杨利伟一样的大英雄,去美国太空维修站大显身手救人,然后手持鲜花对人们挥手致意,王葆看电影《恐龙反击战》然后想与恐龙展开大战等情节,显然是迎合了当代深受超级英雄电影、科幻电影影响的小观众的心态,相比起原著中王葆喜欢下象棋、看电影更贴近大部分当代儿童的现实生活。同时,在迪士尼的帮助下,电影在视觉上也极为绚烂恢宏,如玩具被从店里搬到了王葆的家里,玩具们犹如《玩具总动员》(1995)里一样组成大军排队迁徙等,这些风趣的,同时具有好莱坞水准的场面都是1963年版在技术等因素的限制下无法呈现的。2007年版的《宝葫芦的秘密》在上映后获得了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儿童片奖,也获得了观众的一致认可,可以说是与对张天翼具有时代烙印的文本进行了合理的、极具游戏精神的打磨抛光分不开的。
三、儿童主体性的保留
儿童主体性在儿童文学电影改编中是否得到彰显,是与大量儿童电影出现的过度成人化问题分不开的。一般情况下,儿童理应拥有属于儿童的兴趣、意志以及行为习惯,但是正如前述提及的道德教化的原因,在部分电影中,由于主观或客观(如原著的立场与角度)因素的影响,儿童寄托的是属于成人的情感意志、人生价值或道德期待。例如,在胡红一的报告文学《感天动地父子情》在被江平、刘新改编为《真情三人行》(2001)后,观众看到的是一个理想化了的,能在稚弱之龄就承担起先后失去父母这一痛苦的男孩童小阳。而在童小阳的成长过程中,一直扮演阳阳妈妈的善良的班主任于乐老师,正直的公务员父亲童阿明,以及市井豪侠虾球叔叔等人也给予着童小阳关爱和教育,让后者得以在一夜之间长大,成为社会需要的自强自立者。而这种“长大”,也就意味着儿童主体性的失去。与之类似的还有徐耿的《红发卡》(1996)等。两部电影都有着共同点,家长的一方遭遇重大变故,另一方则对孩子隐瞒事实,而儿童终于得知真相,并在他人的帮助下勇敢面对残酷的事实。这一类电影中的儿童其实都是成人期许的具象化,他们更像是“小大人”而非儿童。
而在张郁强根据秦文君小说改编而成的《男生贾里》(1996)、《男生贾里新传》(2009),根据杨红樱的《杨红樱童话集》改编而成的《淘气包马小跳》(2009)等电影中,儿童能够不承受其不应有的社会责任与精神负担,依然以属于儿童的身心特征去生活,甚至表现出儿童的缺点,如极为顽劣、调皮,过于充满好奇心等,成年人没有代替儿童去做出道德判断或人生选择。例如,在《淘气包马小跳》中,马小跳因为不喜欢秦老师,屡次三番地对秦老师做出如拔单车气门芯这样的恶作剧,仿佛一个违背了成人教育期待的“坏小孩”,但这样的主人公才是具有儿童主体性的,也是符合杨红樱原著注重外部冲突的美学观的。马小跳将自己和秦老师之间的矛盾当成是“敌我矛盾”,同时十分讨厌自己的同桌路曼曼和学习委员丁文涛这些秦老师的“同伙”,这虽然是错误的,但是从马小跳对社会的接触来看,他由于才刚刚上三年级,并没有真正的成熟,缺乏与其他成年人之间的交往,产生这种想法其实是正常的。
从近年来的中国儿童文学电影改编中我们可以看出,电影人在对受众需求和文艺教化功能等进行了考虑后,对电影普遍采取了重视理性教化,兼顾强化娱乐功能,注重儿童主体性的改编策略,以使电影尽可能不逾越审查的限制,不违背儿童的趣味与本性,让故事进一步走向市场,使原著的影响力得到进一步的扩大。这三者是三个既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美学策略,同时在具体的操作中,由于电影的目标受众、电影本身的定位等各不相同,也存在对上述策略“反其道而行之”的现象。
——两岸儿童文学之春天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