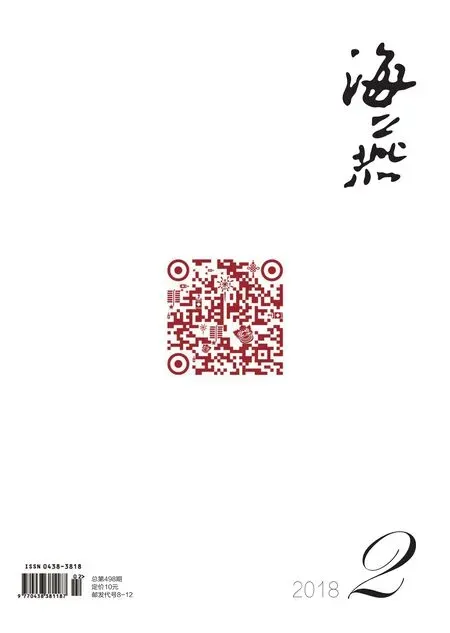大海草山:父亲的草帽(外一篇)
□鲁云
云南多山,云南人自称“山国的子民”。这里的城里都能望得见山,出城更不用说了。山在大地表面浓墨重彩地纵横驰骋,也成了大地本身。等山闲了倦了烦了,留出一块空地儿,云南人叫坝子。坝子交通便利适合农作,稀罕的不得了,历史上多少民族部落争夺了多少年。
云南不同方位的山,各有脾气性格。滇西南的山丰茂,一年四季绿意葱茏,加之多雨,像个阔太太,如高黎贡山。滇东南的山秀美,因是喀斯特地貌的缘故,一座座不大的山头散落开来,在一湾湾水里揽镜自顾,像小家碧玉,如普者黑。滇西北的山卓绝,多是雪山神山,直插苍穹,遗世独立,宗教神话多如石头,像梅里、玉龙,为“隐士”。滇东北的山雄厚,山体既大又不孤绝,生民繁衍利乐者众,堪称山中“仁者”,乌蒙山是其代表。滇中的山,则是取了四方兄弟的平均。
在云南多年,感念最多的还数滇东北的山。每次穿行其间,群山峻拔挺立,扑面而来,围的你如铁桶一般,又或者远远列阵,望之无垠。山就像巨大的臂膀揽着你护着你托着你,有点压迫却也安稳。滇东北的气候更像北方,轮回的春萌动夏苍翠秋枯黄冬洁净兼具一身,看多了也不觉得闷。若再配上白云生处星星点点的人家,便入画境。
不知怎的,大海草山虽只去过一次,却总对她念念不忘。
大海草山在曲靖会泽,紧挨着昆明东川,为乌蒙之巅。大海本是彝语,意为“台阶最高的地方”。我几次到会泽,一直没去爬过。她的图景倒常见:宾馆画册里,饭店的招贴画上,平民家的相框里,融入了当地日常。越是知名景物,我越不急着就它,心里故意留存些距离,也怕见识后不过尔尔。不过对着大海草山的雄姿倩影,确实生出几分期待来。
八九月是大海草山最招人的季节。山上繁花开放,绿油油的草场吸足了雨季水分疯长。说是繁花,其实都躲藏在绿草中间,细细碎碎的,算不上似锦。大海草山海拔有三千多米,草匍匐在地,浅草才能没羊蹄——山顶马和牛都少,多的是绵羊,山羊受不了长年的高寒。一站在这云端花地毯上,冷飕飕的风就来问候,带着湿气朝你衣服里钻,像是来取暖似的。茫然四顾,连绵起伏的山丘如大海涌起波涛,近二十万亩草场,足以把渺小的自我消融。
我在最丰腴的季节来到大海草山,却又幻想起冬日她的清矍俊朗来。雪把大海草山染得像头上的云一样,到处白晃晃的,蓝天落尽山坳里。绵羊或者牦牛在向阳的山坡上啃着枯草,两三个裹着厚厚毛毡的牧人,哈着热气打招呼,四野满是荒凉的静。在这里可以远眺牯牛寨,是为乌蒙山主峰,南诏时被封为东岳,又称绛云弄山。《东川府志》说它“垂冈绝崖,危峰矗立,常有云气覆之,每天晴日朗,苍翠欲滴,滇中四五百里皆见之”。秋冬时节才少云雨,彼时在四五百里外的昆明,悠然欲见牯牛寨,这是何等惬意。
如今山上条件还简陋,吃食有名的是烤羊肉串和牛粪烧洋芋。烤羊肉串的地道自不必说,牛粪烧洋芋值得一提。找几块石头垒个窝窝,没有树枝柴火,就四处捡拾些干牛粪,把洋芋埋进去,生火浓烟起,呛得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等上一阵子洋芋烧好了,蘸点火红的辣椒面,是雪原上牧人的家常便饭。
洋芋就是土豆,滇东北人吃洋芋很有一套,花样繁多,洋芋品种也多,外地人无不惊叹。窃以为,乌蒙山区和洋芋的瓜葛可谓深矣。云南其他地方的人,中国其他省份的人,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也多吃土豆,但像乌蒙山地区这么顿顿离不开,吃出名气也吃进骨髓里的,怕是不多。嗜好吃土豆,大约代表了一种生活上的贫乏、冷酷和顽强。滇东北人口密度大,大山上生存资源又少,故而山民居住特别分散,山腰一两家,山头三四家,老死难相往来。乌蒙山是仁厚的,倾其所有生养利乐她的子民,东川自古炼铜,鲁甸朱提银也曾兴盛一时,如今掏空了枯竭了,便用身上的树和草,用赤红的粗砺的肌肤,给越来越多的人土里刨食。越是见其荒蛮,越是见其贫瘠,我越对乌蒙山满怀尊崇。所谓“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其情其志刻骨铭心。
我见过乌蒙山发怒的时候。或是不满上天让她亘古的苍凉,或是厌弃了子民无止境索取,彝良地震、鲁甸地震时,她尽显凶恶的坏脾气。山河破碎,村庄滑入河谷,房屋被巨石洞穿,横祸如雨,人命如蚁。她时而雷鸣咆哮如野兽,气得身子发抖,没来由似的,又无从劝说,只能由她顺她敬她,以命饲喂她,等她消了气安静下来。她发怒时也痛苦地撕开自己胸膛,像母亲的捶胸顿足。但她终究拗不过日子,平息下来后,又不知疲倦地生养起来。
有时候她也生闷气。2010年前后,云南省连续旱了三四年,乌蒙山地区旱的尤为邪乎。我那时到了偏远的马路乡,在她深刻的皱纹里,土地干得冒烟,龙潭的水都枯了,人们背着桶赶着牛车,从她的一个毛孔辗转另一个毛孔找水。对那些脸脏得黢黑舍不得洗得山里娃,一瓶矿泉水是最好的礼物。一批又一批山民眼含热泪和她做别,去遥远的富庶的地方打工。她不言不语,像绝情的母亲把孩子赶出家门。
“他们会回来的”——她或许这么想。
在乌蒙山,我见过一贫如洗的农户,见过最孤独的牧羊人,见过酒量豪气俱佳的朋辈,见过高山上的俊鸟,见过可以烙鸡蛋的干热河谷,见过这个世界复杂纠结的一面。最动人的是大海乡上下学的孩子们。为了安全,他们凑成一伙,排着队扛着红旗走在山谷羊肠小道上,他们的脸上写满憧憬,他们的歌声稚气纯净,在苍天大地间回荡。或许,他们诅咒过这山,也急于逃离这困苦贫穷。不过我敢打赌,当他们远走他乡建功立业,多少年后魂牵梦绕的,还是乌蒙的山川草木人情世故。
仁者爱山,乌蒙如父,乌蒙就是这样的山之“仁者”。他不是不发怒,贵在他不离不弃;儿女不是不怨他,但生于斯长于斯埋于斯,打断骨头连着筋,怎么都离不开他。乌蒙磅礴,展现的是生存的张力、生死的依存。
大海草山之所以令人感念难忘,在于它是这位父亲的草帽吧。
边城的早晨
没有什么比置身边城更让人觉得新鲜的了,特别是在万物苏醒的早晨。云南边境线长,沿边二十多个小城各有风格气质,徜徉其间,浓浓的异域感让人目不暇接。小城多恬淡自足,静谧安详地足以激起淡淡乡愁,他乡牵绊着故乡,让游子不能自已。
芒市在云南德宏州,德宏是傣语音译,意为“怒江下游之地”,居者多傣族、景颇族。芒市的名号,却是“黎明之城”。相传佛祖来此地时正值晨曦,雄鸡啼鸣,轻雾萦绕坝子,碧绿晶莹如翡翠,即呼为“勐焕”,为芒市来历。我出差习惯早起闲逛,来芒市更不容错过。
早晨六时许,慵懒的黎明姗姗来迟。搁下手里一本写20世纪现代主义的书,收拾停当,喀的一声带上房门,也走进了一方“现代主义”的天地。芒市我到过几次,不算陌生,但每次来新鲜感都如影随形:植物繁多而不识,大都呈现出某种夸张的姿态;气候偏热也不过分,氤氲着“一股荷尔蒙的气息”;建筑风格鲜明却随意,浮现出边城特有的散淡气质;人物嘛,客客气气里多少有些拘谨。
秋雨刚过,空气凉丝丝的,似会沁出水。等午后阳光普照,溽热的气息会让你无处躲藏——金色的阳光落在身上,像无数只蚂蚁爬过皮肤;落在树叶子上的,会给它们涂上一层闪亮的革质。最妙的是雨后的阳光,于树影下逆着光线看上去,似有似无的水雾在梦里漂浮。
出宾馆右拐,约莫二三十米,见有两座寺庙,观音寺和菩提寺。枝叶繁茂的三角梅和七八层楼高的榕树,在其中葳蕤相望。榕树矗立街心,浓荫之下庇护的,竟是财神关羽的神龛——看得出香火旺盛。一个穿长裙的妇女一边收拾残香,一边招呼路人烧香。说的是民族话,电动摩托车从她身边一闪而过。
宾馆旁有条小河,河水失去了雨季时的肥壮勇猛,只剩下清澈的几绺,欢快地穿过石桥,在水草的掩映下奔向远方。散乱的河床上,早时冲下的竹竿搁浅了,徒然回忆着它的青春,回忆在村寨里迎风摇摆的苍翠日子。溪水随阳光一路跳跃而来,遇着大些的石头激出浪花,雪白喧腾凉而不冷。几枝牵牛花顺着堤岸探下腰身,是为了水中倩影,还是哗啦啦的和鸣?
河岸上立着一株罗汉松,周围只此一株,又高大疏朗,像是一次拆除留下的建筑骨架。罗汉松在这里并不多见,应该也非当地优势树种。它的姿态,虽合乎汉族人的性格和审美,却与这里大异其趣。莫非是哪个外乡人移来种在庭前,借以怀乡?我猜测着这棵树的年纪,应该活过了几代人,来历渺茫了。
继续前行。蒲葵正抖落叶尖的露珠,假连翘吐露蓝色的花瓣,几朵软枝黄蝉花朵艳丽却不俗气。它们不属于我的童年,总像来自另一个空间;又或者,是我这个“外乡人”闯入了它们的空间。当我问询路人另一棵树时,竟是菠萝蜜。菠萝蜜我认得,前提有菠萝蜜果实,从树干、枝杈间涌出鼓鼓囊囊的一团,像是吃饱的牛胃,口感也怪怪的。芒市的街边多果树,城市也就成了大果园。
行走边地,常常于智识上感到羞愧。云南是动植物王国,能叫得出几棵树的名字算不错,你对着一株植物流连赞叹,耳目欢愉之后,脑子里仍旧空白。至于当地瑰丽多姿的风土民情,更令人无从置喙。干栏式的宽敞竹楼,利于防潮通风取暖;人字形的屋帽和陡落的屋顶坡面,除了躲雨排水,和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哲理有何相通?明王朝时这里是“麓川王国”的地盘,三征麓川的历史烽烟,如何注定了帝国的统治边界?这些稍动心思的追问,迷幻般的风情,也让人不免“遥襟甫畅,逸兴遄飞”。
想着想着,一棵大叶绿萝突然挺立面前。夏季的雨水滋养了她的丰腴,叶片像面蒲扇,蜷曲的茎蔓大拇指般粗细,顺着枯树向上攀爬,一直爬出仰望的视野。她应该是自由惯了,虽在道边却不加修饰,在微风里窃语,在狂风中大笑。她大口吞吐着周遭的空气,身体能撞碎午后的骄阳,绿油油的一大蓬里,又隐藏着某种疯长后的空洞……
不远处便是街口,一棵大榕树适时出现。街口是卖早点的风水宝地,但如果没有大榕树的庇护,饭是吃不安稳的。早点摊的摆设,像它的口味一样鲜爽简洁。几张桌面斑驳的桌子,数把低矮破旧的板凳。桌子上的调料却蛮丰富,盆盆罐罐的摆了十多样。不论饵丝或米线,这里的口味清爽酥脆,且酸辣开胃,不像昆明小锅米线油乎乎的让人生腻。德宏最绝的早餐,是盈江县的糯米饭团加风干肉,把黏糯和劲道、米香与肉味调和的刚好,一点都不累赘。
几个穿校服的学生正在吃早点,叽叽喳喳的笑闹着,就像是路边林中的鸟儿飞了过来。孩子们的脸上被阳光涂满欢欣,并没有课业负担过重的疲惫,她们的学校就在旁边,里面已经鼎沸了。我在学校对过,看到一排青灰色的砖房,红色的木棱窗往上是楼顶的几株荒草,再往上一片瓦蓝。“民族文化工作队”的牌匾树立在门口,一个俊俏的小伙子,端着塑料盆,踩着人字拖走下水泥楼梯,幽幽的,悠悠的。
因为多雨而不太冷的缘故,芒市的四季没有枯萎和衰败,永远生机勃发的样子。亚热带季风的气候,让当地人对北方的寒冬和荒漠会产生“色差”,且不说身体肌肤粗砺的感受,光是视觉就让“北方”遥远而不真实。我从北方来,对南方的温软和家乡的硬朗俱有感受,渐渐理解了云南人的“家乡宝”。你听听芒市人的口音,味道宛如丛林里的绿植和四季花香,怎会生出某种生硬呢?
想这些的时候,我已踱回宾馆的庭院。上午的边城正在变幻她的妆容,至下午再至晚上,那又是别种风味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