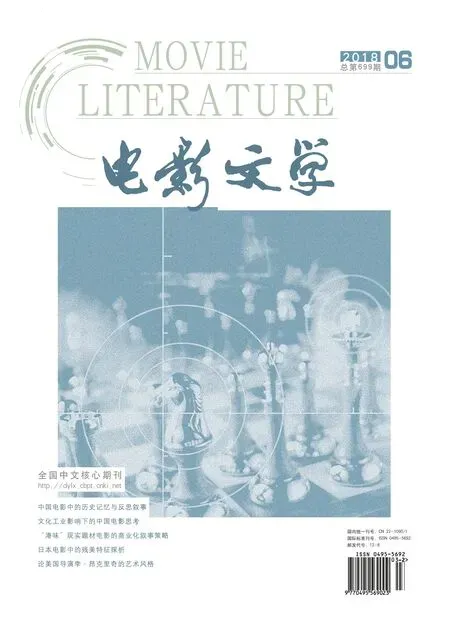蒂姆·伯顿动画电影的哥特文化
刘延斌
(牡丹江师范学院,黑龙江 牡丹江 157011)
德国著名学者威廉·沃林格尔曾经认为,“哥特”是一个具有广泛意义的词汇,它所指称的内蕴不仅仅只是通常意义上的西方中世纪时期(公元5—15世纪)的某个历史阶段,更注重的是它表征着某种独异性的文化风格与“思维习惯”(mental habit)。因此,“哥特文化”影响所及的,在深层意义上指的是一种由哥特式文化形态的直观体认而领受到的哥特人面对世界、宇宙时所生发的一般精神观念或心理状态。这种文化形态,在不断发挥影响的过程中实际已渗透到世界上每一个文明和每一种艺术样式之中,电影作为现今最通行的文化产品,自然概莫能外。
美国导演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就是因为渗透着浓厚的哥特文化基调而为世人所瞩目。这位即便在好莱坞也以标新立异闻名的鬼才导演,自1982年执导《文森特》一片以来,几乎所有的作品均以前所未见的怪诞、夸饰、黑色幽默、恐怖、颓败等创新符号牵动大众的眼球,以诡异又“作者风格”明显的哥特式美学风格赋予动画电影有机生命的活力,成为电影美学乃至文化研究领域所需要观照的重点对象。从哥特文化角度分析伯顿的电影是很恰当的。
一、形式:哥特式美学的影像奇观
所谓哥特式文化,就历史美学的角度而言,首先指呈的是一种艺术风格和美学格调,它具备强烈的形式感,偏好黑色的基调,充斥吸血鬼、阴森古堡等异端形态符号,阴郁、神秘、诡异、变幻莫测,表征出荒蛮、黑暗、落后的形式情感。蒂姆·伯顿的动画作品,在美学形式维度上所体现出的主要特征,恰与之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一方面,在空间场景的审美样式上,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一反好莱坞主流动画,诸如迪士尼、皮克斯等典范性的形式基调,以与主流动画背离的决绝姿态,刻意寻求哥特文化的美学传统,展示顽强的开创动画电影新形式的生命延续力。在早期的电影实践中,蒂姆·伯顿就已经有意识地做出这样的美学尝试。《甲壳虫汁》(1988)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蒂姆·伯顿哥特式文化情趣”作品:它一反动画片朴素的善恶观和场景基调,将作为主要场景的小镇渲染得颓废而怪异,若阴若明的光线、光怪陆离的建筑颜色、不成比例的房屋构造等都有着哥特式情调。而作为鬼魂出现的夫妇更一反惯例成为正派角色。这一切,在空间场景上无不流露出哥特文化风格,对暗黑世界描绘的偏好、对角色命运错位的偏好昭然若揭。在2005年度推出并广受赞誉的《僵尸新娘》一片中,主人公维多利亚及其亲人们生活的家庭、教堂等场景,就是典型的早期哥特式建筑风格,峻峭严肃的外观、顶置高耸的尖塔、狭长深幽的拱状花窗,伴随而至的是怪诞莫名的人物形象、压抑阴恐的场景,以及不自觉弥漫其间的哀伤、忧郁、恐惧、死亡的气氛。这种哥特文化的影像奇观立意,让蒂姆·伯顿的作品一跃而为动画电影的另类经典。
另一方面,在人物塑造上,蒂姆·伯顿大刀斧阔地一改动画人物的“童真特性”,以哥特文化的美学观照加以改写,在哥特文化的美学体系中找到独有的立足点。在人物形象的展示中,蒂姆·伯顿几乎动用了哥特文化美学感受的所有方式——癫狂、古怪、奇特魔幻、反叛孤冷,每一个人物的出现,都在神情、行为、言语乃至衣着上给人失协混杂、破碎支离的感觉,呈现出一种哥特式的“反秩序化”的美学颠覆色彩。伯顿执导的《狐狸与猫狗》里的狐狸陶德和猎狗小铜、动画短片《文特森》里的小男孩文特森、《黑魔神》里的塔兰,以及他参与编剧的《圣诞夜惊魂》里的南瓜王杰克、《飞天巨桃历险记》里的小男子詹姆士、《脏男孩的世界》里的凄凉可怜的“脏男孩”等,无一不是最广泛意义上的哥特式文化审美视角下的角色类型。他们大都缺乏人类属性的生命活力,线条僵硬,神色呆滞,曲线硬直,甚至块状形体常以扭曲面目出现,属于最极端变形的形象。在一般意义上,这些人物哥特式、奇观化的形象符号,可以说完全是人类面对外部世界迷茫状态时一种疏离抑或异己的感觉。
二、主题:哥特式世界的精神迷魅
所谓哥特文化,不仅仅只是体现在艺术形式感上,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其精神世界的结构样式。正如文化学者的研究所表明的,哥特文化的艺术趣味及其独异的情感症状和精神状态,很大程度上借由浪漫主义文学尤其是浪漫主义诗歌所激发而起的,其间夹杂着神秘隐微的自然观、虔诚的宗教观,还有悲怆的宿命情怀等因素。而在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世界里,其思想源流和镜像语言明显都是这种哥特文化的流衍,是哥特文化中颓废意识、怀古幽思、传奇情怀、亢奋情感、冰冷趣味的动画式载体存在,凸显出一股无法言喻的审丑美感和神秘主义。
首先,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其世界观几乎完全为一种“审丑”情感所占据,仿佛是哥特文化精神的记忆之灯。蒂姆·伯顿的作品,似乎有意将已经远逝的哥特文化世界历史化,把其作为人类的一种历史记忆加以保存,并将这种“审丑”的冲动置于动画电影这样的纯真世界的圣殿和家园之中,形成二律背反状态的扭曲感,以期形成某种回应。《圣诞惊魂夜》里作为主人公讲述的南瓜王子,所有的“美”俨然都是依据最丑陋的自然形态的法则所建构起来的。其形体直接就是一个骷髅,细长不成比例的四肢、空空如也的面部表情、眼睛和嘴唇都形似深窟,古怪而忧伤,有着形象化的哥特人物风格。《僵尸新娘》中本应该是童话世界中的公主形象出现的艾米丽,更是外表极端丑陋,破败如棉絮飞舞的婚纱,两道显著的八字眉横穿脸庞,眼珠若有若无仿佛随时可以滚落,大腿和手臂都出现腐败痕迹,白色的骨头历历在目。《文森特》中的7岁男孩文森特,在蒂姆·伯顿的动画人物系列中已经是最接近“正常人类”形态,但依旧俨然是像弗兰肯斯坦一般被恐怖所控制的邪恶体,幻象的所有场景都是和蝙蝠、蜘蛛之类共居一室等。蒂姆·伯顿的动画世界,完全是黑暗力量所主导的,哥特式的、丑陋的人物和场景无疑对观看者的审美接受造成一种震撼性的考验和冲击,但也正是这些哥特文化渗入的独特和新颖,在非常大程度上破除了观看者历来积淀而成的对动画电影的固板认识和审美期许,进而反倒拾获了更为丰富的审美体验。
其次,哥特文化神秘主义的世界图像在伯顿的动画片中,完成了艺术和现实的联结,在荒蛮的迷魅书写中成为其艺术精神的本源指向。著名学者卡尔·舍费勒在其名著《哥特精神》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哥特文化的核心要素是神秘主义的,是一种与理想中有序的、规则的、静态的、知识性的世界样式相对立的,呈现出怪诞的、创造性的、耽于想象的、动态的世界图景。伯顿的作品,始终都致力于创建挣扎的、毁灭的、骚乱的电影形式和世界想象,正是与哥特文化精神一脉相承的神秘品质。他所推出的20多部影片,都是清一色地运用他那似乎与生俱来的哥特神秘文化力量的感知,操弄惊世骇俗的表达方式,在电脑CG成为主导的当代动画界别具一格地让“伯顿式”在动画类型电影领域打下深刻的烙印。《火星人玩转地球》是其中一部哥特神秘意味深厚的影片。这种动画片完全是在一片荒诞和神秘的哥特式模式中完成其前后叙事的:神秘而丑陋的外星人带着和平的使命来到地球,却莫名其妙地遭受到激光枪的进击,狂妄又歇斯底里的科学家被火星人毫无征兆地砍头;《圣诞惊魂夜》是导演首次全面试验其所历来推崇的模型定格动画技术,也正是在这种技术的协助下,影片将哥特文化的神秘主义要素渲染得更为淋漓尽致:主人公阴森不自然的面目与神情,头部为三角状的宠物狗、黑猫、鬼娃娃音乐盒子等人类幻象中的神秘怪物充斥银幕。这些神秘主义的主题阐发,就功能主义而言,迅疾地让伯顿把人类隐秘中的心理骚动转化为惊悚但热切的艺术样式,并在日益固化的动画电影创作中展示颠覆力量。
三、内核:哥特式结构的文化反思
对于一个致力于经典电影创作的导演而言,所有的形式、主题都只是一种桥梁。正如论者普遍指出的,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绝非只是有意耸人听闻,制造视听上的惊奇感受而已。实际上,伯顿在动画电影中如此不遗余力地对哥特文化进行阐发,其最终意图旨在使哥特艺术形式体验所附带的文化性意义和现实那些有针对意义的精神趋向联结起来,在复归传统的可能性书写的同时,传达自身的思想倾向和内核机制。
一方面,伯顿的动画作品在对哥特文化一般心理和精神结构的书写中,渗透着一种隐喻色彩,其所不遗余力宣扬的罪恶、丑陋与堕落,实质上是在剖析和表征着人类社会和人性的悲哀之感。伯顿在作品中都夸饰性地对阴暗事物做出强调,以期观众借由他的眼睛看到人类灵魂丧失之后悲哀和空虚的可能,完成对精神麻木的现代人的映射意图。这一点,在《僵尸新娘》中有着最触目惊心的展示。片中,伯顿巧妙地呈现了两个决然不同但又并非泾渭分明的世界——地下世界和地面社会。地下世界是鬼魅横行的黑暗古堡,本应让人惊怕的鬼魂们却歌舞升平,衣着鲜艳,热情灵动,有着无限的活力和幽默感;而地面的世界,线条笔直,建筑灰色,陆地尘积,大地空旷而荒蛮,生活其间的人类严肃而压抑,不近人情极端苛酷,在刻板的生活行进中毫无情感表征和人性温度可言,虽然是血肉之躯,却虽生犹死,在弥漫的绝望和死寂中残喘余生。伯顿正是运用这样的隐喻性的思维方式,将哥特式的鬼魅世界和现实人生两类意象做出叠加呈现和对接叙事,从而传达出他对人类情感缺失的忧虑。
另一方面,在哥特式的视觉再现中,伯顿深层次地触及了人类的内心体验,寄托着对于生命、欢乐、孤独、死亡、永生等哲学命题的深沉思考,并在荒诞不经的情节设置、暗黑的基调处理中承载着对最纯真、最温暖的人性的心向往之的情思。伯顿的动画作品,自始至终都在死气沉沉的叙事后留下光明的尾巴,展现另类的魅力,在无可奈何悲凉难喻的同时依然充满温情和光明,这正是“伯顿式叙事”,即在让观众惊吓不已后给予的是愉悦的感受,而不是全部都由绝望、死亡和悲伤等负面情绪贯彻始终。以《圣诞惊魂夜》为例,主人公杰克外恶而实际心善,虽然一直以来他都是周遭世界丑陋和惊悚的代名词,但他并没有因此而对生活的世界心生厌弃之感,依然不甘于沉浮于这样的境遇之中,内心深处始终渴望和憧憬着被人们所喜欢。他在那些本应隐秘的活动中,却公然地表现出自己的“坏小孩本性”,甘冒不韪地领着鬼魅们绑架人类美好化身的圣诞老人,意图在已有的秩序外重建属于异类的圣诞节,还精心地为那些孩子制作礼物,这些行为本身实际都是典型的所谓的“哥特式形式意志”的体现,是内在对不公的世界做出的反叛,也是对世俗刻板观念的一种勇敢挑战。
综上,蒂姆·伯顿的动画电影中,充满着哥特文化元素,在形式、主题乃至深层内核上都深深扎根于哥特式艺术形式与精神构成之中。这种哥特式的电影艺术特质,使得伯顿的作品明显超越当下任何特定的抑或主流的动画电影的内外特征,突破传统动画电影的规则范围,在获取巨大成功的同时,也使得刻板化的动画电影创作以一种奇特的面貌再度繁荣,并显示了审美创新、人文思考、精神寄托可以无限衍生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