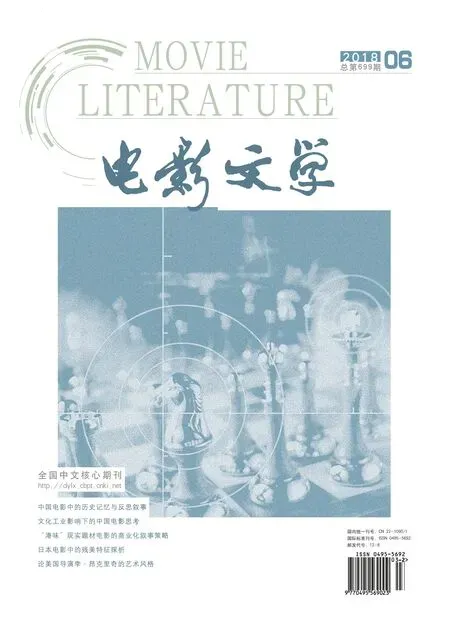观众本体与美国悬疑电影的类型化叙事
钱 璐
(江西警察学院,江西 南昌 330103)
美国电影可以说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且曲折的发展历程,而最终以类型化在商业电影时代在世界电影市场站稳了脚跟,并且几乎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和产业运作通行规律的话事人。这是与美国电影始终将观众的审美期待与观赏快感,置于主流商业电影考虑的第一位的观众本体意识分不开的。
在美国的诸多类型片中,悬疑电影可谓是长期以来一直都保持着较高艺术评价与票房回馈的一类。就悬疑电影而言,美国电影也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类型化机制,包括以观众为本体的类型化叙事。如果说其他国家的电影人对于类型化的制度、技术等层面的模仿是较为简易的话,那么要想因袭美国悬疑片的类型化叙事则殊非易事。而美国的电影人自己也在类型化取得成功后,不断在原有框架下进行调整和创新,甚至有挑战类型化叙事的尝试。
一、观众本体论与电影类型化
美国电影在类型化上的完善,本质上就是一种观众本体论的结果。所谓观众本体,即将观众视为电影制作、发行以及放映各阶段的核心,一切工作围绕着争取观众、满足观众这一消费者来展开,观众本体论认为,观众是实现电影自身“造血”的关键。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电影产业是个系统工程……好莱坞生产的不仅是电影,更重要的是品牌,从宣传、发行、放映到后续产品的开发,这种品牌战略贯穿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始终。”中国电影人敏锐地看到,在美国电影中,观众有着怎样的消费心理是为生产者所关注的,观众作为电影产业的终端,直接决定了电影品牌的培育,观众的审美品位和审美习惯,关系着整个的电影生态环境。这就使得美国电影人在创作之前,就会对影片的定位有着某种具有前瞻性的判断。
在悬疑电影的创作上也是如此。悬疑电影的受众往往来自于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对于悬疑故事,他们已经形成了一定的主流价值观念和审美心态。相对于小说而言,电影的拍摄要集中更多人的智慧和想象力,同时观影也无法像阅读那样进行回溯式、暂停式的思索,这也意味着要放弃更多的个人体验表达,而更多地迎合观众的观赏快感和接受能力。
二、美国悬疑电影类型化叙事
(一)基本悬念的设置
悬念无疑是悬疑电影的核心。在悬疑电影的叙事中,悬念是吸引并保持观众注意力的重中之重。“在上演一出戏给观众看时,首先要抓住观众的注意力,并使他们保持对演出的注意力愈久愈好。只有做到了这基本的一点,才能实现更为崇高和远大的目标……因此要造成一种兴趣和悬念,这是一切戏剧结构的基础。”一部悬疑电影情节的展开,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悬念进行的。例如,在詹姆斯·曼高德的《致命ID》(Identity
,2003)中,最基本的悬念就是“凶手是谁”。十个身份各异、经历不同的人机缘巧合地在一个风雨大作的夜里住进了一家汽车旅馆,随后就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死去。更为诡异的是,他们死亡的顺序都与自己的门牌号有关。从常理推断,凶手无疑应该在还活着的人当中,然而案情却没这么简单,凶手先伪造了自己的死亡,摆脱了他人对自己的怀疑。这一悬念灵感显然来自英国女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无人生还》,而又加入了人格分裂这一理论,对阿加莎原有的叙事进行了开拓。此外,在悬疑电影中,悬念还必须是连续性的,观众在叙事者的引导之下,逐步获得线索,或被逐步带到一个复杂的情境当中,并接受新的疑问的出现以及对旧的疑问的解答。例如,在马丁·斯科塞斯的《禁闭岛》(Shutter
Island
,2010)中,泰迪的查案过程实际上是一次对自我身份的发现过程,只是他这次在医生引导下的自我认识以失败告终了。观众追随泰迪走上孤岛深处时,会不断地发现疑点,如蕾切尔房间的鞋子、反应奇怪的护士等,其中有事物悬念、推论悬念、行为悬念等,而这些悬念都在电影的后部或结尾处得到了解答。观众不断地深入心理情境之中。(二)类型化元素的加入
类型化元素对于类型片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包括公式化的故事情节,如英雄救美;脸谱化的人物,如勇敢的西部牛仔,乃至符号化的影像,如苍凉的西部小镇等。在悬疑电影中,公式化的故事情节即为案件、谜题的发生、勘察和破解,脸谱化的人物则有智慧的侦探型人物,柔弱的受害者,丧心病狂、图谋不轨的作案者等,而符号化的影像则包括与案情有关的密室、荒野或公路,包括一些与宗教、邪教相关的神秘主义内容等。这些都是已经被验证为会触动观众紧张感的叙事元素。例如,在伊恩·索夫特雷的《万能钥匙》(The
Skeleton
Key
,2005)中,卡罗琳在去维奥莱特的大房子工作后很快就发现了种种诡异之处,这里似乎在进行着某种奇怪的宗教仪式。卡罗琳在自己的调查之后认为老太太维奥莱特可能是一个控制了老头本的恶毒妇人,她为了救本而用自己学习到的法术来保护自己。结果最后真相大白,原来维奥莱特和本是男女巫师,分别想通过与年轻的卡罗琳和律师卢克交换身体实现永生,而卡罗琳施展的所谓“法术”实际上正坠入巫师彀中。试图查案的卡罗琳兼任了侦探和受害者的角色,而电影中大量图解式的符号,如阴森的大屋、万能钥匙、宗教仪式等,更是增加了叙事的惊悚与神秘。(三)密闭空间
打造密闭空间也是美国悬疑电影在叙事时给观众制造紧张感的重要手段。例如,在斯坦利·库布里克的《闪灵》(The
Shining
,1980)中,主人公杰克一家三口在冬季大雪封山的时刻住在山顶酒店,面对任何事件都无法获得外界的援助。而这座酒店在1970年曾经发生过上任管理员砍死妻儿并开枪自杀的惨剧,这一故事深刻地影响了杰克的心理,而心态发生变化的杰克又影响了家人,以至于一家陷入越来越可怕的境地。而随着通信技术的发达,单纯的“密室”式密闭空间无疑已经不合时宜。美国悬疑电影又开始寻求制造一种心灵上的密闭空间。如佐米·希尔拉的《孤儿怨》(Orphan
,2009)中,凯特一家之所以会陷入险境,其住处偏僻固然是原因之一,但他们并没有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关键在于曾经的流产让凯特的心灵产生了阴影,夫妇之间也出现了隔阂,亲女是聋哑人,儿子则心中有愧而不敢对父母说实话,一家人无法正常交流,以致出现了一种类似人人被禁闭的互通信息的局限性。三、类型化下的新变
如果说类型化意味着一种稳定、固定的创作倾向,那么观众本体的创作理念则意味着变动、变化。观众的审美心理机制不仅不是一成不变的,且几乎可以说是时刻处于流动状态中的。在类型片塑造着观众的审美时,观众受整体文化环境而改变了的思维也在动摇着电影的套路。这也就使得有着商业需求的类型片基本上都是处于一种寻找某种变与不变的平衡状态中的。
例如,被认为是悬疑电影大师的希区柯克可以说是美国悬疑电影类型化的鼻祖。他的《惊魂记》(Psycho
,1960)称得上是美国悬疑电影的开山之作。希区柯克开创性地运用了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法,对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开掘。如在《惊魂记》中,盗取公款的玛丽安在逃亡途中在一家汽车旅馆的浴室为人杀害,随后她的姐姐、男友等有关人士都接受了警方的调查。而在电影结尾,真相大白时观众才知道,杀死玛丽安的正是看起来正派善良的旅馆老板诺曼。更为可怕的是,在电影中出现的诺曼母亲实际上早已化为干尸,诺曼是一个精神分裂的病人,观众所看到的诺安母亲实际上是诺曼人格分裂的产物,也正是这种人格分裂让他杀死了玛丽安。在《惊魂记》之后,希区柯克所开创的这种叙事模式基本上都被其他导演沿袭着。在事件激发起观众的恐惧、紧张等情绪后,最终一定会指向一个确定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往往就是案情的水落石出。由于案件得到解决往往也就意味着凶手被绳之以法,引发观众恐惧的事件到此告一段落,观众重新回归到具有安全感的心态中,情绪在此得到充分的释放。然而,我们只要对20世纪90年代至新世纪以来的美国悬疑电影进行梳理就不难发现,一直有电影人试图突破希区柯克等前辈创立下的这种有始有终式的类型化叙事。甚至如果我们将目光放得更远,就会发现包括加拿大、英国等西方国家的悬疑电影,如《恐怖游轮》等也纷纷尝试开放性结局或者不完美的结局,这显然与观众的观赏期待发生了变化是分不开的。部分电影人凭借着其天才的对叙事的把控,使电影不仅走向了成功,更是走向了经典。例如,在乔纳森·戴米的《沉默的羔羊》(The
Silence
of
the
Lambs
,1991)中,作为绑架杀人案凶手的野牛比尔被FBI特工克拉丽斯击毙了,但是精神病学家,在电影中同样犯下命案的汉尼拔博士则越狱成功,成为FBI新的敌人,也成为社会治安的隐患。整部电影的叙事主线表面上看是克拉丽斯对野牛比尔一案的侦破,但是事实上则是克拉丽斯对自己心中“尖叫的羔羊”这一心魔的破解。真凶究竟如何被捕等传统悬疑片惯常使用的核心悬念反而被淡化了。《沉默的羔羊》中最终汉尼拔脱逃的结局也为续集的拍摄留下了余地,但续作并非戴米在拍摄伊始就考虑的问题。而部分悬疑电影则是在筹备电影时就有视观众反馈拍摄续集的考量,如克里斯托弗·冈斯根据游戏改编而成的《寂静岭》(Silent
Hill
,2006)中,电影并没有给予观众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跟随罗丝回到家中的小女孩其实不是罗丝的女儿莎伦,而是阿莱莎。而阿莱莎是拥有穿越于三个世界的特殊能力的。因此,尽管罗丝自以为自己回到了家,但是她和丈夫实际上处于两个平行世界中,无法看到彼此。阿莱莎用这样的方式实现自己独占罗丝母爱的目的。当叙事进行到这里时,整个寂静岭的冒险故事既告一段落,又有了往下延续的可能。还有一部分不甘于被类型化束缚、才华横溢的导演,甚至会对悬疑电影的叙事做出革命性的颠覆。这其中最经典的便是克里斯托弗·诺兰的《记忆碎片》(Memento
,2000),相比起其他悬疑电影使用顺序的方式对真相抽丝剥茧,《记忆碎片》则从头到尾使用了倒叙的方式,使整部电影的叙事显得支离破碎,观众完全进入到主人公莱纳德记忆丧失的痛苦之中,从而理解莱纳德为何不得不不断确定自己的身份,并用自欺的方式来给自己寻找活下去的勇气。同样,《记忆碎片》的结局也是开放式的,尽管诺兰在最后似乎对谜底进行了揭示,但是电影依然有另一种演绎的可能性。这也就使得电影能够为观众长久地记住、讨论。类型化是当前主流的电影工业模式形态,美国最早在电影的类型化方面进行了实践与探索。在悬疑电影这方面,美国电影在高度重视观众的观影趣味、观影心理的情况下,以观众为本体建立起了悬疑电影的类型化叙事,保证了美国悬疑电影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较为成功的商业化运作。而另一方面,电影人也会对悬疑电影的类型化叙事进行适度的创新或翻新,电影的商业性、艺术性、受众的大众性以及导演的艺术个性等,也在此得到碰撞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