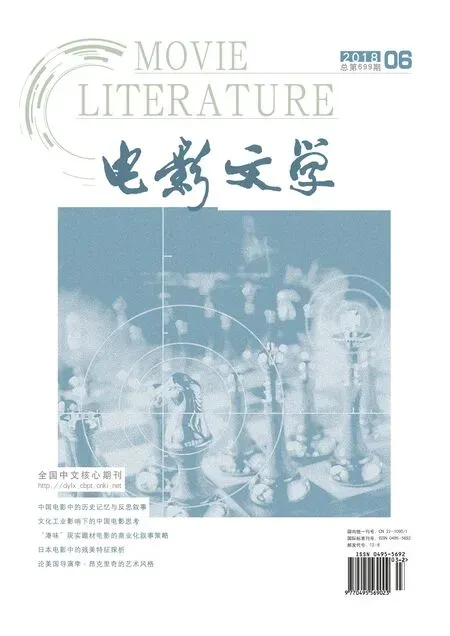美国恐怖电影的社会心理分析
常玉洁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河南 新郑 450000)
电影是城市化进程以及商品经济发展下的产物,也是一门需要迎合大多数人的、与社会心理紧密相关的艺术。这一点在好莱坞的类型片中体现得尤为突出。恐怖电影是好莱坞类型片中的一种,它往往能折射出美国社会某种大众心理。
恐惧是一种人类中普遍存在的心理。“当恐惧降临时,人类的理性便会缴械投降……睿智如哲学家,在恐怖面前也会完全丧失理智——棍棒即将落下之时,哲学家也会闭上他智慧的双眼;紧邻悬崖边上,他也会像孩童般颤抖。于细微处,自然昭示着她无上的权威,提醒着人类必死的命运和固有的弱点。在她面前,我们的理性和斯多葛派的美德也会黯然失色。”在被上升到艺术的高度后,恐惧还能使人们获得审美快感。但是,人们具体恐惧的对象以及面对恐惧时的表现又是有所区别的。电影人有必要在制造恐惧感时,寻求到人们在心理基础上的共性。
一、宗教信仰心理基础
以《圣经》为基础的基督教可以说在美国的文化传统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对基督教的普遍信仰以及对教义的不同理解,也就催生了和宗教文化相关的恐怖电影。例如,奥斯卡历史上唯一得奖的恐怖电影,被认为是美国恐怖电影鼻祖的《驱魔人》(The
Exorcist
,1973)就是根据1949年发生在美国马里兰州的一起真实的驱魔事件改编而成的。建立在宗教信仰心理基础上的恐怖电影,往往有着较为深刻的人文内涵。如在《驱魔人》中,狡黠的恶魔附身于小女孩芮根身上,并且还会欺骗神父,模仿卡拉斯神父的亡母来干扰神父的施法。最终卡拉斯神父为救芮根而死,他所代表的正是基督教徒勇于面对恶魔,并敢于牺牲的教义。而宗教中的相关文化元素,在恐怖电影中可以直接帮助其制造血腥、肮脏的视觉效果,或压抑、紧张的环境氛围。如在《驱魔人》中,芮根被附体后头可以向后做180°的旋转,倒转躯干如蜘蛛一般爬下楼梯的画面等,都令当时的观众极为害怕,有着神秘主义的恐怖感。基督教信仰在为美国恐怖电影提供艺术灵感的同时,也划出了一条无形的界限。由于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基督教保持信仰或起码的敬畏,因此电影人即使不再直接如《驱魔人》那样肯定宗教,也往往并不会否定宗教。基督教所批判的异端,如常常打着基督教旗号出现的,被认为害人不浅的撒旦或邪教信仰,乃至一些毫无人性的巫法等,就成为恐怖电影营造恐怖的来源。
以《寂静岭》(Silent
Hill
,2006)为例,电影改编自有推理解谜意味的日本同名游戏,并且基本保留了游戏中的情节设定,但是其中的心理基础实际上是西方的宗教信仰心理。女主人公罗丝的女儿萨伦患有梦游症。在电影一开始,罗丝和丈夫寻找失踪的萨伦时,背景就出现了一个亮灯的十字架,暗示了电影与基督教有关。后来罗丝带萨伦前去寂静岭求医时,汽车经过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岂不知我们要审判天使吗?岂不知教徒要审判世界吗?”这是改编自《圣经·哥林多前书》中的话,删除掉了“若世界为你们所审,难道你们不配审判这最小的事吗”和“何况今生的事吗”这两句。这无疑是在暗示整部电影中阿莱莎的悲剧。她只是一个无辜的小女孩,然而却因为寂静岭小镇上的人们相信了邪教,对她进行了审判与火刑,让她一直生活在巨大的痛苦中,因此才会迸发出强大的怨念,吸引来罗丝母女,让罗丝目睹她的复仇。又如在罗丝进入寂静岭中阿莱莎曾经读书的学校时,看到门框上写着《圣经》中的文字:“恶必害死恶人;恨恶义人的,必被定罪。”在电影中,人们对阿莱莎实施的集体迫害就是建立在邪教信仰基础上的,小镇上的人们自以为是上帝的虔诚信徒,其实他们信奉的只是邪教。克蕾丝主教用邪教统治着所有人,将无辜的阿莱莎指为“女巫”。当阿莱莎被烧成焦炭以后,每天释放自己的恐惧、痛苦和仇恨的时候,小镇上的教堂也是这些镇民唯一能避难的地方,这种信仰让镇民觉得自己手握正义,却干着无比邪恶的事情。他们想为阿莱莎“定罪”,而最后他们却被阿莱莎“定罪”并残忍处死了。与之类似的还有如充斥着魔鬼崇拜的《罗斯玛丽的婴儿》(1968),以神秘的巫毒术与年轻人交换躯体,从而实现“永生”为叙事核心的《万能钥匙》(2005)等。
二、异域窥视心理基础
弗洛伊德认为,窥视欲是人类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而电影就市场表现来看,又有着一种非常鲜明的猎奇导向,一种异域的,迥然有别于现实的空间,对于观众来说,是极具魅力的吸引元素。
吸血鬼是美国最早的恐怖电影的重要题材之一,而这一题材实际上就来源于古希伯来文化和古罗马文化。而屡屡出现在银幕上,已经具有母题意义的“德古拉伯爵”,其实就来源于19世纪爱尔兰作家布拉姆·斯托克的《德古拉》小说。这一类电影中,古代或近代欧洲就成为一个被窥视的异域。如《惊情四百年》(Dracula
,1992)中,德古拉之所以变成一个不死的吸血僵尸,正是因为在公元15世纪时土耳其人入侵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被传身死,妻子伊丽莎白投河自尽。又如《夜访吸血鬼》(Interview
with
the
Vampire
:The
Vampire
Chronicles
,1994)中,18世纪的巴黎也是主人公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与现实生活不同的环境以一种被窥探的意象出现,强化着人们的恐怖需求。而这种异域往往与禁忌、神秘、诡异、死亡等有关。值得一提的是,科幻背景的恐怖电影实际上也满足的是观众这种窥视异域的心理,对科技发展有可能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的担忧,本身就是一种社会心理,而科幻题材又给观众提供了一种奇观性的异域空间体验。如《生化危机》(Resident
Evil
,2002)中,生化武器泄露,人们遭到丧尸的攻击;《异形》(Alien
,1979)中人类的敌人变成了太空之中一种长相奇特、恶心不堪,能抓住人并寄生其中的怪物等。正是因为人类进入了一个有别于现实的、科技高度发达的空间(或处于未来的时间),他们才得到了这种惊悚的、冒险的体验,而丧尸也好,异形也好,包括弗兰肯斯坦的实验怪物也好,种种意象都寄托着人类对自我之外的,还没能被彻底理解、掌握之物的恐惧。与之类似的还有如《新丧尸出笼》(2008)、《活死人黎明》(2004)等。三、社会现实心理基础
社会现实中的时代思潮、社会事件等,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进而催生着恐怖电影。社会现实与恐怖电影之间的关系是正相关与负相关并存的。
所谓的负相关,体现在电影中是对社会心理的一种对抗。如前述的《驱魔人》,其诞生很大程度上是与20世纪70年代美国社会变更期时的混乱思潮有关的。70年代对于美国而言,意味着越战、婴儿潮、平权运动等轰轰烈烈的事件。其时美国逾70%的人口笃信基督教,主流社会在教义影响下,民风保守,而正是在这种保守的土壤中孕育出了嬉皮士、摇滚乐乃至药物滥用等冲击传统观念,甚至被年轻人视为“英雄”行径的生活方式,动摇着社会心理基础。这无疑是让主流社会感到恐惧的。于是在《驱魔人》中,教会和无处不在的魔鬼这一对不共戴天的仇敌开始了在人身上的相互博弈,如女孩芮根被附体以后,当着别人用十字架来扎自己的下体等行为;又如芮根没有父亲,母亲是一名在外面忙碌事业的、个性强势的“女强人”等,就是一种对当时社会心理的讽喻,电影暗示着,提倡性解放、女权主义等在当时看来离经叛道的开放思潮只会让社会鸡犬不宁,甚至带来世界末日。同样,在电影中,现代医学,包括精神病学、现代心理学等与理性相关的学科显得毫无用处。牧师还说:“医生告诫我不要喝酒,但是谢谢上帝,我意志不坚。”电影将人类得救归于保守不变的信仰而非处于发展变动中的科学。
而所谓正相关,即当社会中出现骇人听闻、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大多为刑事案件),而人们对此束手无策时,电影以此为题材,为观众讲述一个全新的故事,甚至在电影中给原本扑朔迷离的事件提供一个较为合情合理的结局或答案。在这样的情况下,事件本身是得到电影人的正视,乃至作为一个有热点的素材被利用的。社会上人们对于事件的恐惧心理也在这样的处理中得到了宣泄。
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便是《十二宫》(Zodiac
,2007),电影取材于著名的“黄道十二宫”悬案。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一个自称“十二宫”的连环杀手不断作案,并且会在杀人后给媒体寄去一封密码信,跟警方玩起了猜谜游戏,有时还会寄去血衣等证物,甚至通知警方自己的下一次作案。尽管这桩悬案已经过去了数十年,但是由于真凶始终没有确定而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为了体现出真实感,案发时七岁,亲历了当时社会恐慌氛围的导演大卫·芬奇有意将推理部分拍摄得冗长枯燥,略显沉闷无趣,最终也没有指出一个明确的凶手。但正是在平缓松弛的节奏中,恐惧感被逐渐带了出来。在和凶手的角逐中,警方永远慢人一步,并且随着连环凶杀案件的不断上演,警方的意志越来越趋向崩溃。警方不仅无法抓到十二宫,甚至不能确定十二宫是不是一个人。十二宫犹如一个疯子在黑暗中等待,而整个世界则被恐惧所折磨。如果说《十二宫》侧重于表现当时的社会气氛以引发观众的焦虑,那么《黑色大丽花》(The
Black
Dahlia
,2006)则更为直观地表现了恐怖对象,即暴力对个体生存的直接威胁。同样是取材于20世纪40年代发生于好莱坞真实案件的《黑色大丽花》由于有詹姆斯·埃罗伊的畅销小说作为底本,不仅能够给出悬案的“真凶”:玛德琳的已经精神不正常的母亲(这也是人们多年来的猜测中最具市场的一种),同时还有一个帮凶,即玛德琳的生父。伊丽莎白·肖特(黑色大丽花)之死最为人们感到恐怖的就是其嘴角被割开至耳朵,裂开的嘴角使大丽花死后犹如一个小丑,电影中也解释了玛德琳之母这样做的缘由,因为玛德琳和肖特长相酷似,玛德琳的母亲憎恨女儿对自己不忠而认为她是一个小丑,故而这样残损肖特的脸。观众在最终的恍然大悟中得到了战胜恐惧的快感。电影还能以类似希区柯克的手法来组织情节,充分地掌握观众情绪上的张弛。从20世纪初,吸血鬼德拉库拉被搬上大银幕之后,美国恐怖电影就一直受到人们的追捧。美国恐怖电影之中体现出来的技术,以及电影的具体表现类型和形式都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有所变动。而在社会心理层面,美国恐怖电影主要从宗教、异域以及社会现实事件这些影响广泛,困扰大多数人的对象中挖掘素材,也正是因为始终把握住观众普遍性的心理基础,美国恐怖电影才能一直散发着独特魅力。但社会心理同样是有一定范围的,当电影在另一种社会背景下放映时,观众的心理预期、文化积淀就有可能全然不同,能让美国或西方观众惊出一身冷汗的情节,对于东方观众而言很有可能便不知所云,毫无反应。这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更加体现了社会心理这一“本”对于恐怖电影这一“木”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