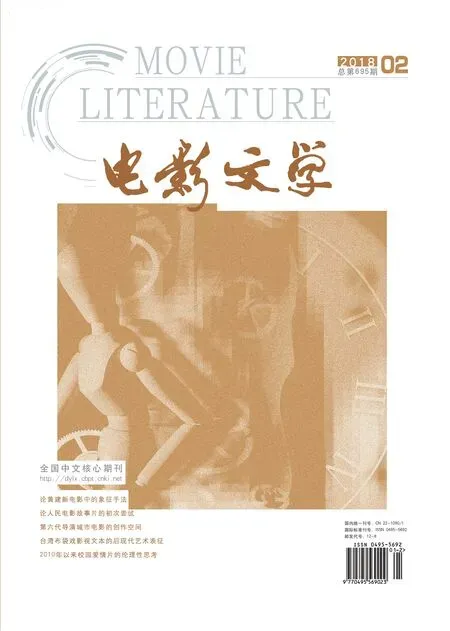存在主义视域下的《梦之安魂曲》
魏春燕
(许昌学院,河南 许昌 461000)
《梦之安魂曲》(Requiem
for
a
Dream
,2000)被认为是达伦·阿伦诺夫斯基最为经典的电影之一。电影自上映之后,就不断被人们从各个角度进行阐释。《梦之安魂曲》本身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电影表达的侧重点在于吸毒者的堕落生活以及吸毒后恐怖的精神状态。阿伦诺夫斯基用其令人叹为观止的镜头设置和剪辑能力让没有吸毒史的观众看到了吸毒者不堪的生存体验,以及他们后悔而又无法自拔的感悟。在《梦之安魂曲》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世界存在的荒诞以及人类存在的悲哀和虚无,而这正是存在主义所揭示的。应该说,存在主义也是我们分析《梦之安魂曲》的一个合理视角。一、痛苦人生
存在主义兴起于20世纪,在海德格尔、雅思贝尔斯、萨特、梅洛-庞蒂等人对存在主义思想的丰富下,存在主义风行欧洲,并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大影响。尽管存在主义被认为是特殊的历史阶段下的产物,即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人类开始感受到了被“异化”的危险,曾经的理性主义受到了质疑。在存在主义中,人成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物,人“存在”时的体验成为存在主义作为哲学的出发点。这种看似非理性的、主观的思考方式实际上是为了争取人性的自由,呼唤人类获得自我解放。到了20世纪60年代之后,存在主义渐渐式微,但至今仍未退出历史的舞台。存在主义的肥沃土壤继续开放着艺术之花,具有荒诞派意味的戏剧和电影就是其中的范例。
存在主义指出人处于一种危机中,人生痛苦、无聊且虚无,人被置于这个世界中,软弱无力,无论穷人或富人都要忍受这样的痛苦。以片中的萨拉为例,她被孤独所笼罩,身边没有丈夫、儿子的陪伴,和其他老太太也相处得不好。萨拉将全部精力投在了电视节目上,当她被电话通知可以上电视时,她就开始为了能穿进自己漂亮的红裙子而疯狂地减肥。这种对于上电视的痴迷,使得她丧失了精神和人身上的自控,成为一个被电视节目操纵的提线木偶,最终滥用药物,无家可归。而萨拉之所以将上电视作为自己的全部人生追求,固然有她虚荣心作祟的原因,也与她希望自己能因为上电视而成为儿子哈利的骄傲,让吸毒的哈利回到自己身边有关。
电影的最后,阿伦诺夫斯基用了一段让人眼花缭乱的高速快切交代了四位主人公痛苦不堪而又互有对应的结局:哈利的朋友泰隆被投入监狱,在狱警的羞辱之下不断干着体力活,累得呕吐不止;而玛丽安则在淫乱的夜场中彻底沦为娼妓,在嫖客的命令下麻木地听从摆弄;哈利被固定在病床上截肢,左臂在骨锯下飞溅出来的鲜血洒满了他戴着氧气面罩的半边脸;萨拉则在医院里忍受着一次又一次的电击疗法,最终头发被剃,记忆丧失,当她的朋友来探望她时,她表情呆滞,面目全非。四个人不仅都失去了身体上的自由,也失去了作为人的基本尊严。观众可以在飞速切换的画面中感受到四个人难以言表的痛苦。而在这段激烈的快切后,叙事进入平缓期。三位年轻的主人公躺在医院、家里的沙发和监狱的小床上,几乎都以一种蜷曲的、类似婴儿在母体里的侧身屈膝的方式睡去。这一方面表示了主人公在高度疲倦、哀痛之下混沌、迷茫,希望逃避现实世界的精神状态,另一方面也暗示了他们都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幼年的泰隆曾经对母亲说自己以后一定能成大事,而宠爱他的母亲则表示:“你不用成大事,你只需要陪在妈妈身边。”而成年后的泰隆却只能泪流满面地望着母亲的照片,自己童年时的豪言壮语早已破灭。玛丽安的母亲早已在玛丽安卖身之前就和她断绝了关系,在玛丽安成为娼妓后,母女关系显然更加没有了转圜的可能;而萨拉和哈利之间的母子亲情是贯穿整部电影的,在电影的最后,他们也是相爱的,可惜的是母子两人都被困在了医院之中,一个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左臂,一个则已经变成了六亲不认的疯子。
电影终止于萨拉的幻觉,萨拉似乎看到自己穿着红裙子上了电视节目赢得万众欢呼,主持人介绍她引以为傲的儿子哈利,哈利走上台来和她拥抱。这一已经永远不可能发生的画面与现实形成鲜明的对比,更让观众感到结局的残忍,另外,《梦之安魂曲》的叙事开始于电视,也终止于电视,这种首尾呼应令人嗟叹。
二、荒诞社会
在存在主义看来,世界是高度荒诞的,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无法避免感到虚无、恐惧和被遗弃感。由于存在主义认为人的价值是高于一切的,人与社会处于一种对立的位置,社会对于人的“自我”有一种威胁。当萨特等人不断在这方面进行探索时,他们的动机与目标就是质疑和否定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价值体系。
在《梦之安魂曲》中,整个社会存在种种乱象,人们普遍精神空虚,黑帮横行,贩毒者层出不穷,而在部分衣冠楚楚之辈的身上,也可以窥见社会的病症。
电影的四位接触毒品的主人公里,母亲萨拉是最为无辜的。她因为服用减肥药而染上毒瘾,与当时混乱、非理性的社会秩序有重要的关系。当时的美国社会本身就有着滥用药物的氛围,部分毒品最早就被用于疾病的治疗。而在《梦之安魂曲》中,为萨拉开药的医生显然是一个毫无责任心的人。阿伦诺夫斯基有意将摄影机置于萨拉身边,而身穿白大褂的医生则距离她很远,似乎从头到尾就没有认真地观察和倾听过萨拉。萨拉后期已经出现了明显的精神不正常的现象,高度亢奋,对自己症状的叙述也有些语无伦次,然而医生对此却毫无反应,他的动作便是打断萨拉的陈述,低头开药。对于医生来说,他完全不关心萨拉出现了什么问题,也不关心萨拉想要的是什么,而只是机械地完成自己的工作,使萨拉进入到越服药越成瘾,越成瘾就越依赖药物,最终甚至混合服药的恶性循环中。这种态度与其说是医生黔驴技穷,倒不如说是他代表了社会中的一类唯利是图的骗子。
与之类似的还有如玛丽安的心理医生。他觊觎玛丽安的美色,同时也因为职业之便而知道了玛丽安沉迷毒品难以戒断的弱点。玛丽安的父母请他来为玛丽安进行疏导,而他却乘虚而入。在富家小姐玛丽安失去了父母那边的经济来源,而哈利又急需用钱时,让玛丽安用自己的肉体来换钱,玛丽安不得不为了两千块完成了这项耻辱的交易。而这一次也开启了玛丽安后来更为堕落的卖身生涯。在玛丽安出卖肉体后,她强忍恶心,直到走出酒店大堂才终于忍不住呕吐。可见她极度厌憎自己这种行为,并且即使是在已经堕落的情况下,她的教养依然在控制着她的行为,即不要在干净亮堂的酒店,不要在封闭的、有他人的电梯里呕吐。玛丽安并不是一个彻底失去了道德感的人。无论是萨拉的医生抑或是玛丽安的心理医生,他们原本都应该为自己的病人提供有效的帮助,然而他们却印证了存在主义所认为的,世界带给人的只有无穷无尽的苦闷和失望。这一类人尽管没有与主人公之间发生尖锐的抗争和冲突,但是他们依然以一种残酷的方式对待居于弱势的两位痛苦的女性。这样的人的大量存在,共同造就了这个荒谬而冷酷的世界和无数个痛苦的人。而从他人的角度来看,贩毒的哈利也是一个制造他人痛苦的人。
三、个体责任
如前所述,存在主义对于社会有着严峻的抨击态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主义将人的焦虑、担忧、堕落,将人无法获得“绝对自由”全部归咎于社会。反之,萨特就曾经在其戏剧《禁闭》以及其他著作中提出,人拥有着本质上的自由,可以进行“自由选择”,个体的行动都出自自由选择。这样一来,人就应该对自己的人生负完全责任,如上帝、社会等外在因素都不应该成为人推卸责任的对象。人生的意义就通过人的行动来体现。萨特的这一观点深刻地影响了后现代主义文学。尽管萨特的观点并不绝对正确,存在先于本质意味着人的行动没有参照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在任何环境下都可以“自由选择”。但是,萨特对于人生责任感的理解用于对《梦之安魂曲》中人物命运的考量却是适当的。正如人们所公认的,电影中的四个主人公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是他们都无可避免地被自己的弱点击倒了。而他们在毒品面前没有把握住自己,也与他们对自己的不负责有关。这也是《梦之安魂曲》的可贵之处,即对于主人公,电影在同情的同时,也有着旗帜鲜明的批判。
尽管存在主义不断指出人生的种种虚无之处,强调人与客观事物之间的对立,但并不否定道德和人的自我努力,存在主义中也有人道主义的精神存在。加缪曾经通过《鼠疫》等作品提出,人可以充实自己的内心,以人道主义精神来对自己进行支撑,寻求人和人之间的爱情、友情等,达伦诺夫斯基在电影中也确实暗示了这一点。如萨拉虽然一直孤身一人,在那一群晒太阳的老太太中似乎格格不入,但是在她被电疗后,还是有朋友前来探望她,拥抱她,曾经被萨拉以“她们不一样”否认她们是自己朋友的老太太把萨拉接走,成为电影结尾唯一的温情画面,可见阿伦诺夫斯基并不否认世间依然有真情。而主人公对于友情和爱情的把握就并不理想了。在《梦之安魂曲》中,泰隆和哈利之间有着深厚的友谊,哈利和玛丽安之间的爱情也是真挚的。当泰隆被警察抓走时,哈利毫不犹豫地拿出他们赚的所有钱来将泰隆保释出来,以至于他们提心吊胆做的毒品生意走进了死胡同。而当哈利的手臂被感染,生命垂危时,泰隆明知道如果找医生自己毫无疑问地要被送进监狱,他还是为了保住哈利的性命而将哈利送去了医院,自己锒铛入狱。而哈利在自己生命垂危时,依然对玛丽安念念不忘。
但是无论是友情抑或爱情,都没有将他们引向一种更为积极的人生。在电影一开始时,三位年轻人就已经染上了毒瘾,哈利甚至为了得到毒资而不断向自己的母亲萨拉要钱,在要钱未果后就去抵押萨拉须臾不可离开的电视机。随后泰隆和哈利开始了亡命街头的毒品生意以贩养吸,而哈利则为了抢购毒品而逼迫玛丽安去向心理医生借钱,尽管他非常清楚这所谓的“借钱”需要玛丽安付出怎样的代价。换言之,有了毒品这一前提,无论是友情抑或爱情,都无法照亮他们生命的前路。三个人如果一开始就在吸毒和不吸毒之间选择了后者,那么后面的一系列挣扎与斗争就有可能不会发生。而在经济上山穷水尽之后,哈利也没有选择戒毒,没能洗心革面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而是让自己的爱人玛丽安去出卖肉体,让自己继续深陷在毒品的泥潭中,也将玛丽安推向了一个更黑暗的深渊。这不仅是对自己的纵容,也是对爱情的不负责任。一言以蔽之,正如萨特所指出的:“是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是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主人公对于人生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实现是失败的。
在《梦之安魂曲》中,几乎处处都有存在主义的影子。人物处于一种痛苦、荒诞的人生之中,他人成为他们的“地狱”,而他们也在为其他人制造痛苦。社会对于他们灵魂的污浊、行为的堕落有着密切的影响,而他们也对自己最后失去了自由的结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阿伦诺夫斯基在用精湛的镜头语言为观众展现吸毒者人生的消极一面时,也对于他们何以一步步走向悲剧结局进行了存在主义的积极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