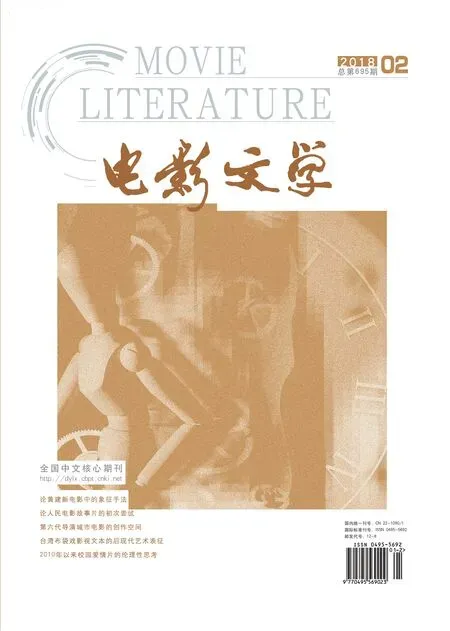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神奇动物在哪里》与历史的艺术重构
邵 帅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外语教学部,北京 100048)
由大卫·耶茨和J.K.罗琳合作完成的电影《神奇动物在哪里》(Fantastic
Beasts
and
Where
to
Find
Them
,2016)延续了罗琳在《哈利·波特》(Harry
Potter
)系列中的魔法世界设定,同时在创作上也延续了《哈利·波特》中向已经远去的历史寻求资源的故事言说习惯,这也是电影增加自我深度,摆脱“粉丝电影”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一、历史叙事
作为一名被认为可以与《魔戒》作者托尔金相提并论的魔幻小说作家,J.K.罗琳也有志于创建一个完善、庞杂、历史悠久的魔法世界,并使魔法世界成为一面反映现实世界的镜子。与托尔金在中土世界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隐晦的记录和臧否一样,在《哈利·波特》以及《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小说中,事件与人物也并不是凭空建立的,它们来自于历史或现实中的已然存在。因此,罗琳的小说被认为有着关注历史,甚至是对历史进行唤醒与复活的特征。罗琳本人并不直接攫取具体的历史事件,但是观众可以在电影中感受到她所精心设计的指向了历史客观存在的细节,以及罗琳本人对历史事件的回忆和总结。如在电影中,蒂娜一行人要打听神奇动物的下落,就不得不跑到地下酒吧“盲猪”去找妖精黑帮成员哥纳拉克,而这个妖精开办的地下酒吧隐喻的便是20世纪20年代猖獗的纽约黑手党,他们在禁酒令的限制下依然从事着违法兜售酒精的活动以牟取暴利;又如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得以向欧洲回收借款,大量美国人向国家贷款寻求创业,一心想成为面包师的雅各布正是因为去向银行贷款开糕点店,才被卷入纽特的故事中来等。
值得一提的是,文学和电影的创作是不同于历史的。在历史撰述中,一系列事件的前后相继顺序以及其中的因果关系是最为重要的,如体制变迁、社会发展等,而人在历史撰写中仅仅是社会或经济力量。在艺术创作中,人的地位则被凸显出来,主创们深入人的内心深处,去探寻人物隐秘的精神世界以及真实的感觉,甚至可以说,人物的心理真实相对于外部真实而言有着更为优先的位置,人不但是历史事件的参与者,更是整个时代的推动者与写照。只有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创作,观众才能为电影的叙事所吸引,进入片中人物的视角之中。这在《神奇动物在哪里》中也不例外。
在电影中,最为关键的历史叙事便是1962年发生在马萨诸塞州的“塞勒姆审巫案”。在这次宗教迫害中,二十余人被迫害。罗琳将这个故事编织进电影的背景中,并将其与北美的殖民历史联系起来:美国巫师界因为塞勒姆审巫案的冲击制定了最为严苛的种群隔离法案,巫师被禁止与麻鸡交往。而殖民背景又使得美国种群混杂,大量欧洲来的黑巫师隐匿于此,部分黑巫师组织了一个叫“擦洗者”的组织,通过出卖巫师,甚至抓捕无辜的麻鸡献给教会来获取利益。擦洗者最终融入麻鸡社会中,成为美国巫师社会的隐患。在这个背景设定中,罗琳塑造了玛丽·路·贝尔伯恩这一人物。她是“擦洗者”的后裔,是对巫师社会充满了愤恨,并几乎颠覆了国际巫师界的黑巫师巴塞罗姆·贝尔伯恩的后人,也是“新塞勒姆慈善会”的女组织者。从表面上看,贝尔伯恩收养孤儿,并按时给贫苦的孩子们分发食物,一切似乎符合一个慈善会的标准。然而实际上,贝尔伯恩的内心充满了对巫师世界的仇恨,她一心要把所有的巫师赶尽杀绝,将贝尔伯恩这一姓氏所承载的血雨腥风继续通过这些无辜的孩子散播出去。电影用这个人物直指三大历史问题:一是宗教迫害问题,二是殖民历史带来的种族歧视和种族隔离问题,三是恐怖主义问题,并以展现历史中人和人的冲突抵牾,来让人们看到历史遗留下来的当前社会的种种失衡。
二、现实旨归
如果说我们可以从《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窥见一种有着“过去时”意味的重温式叙事,我们更应该看到一种“进行时”的现实思考。克罗齐曾经指出:“只有对现在生活的兴趣才能促使人们去研究过去的事实。故而,过去的事情一旦和对现在生活的兴趣相结合,它的关注点就不再是过去,而是现在了。”这一点尤其适用于艺术创作。当人们在艺术作品中看到历史叙事时,理应意识到主创的动机绝不只是为了对历史进行再现,而是让历史针对某种现实状况说话,甚至是解决某一具体的现实危机,这是一种对历史的有目的的重构。对于《神奇动物在哪里》亦然。早在创作《哈利·波特》系列时,罗琳就已经感受过现实的重重困境。在2000年之前,部分基督教社区出于宗教信仰而抵制罗琳创作的魔法世界。人和人之间的仇恨、偏见以及隔阂问题是罗琳所关注的,它们往往是历史留给现实的伤痛。在《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罗琳也探讨了这一问题。
由于慈善会对未成年人而言有着强大的力量,因此被收养的孩子们是无法抵御贝尔伯恩的洗脑和折磨的,他们只能在自己无法形成分辨能力的时候,在无数次聆听教诲和接受惩罚中接受贝尔伯恩的仇恨心理。电影中的克雷登斯正是因为年纪渐长而越来越遭到贝尔伯恩的嫉恨和控制。被以善良包装的邪恶一旦“体制化”,那么将对社会造成极大的危害。在现实生活中,罗琳在完成《哈利·波特》的写作后长期苦心经营一个名为“荧光闪烁”(Lumos,在小说中是一个与光明有关的咒语)的慈善机构。罗琳之所以要建立“荧光闪烁”,正是因为她注意到在全球范围内有大量的孤儿院在腐败体制的庇佑之下对孤儿进行迫害。显然,儿童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必然会被扭曲。于是在《神奇动物在哪里》中,克雷登斯作为“慈善家”母亲贝尔伯恩的养子,多次遭到贝尔伯恩的迫害,最终因为压抑自己的魔法力量而成为一个默然者。而无数个克雷登斯这样的孤儿在受到了孤儿院的虐待之后,依然要感谢孤儿院对他们的抚养,甚至因孤儿院强加给他们的仇恨而走投无路。
克雷登斯这一悲剧人物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中联结历史和现实的关键人物。电影一方面通过他来揭露出现实中体制化后的罪恶孤儿院/慈善机构的嘴脸,另一方面又重新敦促人们思索历史问题,因为克雷登斯背负的是历史仇恨,巫师与麻鸡之间的对错是非是复杂的,隔阂是深重的,而这些长期的、灭顶的仇恨无论如何是不应该由一位孱弱、无辜的少年来承担的。双重的悲哀同时体现在克雷登斯一个人的身上,这也是《神奇动物在哪里》中悲悯色彩的最大体现。
三、女性与历史批判力量
在探讨《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的历史艺术重构问题时,我们不能仅仅针对文本本身对历史和现实的指涉,而忽略了解构者和批判者,即罗琳本人。所谓的历史重构,并不仅在于一种“以史为鉴”的方法论,还在于一种在重新认识历史、重新建立叙事话语时的自我体认,即“是谁在以史为鉴”。而罗琳显然在其中彰显了女性的力量。
一方面,在男权社会中,男性不断按照自己的利益和需求来改写历史,并将这种历史强加于人,而女权亦日益觉醒,参与到对历史的认知和重构中来,罗琳本身的写作就是这种行为的体现,《哈利·波特》和《神奇动物在哪里》系列电影都是罗琳以魔幻题材对历史进行评价与架构的载体。另一方面,罗琳也在自己的作品中提出,女性完全有能力,也有权利在生活中发挥自己的积极作用,使自己成为消解男性中心话语以及性别主义的一支重要力量。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在《哈利·波特》中,承担了拯救世界或改变世界的主人公还是男性,即哈利·波特,而他的行为离不开女性的推动与帮助,如赫敏和金妮等。而到了《神奇动物在哪里》中,纽特的光芒则为蒂娜等女性掩盖,初到美国人生地不熟的纽特成为女性的拯救和帮助对象,女性们更是男性的帮助者和指导者。
在《神奇动物在哪里》中,蒂娜一开始表现给观众的是古板的一面,但是她的个性和历史作用很快展露出来。蒂娜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且有着高度的敏感性,即使在被上司开除出傲罗队伍后,她还是主动继续盯梢蠢蠢欲动的“第二塞姆勒”,并不顾自己已经失去傲罗身份而在街上逮捕闯下祸端的纽特。她强烈的,甚至让观众不满的责任感正是源于她对正义的坚守。从国会会长瑟拉菲娜女士抱怨蒂娜为什么又闯进国会,以及四人晚餐时奎妮对姐姐事业的骄傲来看,蒂娜这种一意孤行的行为绝非孤例。而单纯有职业操守和正义感并不足以体现蒂娜这一角色的历史批判力量。蒂娜之所以会失去自己引以为荣的傲罗职业,正是因为她违背了巫师界法律当众攻击了虐待克雷登斯的贝尔伯恩。这是因为蒂娜对于“爱”和同情有着同样的执着心理,这种正面的情感在她心里有着强烈的压倒性力量。这也正是为什么蒂娜在被处以死刑时,她在冥想池中看到了大量关于克雷登斯的画面,因为她重视这个陌生男孩的生命。与之类似,纽特也同样在救克雷登斯的过程中不惜丢下自己视若性命的,藏有大量神奇动物和他的研究手稿的箱子。因为对于纽特和蒂娜来说,挽救一个活生生的人要比自己的事业更重要,这也是两人最后能够相爱的原因之一。
在当时的语境下,克雷登斯这样的默然者是一个需要避而远之的怪人,或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武器。然而作为女性的蒂娜却表现出了坚忍、博爱,她能够对一个和自己没有亲密交集的生命个体给予平等和爱护。电影用这样一个角色来同时展现了两个历史批判力量,一是对性别歧视的批判,二则是对一种物化生命、否定平等的理念的批判。这种思想正好是与电影中的大反派格林德沃可以利用一切、牺牲一切的世界观截然相反的。与之类似的还有同样极具魅力的女性角色奎妮。在电影中,由于20世纪20年代女性所受到的诸般限制,拥有高超魔法天赋的奎妮无法出去工作,但她依然想尽办法展现自己的才华,并且抛开偏见与麻鸡面包师雅各布相爱。奎妮的个性、外观等与蒂娜并不相同,但是在电影用以表达对女性力量的张扬、反对歧视和隔离这一方面,却是和蒂娜一样的。
在消费时代,主流话语的招揽是诱人的,这从好莱坞漫威、DC等一而再再而三推出的超级英雄电影不断成为票房宠儿就不难看出。而罗琳以及与她合作的耶茨等导演依然没有放弃以电影来推动社会进步,改变历史和人们思维的宏大梦想。
可以说,《神奇动物在哪里》无疑是一部成功的商业电影,它的票房成功很大程度上也与《哈利·波特》系列持续多年的火热分不开。但这并不意味着《神奇动物在哪里》只是一部商业意味浓厚的跟风之作。反之,罗琳不仅在艺术上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文本的水准,同时也在思想上沿袭了之前《哈利·波特》七部曲的核心主题,并对历史进行了艺术重构。这种对历史的重构并不意味着对史实的扭曲,而是指在一个看似架空的世界中,以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矛盾作为电影的戏剧冲突,从而敦促人们反思历史或现实中的类似事件,并对其中的是非曲直进行追问。这样一来,在看似娱乐性十足、轻松的奇幻和冒险的类型片外衣下,罗琳的种种关于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沉重思考便可以随着魔法世界的家喻户晓而得到更好的传播。
——吐槽之神快来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