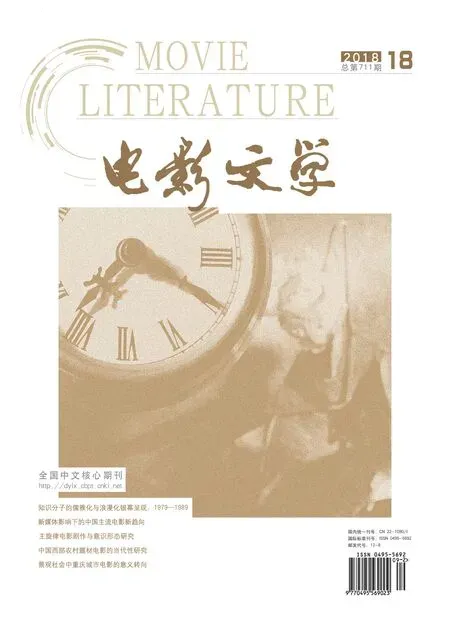景观社会中重庆城市电影的意义转向
欧阳照 李常昊
(重庆大学 新闻学院,重庆 400000)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写道:“城市也认为自己是心思和机缘的产物,但是这两者都不足以支撑起那厚重的城墙。对于一座城市,你所喜欢的不在于七个或是七十个奇景,而在于她对你提的问题所给予的答复,或者在于她能提出迫使你回答的问题,就像底比斯通过斯芬克斯之口提问一样。”对于一座城市而言,拥有能够区别于其他地区的奇景自然会使人印象深刻。在重庆,解放碑就扮演着这样的角色。2016年重庆文化艺术研究院研究和调查推出的“重庆十大文化符号”中,解放碑不出意外地强势上榜。2018年五一节期间,渝中解放碑地区更吸引了近300万人次的游客,相比上年增长了216%,增幅在全国热门城市中排名第一,重庆也首次进军全国旅游城市前三,成为名副其实的“网红”,而这其中也不乏重庆城市电影的功劳。
正如东方明珠之于外滩、大本钟之于泰晤士河畔一样,这些由地标建筑延伸出的空间伴随着城市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内涵,让人们认识并且记住这些城市,而同时最重要的还是,使我们去追问解放碑这样被赋予结构特征的地标建筑在景观社会中如何彰显出它们独特的形象,特别是由媒介为解放碑构建的光影空间又会为重庆城市电影提供怎样的新的维度?
一、时空变迁中的解放碑
解放碑的历史要从全面抗战时期说起。由于正面战场的失利,国民政府于1940年正式迁都重庆,与此同时,为了鼓舞士气,动员全国人民抗日救国,国民政府就于1941年12月31日在重庆市中区都邮街广场建成一座四方形炮楼式木质结构纪念碑,为象征“七七事变”,故将其修成约七丈七尺高,命名为“精神堡垒”。但是,木质的纪念碑经不起长时间的风吹日晒,战争期间也不能很好地保护,最后整体坍塌。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政府为了纪念全国军民一致抗日做出的巨大牺牲,在原“精神堡垒”的旧址上建立起了“抗战胜利纪功碑”。1950年10月,人民解放军解放重庆主城后,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于“纪功碑”下广场检阅驻守重庆的武装部队和民众游行队伍时,题词将“抗战胜利纪功碑”改为“重庆人民解放纪念碑”。而后解放碑渐渐成为重庆重要的公民文化、经济活动场所。1997年解放碑地区最繁华地段率先建成购物广场,随后又建成了八一路“好吃街”,以延伸民族路休闲购物步行街,与此同时,众多高层和超高层建筑也开始云集解放碑,使解放碑成为名副其实的城市中心。
然而就像孙隆基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中提到的中国城市历来“重京师而抑郡国”的发展模式那样,解放碑从最初单体的“精神堡垒”,发展到了现在2.24万平方米、现代化建筑林立的综合商业区。然而“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人为地将首都、中心的地位抬高,显然并不只是天下主义后遗症(以首都为中心、其他区域为次第边缘的地理空间想象之上具有普世特质的“大一统”式政治文明体系)的一种仪式性残留那么简单。强干弱枝倾向的存在,同样标示可能出现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在度过快速成长的时期以后,由于渝中区先天的山地丘陵地貌——地势起伏大、建筑用地缺乏,暴露出一些不可回避的问题,例如产城分离现象、道路交通矛盾以及地理条件更加优越的城北观音桥等城市中心的出现,都让设计初衷用于集会、纪念的解放碑不论从性质、意义,还是自身实际发展需求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然而在这些冲突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狭窄紧凑的空间地形、起伏魔幻的建筑格局的确制约了解放碑地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但赋予了其创造光影空间中独一无二景观的优势。
二、城市电影中的解放碑
我们一般将城市作为叙事空间的电影称作城市电影,随着城市地位的提高,国内对城市电影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并且将城市电影和城市形象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城市电影不仅记录和反映着现代城市生活,同时也影响和塑造着以现代城市为标志的新的文化空间和社会关系”。
复旦大学城市传播研究学者孙玮认为,上海作为现代都市是以交流作为社会的基础,“这种交流以经济贸易为核心,扩散到政治、文化、社会的各个领域”。而当我们的目光聚焦于重庆时,就能发现这种交流却迸发于现代化进程中的新旧文化碰撞,而解放碑地区恰恰就是这种复杂性冲突最明显的地区之一。不得不承认的是山地地型和江城风貌为重庆的影像空间提供了极大的发挥潜力,使它的景观呈现能够区别于京派、海派等城市电影。特别是近些年在张一白“重庆三部曲”(2002—2009)、王小帅《日照重庆》(2010)等著名导演的镜头下,于重庆取景并反映重庆日常生活的作品成为具有很高辨识度的一类城市电影。据统计,自1933年在重庆开拍的第一部电影故事片《歧途》到如今,已经有316部影片在重庆取景。从2010年开始重庆电影更是成为电影市场上的宠儿,仅院线就上映了多达34部在重庆取景的电影并且其中14部出现了解放碑地区的景观。根据这些电影拍摄的主题和类型,我们可以简单将重庆城市电影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抗战时期,国家电影制片厂在重庆拍摄的抗战宣传片,如《中华儿女》(1939)和《胜利进行曲》(1940);第二个阶段是新中国成立以后重庆本土的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如《嘉陵江边》(1958)和《巴山夜雨》(1981);第三个阶段就是重庆成为直辖市以后,越来越多的外地电影摄制组慕名来渝拍摄,如《火锅英雄》(2016)、《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6)。重庆独特的自然环境成为电影景观得天独厚的优势,并且也使其故事情节获得了别具一格的气质。
(一)地域特点创造城市奇观
法国哲学家居伊·德波在《景观社会》中认为“世界已经被拍摄”,而景观更是正在改变我们观看电影的角度,并且成为一种物化的世界观。可以看到江城风貌催生了重庆独特的城市形态,而其城市电影最为突出的特点也在于利用极具城市空间代表性的新奇景观,传递具有视觉吸引力和快感的影像。解放碑地区代表性的自然地理与城市空间,为“城市奇观”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可以看到重庆城市电影中这样的景观很大一部分都出现在解放碑地区,例如《疯狂的石头》(2006)跨越奔腾江水与渝中区层层叠叠居民楼的长江缆车,还有在解放碑地区落差巨大地表上耸立的纽约·纽约大厦以及《好奇害死猫》(2006)中隔江眺望解放碑的豪华建筑“海客瀛洲”。这样的“城市奇观”是电影创作者对重庆的解释和呈现,对于外地观众来说“长江索道”“纽约·纽约大厦”“大江奔流”这些基于特殊城市空间存在的景观,在自己城市中是几乎无法看到的,也就必然会使他们对电影留下特殊的印象。对于新奇的强调,无疑是创作者们有意选择的结果,他们试图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创造关于重庆这座城市独特的景观。重庆城市电影中的“城市奇观”正在成为一个代表重庆的符号,而这个符号则由“魔幻空间”“新旧对峙”“家乡归属”三种景观组成。
第一类“魔幻空间”主要是呈现错落立体的山地江城,例如《周渔的火车》(2002)中对横跨长江的渝中区索道长时间的特写——从南岸区视野开阔的江畔一直随着索道延伸至渝中区错落的建筑物深处,滔滔江水与此起彼伏的楼宇把江城的恢宏形象刻在了观众的脑海中。《火锅英雄》(2016)中时而与街道齐平时而跃过高耸的楼顶,时而又从狭小密集的层楼中钻出的城市轻轨,把山城起伏错落的地形表现得格外魔幻。另外,为了节约空间和夏日避暑在防空洞里改建的火锅店——“洞子火锅”,更是将重庆市民的饮食习惯赋予了魔幻新奇的色彩。独特的城市空间决定了重庆城市电影对于景观选择的先天优势。因此,重庆城市电影往往都能创造出令人记忆犹新的场景,就像穿楼轻轨、洞子火锅等,这些魔幻又极具重庆特色的景观经过影像上的不断重复,很自然地成为重庆最特殊又最新奇的景观。解放碑地区独特的城市构造成为重庆电影的独特性重要的一部分,而电影的景观呈现也让重庆这座城市在观众看来具有与千千万万个中国的城市不同的独特性。
第二类“新旧对峙”是表现戏剧冲突的城市空间,如《疯狂的石头》中从228米高的纽约·纽约大厦上俯视近在咫尺的低矮贫民区,巨大的空间落差更凸显了繁荣和贫困的对峙;《好奇害死猫》中的洗头妹居住、工作的破旧出租屋被豪宅和高楼密不透风地包围着,错落重叠又拥挤不堪的民居为全片的戏剧冲突定下了基调。从城市建设的角度来说,直辖以后重庆经济发展迅速,然而稀缺的建筑用地还是很难满足快速增长的人口,“新旧对峙”的现象在城市建设早期着重发展的解放碑地区就显得尤为常见。这种新与旧、现代与古老、繁华与贫困在及其近的距离和极小的空间里呈现出撕裂和对峙,在其他城市也少有重庆体现得那么集中和戏剧化,这激发了创作者以这种特殊的对峙感来呈现重庆视觉形象的意图。
第三类“家乡归属”则是通过特定景观寄托了重庆人民的乡愁情节。重庆作为一个码头文化城市,流动人口较多,社会关系是建立在对个体内在本质的认可和评价之上的,而对外在身份地位的关注则相对较少。这一点在饮食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重庆“江湖菜”就是力求食物口感味觉出众,并不像其他菜系那样以高雅自居,而各个阶层间在饮食上更没有明显的区隔,在这样的人文环境中就能看见公司白领和无业百姓为了美食,融洽地拥挤在同一家老店中涮着火锅的场景,同样街边简单的小面馆在老板热情的招呼下也更蕴含了重庆码头文化务实中透着一种自豪的精髓。这就让重庆城市电影能够相对贴近平民百姓生活,并且能够更多地通过日常生活景观表现出一种平易近人、触手可及的家乡感。在特有的生活方式下产生的人文景观对于观看电影的外地人来说是一种新奇的体验,而对于重庆本地人来说则就饱含了浓厚的家乡情感。例如《火锅英雄》中主角和阔别已久的初中女同学在渝中区群楼穿梭的轻轨中相遇、《从你的全世界路过》(2016)里十八梯老城中沿着石阶搭建生意火爆的小面摊以及“猪头”与恋人分手时留着眼泪跑过的灯火辉煌的滨江大道。“穿楼轻轨”“石阶小面”“滨江夜景”都是重庆最具代表的城市景观,而初中同学、发小、初恋情人又都和“家乡”有关。解放碑作为重庆的标志,虽然经过战火的影响但其经过时间积累下来的特殊的城市空间和文化价值,在令外人好奇惊叹的同时也承载了重庆人民宝贵的乡愁。对于很多离开家乡的重庆人来说,“解放碑=家”这样的观念早已是深入人心。
地域优势在重庆城市电影的景观呈现中可以说表现得淋漓尽致。重庆城市电影光影空间的意义也在景观社会的影响下开始发生了转变,选择具有极具特点的新奇景观来推动电影叙事,一方面在“可控范围里增大文本的阐释空间,降低电影的复杂程度”,并且使景观成为一种新的电影语言,另一方面在经过电影构建的光影空间重复和强调,这些新奇的景观成为一种具体的城市符号,在观众心中固定了下来,成为人们对重庆城市电影和重庆这座城市的潜在认知。并且事实证明这样创造城市奇观的方法收到了很好的效果,2016年《火锅英雄》和《从你的全世界路过》热映,相继以3.7亿元和8.1亿元的票房打破在重庆主城区拍摄电影的票房纪录,《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更是获得了中国内地影史华语爱情片票房冠军。“洞子火锅”“山城夜景”也成为重庆城市文化的热点,而长江缆车更是从最初方便人们生活的交通工具,变成日运载量1.05万人次的观光景观,并且在2018年2月6日升格为国家4A级景区,在一定程度上说明重庆城市电影的传播效应日趋显著。
(二)内容单薄缺乏本土意识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重庆城市电影中这样的景观正在逐渐类型化。“在现代生产条件无处不在的社会,生活本身展现为景观的庞大聚集。直接存在的一切全部转化为一个表象”,在电影中被想象和被阐释的重庆并不是真正完整的重庆,观察电影中出现的景观我们可以发现,这些表现城市特殊形象的景观大多显得“草根”“市井”“贫富悬殊”,但这些并不能展示现代化的重庆新貌。同时电影中也很少展现出重庆区别于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现代化建设中独特的一面,简单地呈现“高楼”“夜景”或者“都市生活”并不能将重庆与其他城市区分开来。从艺术创作和作品接受的角度来说,稳定的符号肯定会比复杂陌生的形象容易理解和接受,商业电影对重庆魔幻城市奇观的呈现,是为了吸引更多的观众从而获得更好的市场票房。“对于过去尚未形成区域电影特色的重庆电影来讲,符号的形成固然具有积极意义,因为它可以为城市和区域电影提供更高的识别度和独特性。但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看到在审美过程中,符号有可能覆盖甚至遮掩真实,以至于排斥本符号外对客体的再阐释。”对于重庆城市电影而言,“草根”形象的固化,会让观众产生极大的偏见,这样独特景观的积极意义也会逐渐减弱。
作为现代化新城与落后老城并存的空间代表,重庆成为银幕上中国时代剧变中一个显眼的、高识别度的城市。但真正反映这座城市本身的故事还不够,更多的影视作品只是把重庆作为一个故事的背景,并没有让它成为主题。相比而言,同样是山地城市代表的香港,在城市电影的制作上则要显得更加成熟且细腻。在景观的呈现上香港城市电影并没有突出表现与众不同的城市奇观,反而更多地展现日常可见的香港本土符号,如《岁月神偷》(2010)中的处于港英政府压制和内地运动波及的市民生活中心——永立街、《文雀》(2008)中任达华饰演的主角每天早餐都会去吃东西、看报纸、聊天的茶餐厅。“城市空间的特点在香港电影中通过最本土化的空间符号来体现,茶餐厅、巴士、写字楼和街道,它们是香港的符号,共同造就香港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殊性。”除此以外,香港城市电影在题材上还格外地注重本土意识的塑造,“香港电影深深根植于民间,以一种画面上粗糙但感情上贴近的方式反映这个城市的本土现实”。像《虎度门》(1996)、《香港制造》(1997)等电影将个人的成长与城市发展紧密结合,并且传递出一种无关你的身份地位、只要努力就能在香港实现个人理想的价值观。1997年香港回归以后更是将镜头直接对准转型时期香港社会的纷繁陆离与香港民众的现实生活,如近些年获奖的反映香港社会阶层僵化以及对底层人士的漠视戕害的《踏血寻梅》(2015)、反思香港回归前后社会迷失感的《树大招风》(2016)。强烈的社会责任、深厚的时代关切与鲜明的艺术个性组成的本土意识,成为香港电影能够长久地在国际影坛上获得关注的重要原因。所以当在重庆城市电影中出现的“草根”形象扎根于观众脑海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将富有个性的故事内容展现在观众眼前。
三、结 语
景观社会中,每一个电影场景都尽可能地让观众感受到新奇和刺激,然而这些画面和叙事的推进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以说重庆城市电影中虚拟空间对城市的展现仅仅停留在对新奇景观的塑造上,对真正孕育城市独特形象的本土意识和人文历史的挖掘还远远不够。但事实上从新中国成立时“川渝合并”“三线建设”到“九七直辖”,重庆本土文化情结还是有很多可以记叙的故事。借由城市奇观留在观众心目中的城市虽然独特新奇,却难以保持新鲜,不足以支撑一类具有长久吸引力的城市电影,更无法展现一个完整的、发展的重庆城市形象。景观特点成为符号是城市电影创作从零散状态向有序状态的重要转折,但是能够在已经固化的符号中寻找更具本土人文特性的元素才是重庆城市电影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