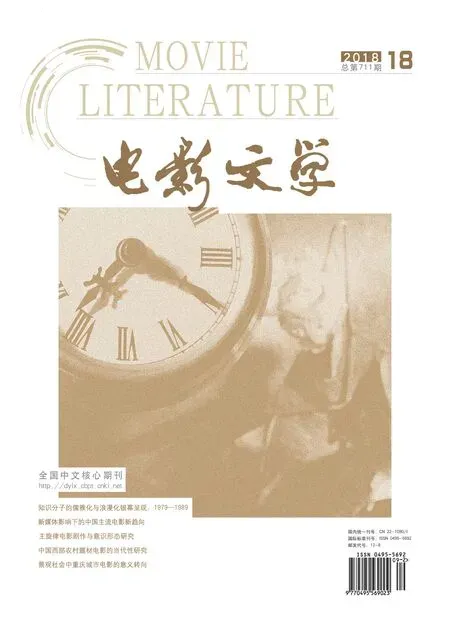电影《动物庄园》的意识形态解读
高 坚
(中国传媒大学,北京 100024;南阳理工学院,河南 南阳 473000)
英国小说家乔治·奥威尔的代表作《动物庄园》(Animal
Farm
)完成于1945年,时值第二次世纪大战刚刚结束之际,作者用一种超乎想象的政治隐喻描绘了专制独裁和政治霸权所导致的恶果,其批判力度引人深思。在电影史上,《动物庄园》曾被两次改编,分别是1954年英国拍摄的同名动画电影和1999年美国拍摄的真人电影。虽然两个版本风格不同,但都尊重了原作精神,较明显地探讨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 “意识形态”不再仅仅是哲学上的一个认知概念,而是凸显了一种政治倾向和阶级构成上的功能,重点强调的是它对社会个体的“询唤”。这种“询唤”与阿尔都塞的理论观点不谋而合,都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意识形态的运作机制和它在“主体”生成过程中的三种功能,即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征服功能和身份认同功能。尤其是1999年版的美国电影《动物庄园》,通过人和动物的真实演绎,更是将这三种功能贯穿影片始终,用一种特殊的影像造型、极具风格化的视觉符号,通过一场在“意识形态”操控下的“动物革命”,诠释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功能。一、“启蒙与询唤”: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再生产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系统地讲述了主体生成的过程是“主客对立”与“主客同一”之间周而复始的循环运动,就是一种主体的生成过程。尼采和福柯先后宣称上帝已死、人类已死,直接“剥夺”了人类的生存意义和生存价值。西方哲学的“主体死亡论”将现代哲学对人的研究蒙上了一层消极的暗纱,而“主体生成性”的提出,是对“主体死亡论”的一种超越。后结构主义学派也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言说,即“主体的一生,永远‘不是在说话而是被说’的一生”!这说明了主体的生成过程,更说明了这种“生成性”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极大,其中恰恰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即对主体的“再生产”。
这种“再生产”不仅仅是指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更是指“个体”在思想意识、观念意识等方面的再创造。阿尔都塞曾说过“人生来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从发展观的意义上讲,人作为主体,不是一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未完成的”和“趋向生成”的东西,体现了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这都说明“个体”具有“生成性”,是运动和发展着的,而非处于一成不变的静止状态。将“个体”对现存统治秩序和法律规范在顺从态度上的再生产,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在实践方面的再生产,最终使个体变成被“询唤”的主体。这种“再生产”可能是自动寻求的,也可能是强制性的。而在影片《动物庄园》中,黑猪拿破仑从一个地位卑下的普通个体,后来通过暴力政变成了庄园的领袖,这一过程印证了一个从“个体”到“主体”的生成性过程。影片开头部分,拿破仑作为一个懒散的、无知的“个体”,身处一个特殊的社会环境。而老麦哲的出现,一个团体意识形态的化身,它提出了“动物主义”的思想,通过身份建构、语言教化和“主义”话语的言传身教建构了拿破仑的主体性,为拿破仑后来的夺权、革命和建立新的秩序,提供了合理的理论依据。拿破仑改头换面,从一个下层“猪猡”变成了至高无上的统治阶级,这是一个典型的主体生成性过程。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再生产。这种意识形态,来源于老麦哲的说教,一开始他就给农庄里的所有动物上了一堂“思想启蒙课”,让他们认清了自己任人宰割、受人剥削、被人奴役的处境。在它所提倡的“动物主义”思想的感召下,动物们与农场的原主人琼斯之间展开了殊死搏斗,并最终赶走了他。正是老麦哲这次意识形态的“思想启蒙”,动物们开始重新认识自己,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即对个体思想上的一种“再生产”。
二、“霸权与教化”: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及其运作机制
意识形态一旦稳固下来,就要发挥其另一个重要功能,即维护稳定和征服不同思想的功能。它一方面保证了个体的顺从,另一方面又维护整个社会的制度体系。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起到了重要作用。“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是阿尔都塞首创的一个概念,来源于1969年他所写的著名论文《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一概念“揭示出了主体及主体性被建构的物质基础和体制结构”。阿尔都塞认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通常通过政治、法律及其附属物,诸如政府、军队等使个体屈从于它,进而用观念性的意识形态使个体被询唤为主体。
只要“主体”存在于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就必定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意识形态是一种较为抽象的理论,但并不是空洞无物的。它是由各种具体意识形态组成的,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宗教思想、社会思想等多种思想构成的意识形态总体,而这些思想是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向性,也可以将意识形态理解为一种实体的物质存在。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时代性,它是一个社会阶层、一个时代主导的核心价值观,是社会思想观念塑造的主导因素。阿尔都塞强调意识形态的物质属性,不单指意识形态广泛存在于社会实践中,个体只能在思想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产生虚幻的想象,进而屈从于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个体要参与并成为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人的主体性塑造与意识形态是密不可分的,意识形态主要通过身份构建、话语构建等途径来建构“主体”。意识形态的霸权特性规定人们哪些不能做,哪些不能想,其教化是想告诉人们应该怎么做,应该怎么想,在意识形态的规制下塑造了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的“主体”。这种意识形态兼具霸权与教化两种特性,霸权导致屈从。通过教化和屈从,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及其运作机制。这在影片《动物庄园》中拿破仑的对手斯诺鲍和老马鲍克瑟身上体现的尤为明显。
“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首先体现一种“霸权”特征,通过这种“霸权”,完成了统治者清除异己,统一思想意识的目的,从而建构意象中的“国家”。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施行镇压和干预的力量,这样的国家机器才是真正的国家,才真正定义了它的基本“功能”。电影中,唯一对拿破仑的独裁统治提出质疑和反抗的是动物庄园革命领袖之一,一只叫斯诺鲍的猪。后来,斯诺鲍被认定为革命中最危险的敌人,被统治者驱逐出境。拿破仑与斯诺鲍展开了殊死搏斗,最终战胜了对手,确定了自己新的统治权威。同时这种霸权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主体性”,完成了意识形态的霸权使命。而影片中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化”作用主要体现在老马鲍克瑟身上,它是一位“动物主义”理念的忠实追随者,一生忠心耿耿,吃苦耐劳,时刻响应革命领袖拿破仑的各种号召。鲍克瑟一生从不怀疑,只坚信两个信条:“我要更加努力地工作”和“拿破仑同志永远是正确的”。它在农庄建设风车的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最终积劳成疾,被主人卖给了屠夫,拿破仑用它的毛皮和骨头换来了威士忌。在鲍克瑟的追悼会上,拿破仑一边喝着换来的酒,一边给其他动物讲要向鲍克瑟学习,继续效忠于他,这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教化”作用发挥到了极致,通过这种精神束缚达到了拿破仑独裁统治的最终目的。无论是这种“霸权”还是“教化”,都体现了意识形态的征服功能及其运作机制。
三、“认同与接受”: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结果
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对人个体性的建构的分析,解析了社会个体如何对自我身份进行认同。意识形态不可能离开主体而存在,它的重要的功能就是把单一的“个体”变为社会的“主体”。他还认为“主体”并不是客观存在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意识形态对“主体”的建构主要是通过对“个体”的“询唤”来实现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并不是简单的生理反应,即“刺激-接受”的过程,而是一种更高级别的影响过程,即“教化”和“暗示”等。“个体”对社会身份产生认同的过程就是意识形态中将个体“询唤”为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和拉康的“镜像理论”都强调“认同”,“认同”是对主体自身的一种认识和描述,而这种认同是随着社会现实而不断变化的,这一概念将“认同”与社会关系联系起来。拉康是最富争议的精神分析学家,他认为“镜像阶段”是发生在婴儿前语言期的一个瞬间,6~18月的婴儿在镜中能够认出自己的影像,并能够意识到自身的存在。但这种对自我影像的认知并不是对“主体”的认同,而仅仅是对“幻象”的认知,是生物性的“我”而不是社会性的“我”。此后,个体通过各种外界的影响和规制,镜中的“幻象”逐渐成长为社会现实中的“主体”。阿尔都塞的“询唤理论”借鉴了“镜像理论”,意识形态对“个体”的“询唤”不可能直接造就“主体”,“个体”必须通过借助各种社会现实对自身进行“身份认同”,才能够确认自我身份和形象等,并进行想象性的关联,将自己同社会现实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影片《动物庄园》中,作为个体的斯奎拉一开始就对主体意识形态有一定的认同,它是拿破仑的随从和谋士,当拿破仑所建构的那套“意识形态”起作用时,斯奎拉是那群动物中最早得到认同的一位,也是意识形态对“个体”询唤最为成功的一位。它时时处处维护新形成的意识形态,为了让其他动物们听命于拿破仑,“接受”拿破仑建构的新的社会秩序,它不厌其烦地对动物们进行思想训诫,用它那惯用的伎俩——通过今昔对比,让动物们“接受”现状。他常说“你们没有谁希望看到琼斯卷土重来吧”,这句话成了动物中那些怀疑分子的“紧箍咒”。通过把过去的可怕经历和眼前“安逸美好”的现状做一对比,来消解动物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从而达到他们对拿破仑所建构的现实社会的认同。斯奎拉自身对主体意识形态的“想象性认识”,是确定自我“认同”的前提和基础。而这种“想象”使它和拿破仑结成了坚固的独裁同盟。斯奎拉从奴仆到谋士,从一开始与主体意识的想象性关联,到发展成为革命团体的一分子,最终与这一革命团体和意识形态结成了紧密的关系。这种“认同和接受”,无不体现出意识形态对“个体”的成功询唤,最终确定了它稳固的社会地位。
对影片《动物庄园》的解读,不应仅仅局限在文本层面,更应该把它放置在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去理解。把电影放在特定的文化意识形态中去理解,把电影当作一种利用和满足观众欲望、制约和影响观众思想的社会文化机制。如果按照这种思路分析影片《动物庄园》的结尾,会发现有个特别意味深长的情节:当群体动物围攻拿破仑公寓时,它们在窗外看了屋里面的一切:那群独裁者觥筹交错,把酒言欢,竟然已经竖起了两条腿走路,与人类相差无几了。影片中,人和猪的界限已模糊不清。至此,我们才恍然大悟,乔治·奥威尔的这个动物寓言实际上是在指涉人类。通过这种隐喻性的方式,批判性地诠释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询唤过程,这是一次社会学分析,是对西方独裁霸权的一种变相批判。同时也不失时机地分析了这种霸权和独裁所形成的那种“集体无意识”社会环境。从这个角度讲,《动物庄园》与德国电影理论家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的《从卡里加里博士到希特勒》形成了一种“互文关系”,因为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揭露了“意识形态”对“主体”的那种询唤功能。
——重读阿尔都塞的《论青年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