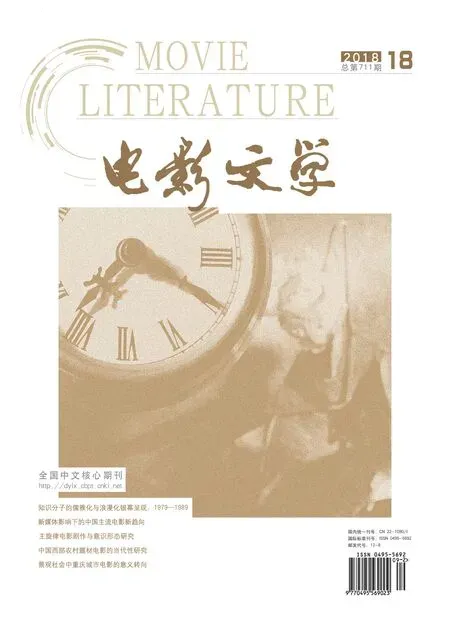论《芳华》的青春叙事
张倩玉
(中国艺术研究院 电影电视艺术研究所,北京 100029)
冯小刚新作《芳华》独特的叙事背后的丰富意蕴让我想到了先锋文学,尤其是长于描写苦难与残酷的那些作品,虽然严歌苓从未被划为这一流派。这种对苦难和苦痛的表现使影片受到了不少非议与“误读”。我认为,电影《芳华》讲述了一个关于失败和失落的故事,这一主题及其讲述方式体现出这一电影文本的文学性与现代性。
剧作方面,普遍遭到的质疑是人物塑造的“缺失”与“模糊”,我要说的第一点就是这种对人物形象的不满,某种程度上或许是人物形象过于特异引起了观众情绪上的反感。两个主要人物刘峰和何小萍与我们熟悉的“好人”形象大相径庭。一方面,作为英雄“候补”——意即他们只是渴望成为英雄人物却没有成功,他们露出了“舞台背后”的东西,展现出他们过于强烈的对于当英雄的渴求,更不用说这渴求甚至被表现得略显病态。这两个人物并没有在一开始就把“真爱”“正义”等当作信仰来追求,从而使自己区别于或说高于其他人,获得成为主角的合法性。如果将这个电影看成青春片,那么这样处理会变得合理一些。他们还年轻,生活还没有把真正的价值完全展露给他们,他们也毋须做出关键的选择,一些小的恶意可以解释为幼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接受将本片与《阳光灿烂的日子》做对比。
还有一种典型的批评针对冯小刚所属的“大院”传统,《芳华》里的青春不是普通人的青春等。这种观点只对了一半,在那个年代,这些军人是天之骄子,只有无忧无虑的他们才会去尝试当时被社会集体所禁忌的事情,也就是谈恋爱,并甘愿为此付出代价。另外,文工团也有很多象征意义。《芳华》很强调回顾的视角,方式就是萧穗子的旁白,或许可以将之和贝托鲁奇的《戏梦巴黎》对比。许多人说《芳华》拍出了时代感,文工团和越战的题材确实涉及历史,但似乎仅是背景,《戏梦巴黎》则有更多时代和人的互动与互为因果。
“五月风暴”的众多前奏之一包括法国电影迷占领电影资料馆的“朗格卢瓦事件”,《戏梦巴黎》的主角就锁定三个迷影青年。其中一对孪生姐弟伊莎贝拉和马修仿若艺术的化身,深情而天真,他们自己甚至不知道他们早已彼此相爱,一个美国青年的到来打破了他们含混的乌托邦。美国青年先是和姐姐相爱,随后姐姐发现了她内心对弟弟深藏的情感。他们三人经历了友谊、性和艺术,但将这些都抛弃了,姐弟俩最终选择了他们爱的乌托邦——死亡。在美国青年夹杂嫉妒的激将之下:“你们只会说,为什么不去加入革命呢”;在对乱伦之爱绝望之后,姐弟俩手拉手投身火光熊熊的街垒战,留下震惊之后怅然的,失去了爱情和友谊的美国青年站在原地。他目送姐弟俩离开,仿佛看着自己的青春和理想远去,背景音乐是皮亚芙的《不,我不后悔》。我认为影片赞美艺术与爱高于一切,甚至高于革命。年轻就是懵懂甚至有些堕落的,他们的牺牲可能并无崇高的目标或不仅为了理想,也可能是走投无路,即便这样也是美的,因为那是不可重来的青春,美感就在于迷茫。
回到《芳华》,除了“抓猪”一段介绍了时代,影片中看不到更多革命年代的“街景”,导演似乎有意将这群人和时代隔绝了。这种隔离感在《戏梦巴黎》里也有,但侧重表现的是主角三人和其他人的隔绝,而不是主角和时代。而《芳华》则是一种环境和时空的区隔,仿佛文工团和外面的人同在一个时代又不在一个时代。我以为时代问题就是理解这个电影的关键。
题材方面的禁忌或许是个问题,被略去背景的革命和战争之外,剧情重点有一部分转移到了当代生活,这使剧作分成了前后两部分。表面看似乎“断裂”了,但如果我们的前提是分析既成文本,而不认为它是“有问题”的,那么现在这个两段式的文本就可以作新的理解。简言之,表现那个火红年代的生活经验或许不是这个片子的真正意图。一个重要线索就是“文工团”这个影片的表现对象,它是一个集体,也是一个特殊的场域和空间。普通大众并不了解文工团是怎样的,好奇从一开始就支撑了影片。换句话说,文工团才是本片的“主角”,影片叙述了文工团的样貌以及文工团的解散;而电影后半部分对文工团解散后的展现,就是为了进一步说明文工团是一个怎样的存在。
那么“文工团”到底是什么?影片一开始的时代是“文革”,文工团跳《草原女民兵》,舞蹈表现的是“文革”之前的战争年代。问题在于战争已经结束了。战争过后,人们却还沉浸在战争的美学中。这也可以部分解释文工团外面正在发生的事——无尽的酷烈斗争在战争之后延续着,从肉体蔓延到精神,又返还到肉体。而文工团里这些人免于社会上的事件,被艺术庇护,被“特权”庇护,他们是否就得到了幸福?通过小萍的遭遇可以得出,答案是否定的。时代的创痛波及每一个人,通过小萍这一个角色已经可以见证时代。小萍深夜给父亲写信,长镜头深深“注视”她默默哭泣的脸,这是比舞台上的光鲜形象更真实和高贵的人性之光。这个镜头需要在时代背景下去看,如果对当时的人性扭曲没有认识,就会觉得这是一个不必要的煽情。我欣赏这个固定的长镜头,它有很大的张力,表达了清晰的价值观。冯小刚的作品不乏煽情,但这一次因为有时代的深沉底色而真正落实了。
当小萍和刘峰相继遭遇生活的创伤后,他们来到了战争的流放地。在战场上,刘峰才拥有了成为一个真正英雄的时刻,而他自己却未必意识得到,观众也未必会发现。他从沼泽里救出了战友的时候,这一段可以看成整个电影的“题眼”。刘峰一只手臂受伤,拼尽全力也无法救出战友,眼睁睁看着他被污泥淹没,他痛苦得撕心裂肺;终于,其他战友及时赶到,大家合力拉出了沼泽里的战友。这一段表演戏剧性充足,含义也很丰富。刘峰在这时哭了,不只是因为救出战友的高兴、庆幸、后怕等复杂情绪,还有一层象征是他看见了他信仰的东西——集体主义是有用的,从而重新确证了因为不公的遭际或许已不自觉开始动摇的信仰。他救了别人,也救了自己。影片最后,刘峰终于在爱情上也无私了,他和小萍在一起也是一种成全别人,尽管是互相成全。刘峰整个人生的失败是一种对时代的叹惋,同样地,受尽苦难的小萍也是一位牺牲者。在今天的时代讲述这样两个人的故事,我认为表现出了一种正视历史和悲悯的态度。雷蒙·威廉斯在《现代悲剧》中提出“令人悲伤的无序状态及其解决”就是悲剧,现代的社会革命与危机属于悲剧,需要被审视并给予审美上的关注。
从惨淡的结局反推,战争才是男女主角人生的高潮。战争的作用就是为我们“筛选”出剧中真正有信仰的人,也就是刘峰和小萍这样的人,或许还有战地记者萧穗子。值得注意的是,她同时也是最留恋文工团的人,她的情感全部寄托于此,标志就是她在离开文工团的同时失去了爱情。萧穗子是文工团的一个象征,所以被称为第三个“主角”。从主题来看,其实刘峰和萧穗子这两个人才是本片真正的主角,因为他们都经历了刻骨铭心的失恋。
说他们俩是主角还有一个原因,只有这两个人兼具了剧中人和旁观者两重身份,和作者/导演的视角合一,他们理解了一切,原谅了一切。何小萍则不具备这样的动作,她从头到尾都被伤害,只有一个主动的反抗就是拒绝演出,而这之后,她不得已在台上进行舞蹈表演的片段在影片中被删去了。如果不把她看成主角,那么这样的删除就是合理的:她的拒绝有没有产生效果,或产生了怎样的效果并不重要。她只是苦难与折磨的象征,是对时代的批判。《归来》的女主角没有清醒过来,小萍却忽然痊愈了。她痊愈之前的最后一个镜头是她在草地上的独舞,剧情上这里缺乏交代,也缺乏说服力。或许可以理解为身体记忆唤醒了她对于从前的记忆,并最终帮助她克服了战场上的创伤。
影片这样的处理确实有些“以意逆志”,文学性强而合理性不足。我的理解是她跳的那支舞是当年和刘峰搭档跳的,那之后刘峰就离开,她从此失去了自我,这是她的第一次创伤,后来在战场上层叠的心理创伤压垮了她。她的疯狂是有根据的,但她的痊愈过于象征性,说明这个人物只能算作功能性人物。另一个具象征性的人物是林丁丁,她拒绝刘峰这个情节也是作品的关键情节。她“恶心”的感觉放到全片主旨来看也是一种象征。高尚的、精神性的存在忽然显露出身体的、本能的东西,林丁丁感到巨大的冲击,这种体验其实是面对商品时代的社会巨变时大众的共同体验。从这一细节也可以看出,影片前后两部分内容是呼应的。
刘峰和萧穗子的恋爱,或者说“表白——失恋”就是本片主线,因为和文工团关系最密切。对于《芳华》表现几个时代的目的,这里提出一个假设。《草原女民兵》表现的是战争年代的事,非战争年代只能对之怀恋,“文革”时,文工团将那些青春少年隔绝在现实的残酷之外,使他们沉浸在对上一场战争的怀旧中,并树立信仰。这之后,刘峰和小萍真的去经历了战争,对刘峰们来说,这战争不算残酷,反而是他们梦想成真、变成英雄的时刻。更残酷的其实是这场战争之后的当代生活,血腥的战争反而成了最后一段可以怀旧的时光。怀旧就是一种救赎,历史是战争和非战争状态的交替,只有怀旧的乌托邦可以寄身。
失恋的青春、流血的战场仍是美的;失去青春,没有了梦想,没有梦想成真或破灭的机会的平淡生活才是最可怕的。刘峰和小萍以及萧穗子继承了文工团的怀旧机制,并将怀旧的对象替换为真正的战争。因此他们始终成功将自我隔绝于现实之外,他们心中是战争年代的血与泪,情与义。其他团员则对文工团没有那么深的感情,也就是说这种怀旧没有进入他们的骨髓,因此他们要接受生活的摧残。况且,其他团员怀的是文工团的歌舞表演里战争想象的旧,刘峰和小萍怀的是真实战争的旧,后者的信仰因确证而真实。《芳华》有一组概念是可替换的,使这部电影具备了完整性和可阐释性,它们是:革命—信仰—青春—爱情—美—真实。
《草原女民兵》和红歌都是对战争年代之“真实”的致敬和缅怀,目的并不是想要回到战争年代,而是回到纯真与信仰。其他团员没有见过那足以产生信仰的战争/爱情,只有刘峰和小萍以及萧穗子经历过,不管多么惨痛,只要是真实的就是有价值的。跳舞的萧穗子和小萍令人印象深刻,因为那是灵与肉的合一,是对青春的赞颂。萧穗子是用青春的热情去相信,这种先验的热情能穿越时光直抵彼岸;而穿病号服的小萍则是重新选择相信早在文工团时期就开始失落的信仰,将无形的信仰用身体彰显于草地夜空。同时,他们俩也是爱情的失败者和始终不渝的信仰者。以上就是《芳华》的主题,即对于爱情理想和以战争为表征的青春理想的歌颂在影片叙事中的表现。
文工团员们对歌舞里没有见过的战争年代的赞美和回忆,以及对于这一段回忆战争的年代的回忆造成了几重距离。这不是有意地遮蔽某些年代,而是通过距离强调纯真年代的美好可贵与难以触及,通过怀旧的失落来召唤怀旧,甚至美好本身。与此同时,这种距离也显示出一种怀疑主义倾向。怀旧既已是一种“逃避”,对革命年代的召唤更略显小心地止于对于它的怀旧的召唤,这是含蓄还是怀疑?此外,如果和美好相伴生的是暴力,应如何看待?影片并未做出很好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