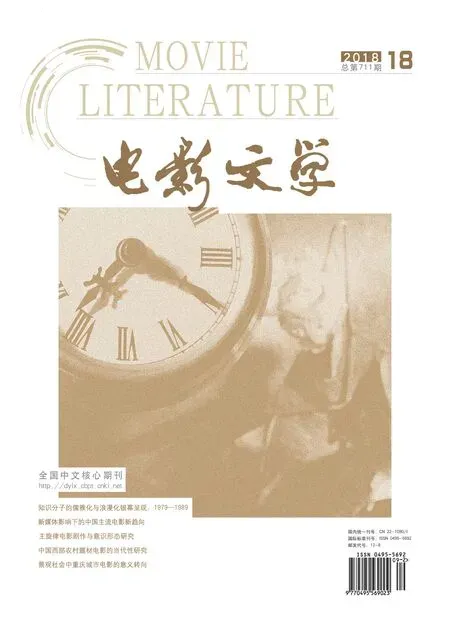“恨”文化视阈下的奉俊昊电影研究
何 静 夏 颖
(南昌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江西 南昌 330031)
尼采指出:“怨恨发自一些人,他们不能通过采取行动做出直接的反应。”是因为怨恨者始终处于一种弱势又无力反抗的状态。韩民族的怨恨便产生于命运多舛的民族灾难,亡国之恨、阶级之恨、分裂之恨……被不断伤害的民族情感因为自身的弱小而无法做出相应的反击,负面情绪的不断累积导致怨恨的产生。最终形成了脱离个人情感体验的“集体无意识”之恨。荣格认为:当集体无意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这一事件就是创造性行为,它对于每个生活在那一时代的人,就都具有重大意义。由是“恨”成为深深植根于整个韩民族的文化心理特征,影响着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恨”文化背景下的韩国电影善于表现本民族的历史和现代事件,近年来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电影的热映成为韩国较为突出的文化现象。奉式电影便是这种“恨感”精神的文化缩影。《绑架门口狗》中对压抑社会制度的控诉,《杀人回忆》里对病态社会的剖析与反思,《汉江怪物》对民族自我身份的确认,《母亲》当中对弱者的重新定义……奉俊昊以“恨”文化这一民族情绪为创作支点,运用丰富的电影叙事手法,将对时代创伤下的痛感记忆、底层人物的深刻关怀,以及“未解决”的结局策略熔铸于其电影文本中,实现对韩国民族历史、社会生活事件具象的描摹与呈现。
一、时代创伤下的痛感记忆
汤姆金斯认为:对痛苦的敏感程度,可用来描述一个社会的发展程度,如果一个社会对它自身所存在的不公正、恐惧、耻辱或敌意等负面行为不觉得痛苦,这必将是一个发展迟缓的社会。“痛感”显示的是对社会不公与丑恶现象的态度和立场,是道德底线上的一道敏感神经,是付诸行动的情感前奏。
拍摄于2003年的《杀人回忆》,故事原型取材于20世纪80年代全斗焕军事独裁时期,韩国京畿道华城发生的一起连环杀人案件,折射出暴力的独裁背景下混乱的社会状态。它将连环杀人案的社会成因与当时军事独裁统治下人人自危的韩国“社会特质”相结合,将大时代背景与小人物命运紧紧贴合在一起,通过建构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希望与绝望、生存与死亡的复杂的二元对立,揭示出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在时代洪流的旋涡中命运不可自控的悲剧性,勾勒出一幅韩国民众众生相。奉式电影的一大特点是它能敏锐地捕捉到社会现实中的不公现象,并直面于此,同时将自身对社会的痛感感知以艺术作品为媒介传达出来。《杀人回忆》回忆的并不是一件简单的连环杀人案件,而是对整个混乱年代的集体追思。军事独裁统治所带来的学生反抗运动与血腥暴力镇压积蓄成民众内心集体无意识的“恨”感情绪,并通过主人公对它的外在指向,揭露出尘封时代的痛感记忆。《汉江怪物》则借用怪物电影的类型叙事外壳,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如何克服重重困难从一只怪物手中解救孩子的故事。但随着剧情不断展开,体型庞大、凶残嗜血的怪物从何而来,为何家人在拯救孩子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怪物又是如何被消灭的等一系列问题的影像呈现,裹挟着韩国的现实问题扑面而来,突破了类型叙事的框架。在文本的深层结构中,汉江怪物背后所隐射的西方现代文明对韩国本土文化的同化与吞噬以及韩国社会各阶层利益链关系下人性的冷漠,形成某种同构关系。拥有社会学背景的奉俊昊以冷静的态度,将对社会历史的严肃思考置于故事的讲述中,对韩美历史遗留问题的考量、对政府无作为的“社会议题”发问,在无形之中将韩国的历史地位与民众对独裁和强权的不满与愤懑巧妙地外化出来。
奉俊昊电影在艺术创作层面跨越了真实与虚构的界限。影片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查案、救人的过程展示,挖掘灾难的根源,还原历史的真相,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重新塑造当代受众对时代创痛的集体记忆,对遗失的“我们的东西”的追溯,这种极具反思性的特点,使得奉俊昊电影具有超越时代性与地域性的艺术魅力。
二、底层人物的生存困境与精神隐喻
奉俊昊对身处底层的人物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关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在其著作《狱中札记》中首次提出“底层”一词,其所述的底层阶级与马克思所指的城市无产阶级有着很大的区别。它处于一种从属位置,政治地位、经济环境及文化资源都难以得到保障,压抑也成为底层群体共同的心理特征。他热衷于描写“虚弱之人”,是因为这些人是产生“恨感”情绪的首要人物,他们大多远离权利,经济困难、生活压抑,需要借助某种方式将积蓄在心中的“恨”表达并释放出来。正如马克斯·舍勒所言“怨恨首先限于仆人、被统治者、尊严被冒犯而无力自卫的人”。底层人物是奉式电影的主要表现对象,在多部影片中以“弱智者” 形象出现的“目击者”或事件“亲历者”,更是其作品隐喻的载体,亦是奉式电影极为个性化的签名方式。
《母亲》呈现出小人物命运的不可控所带来的悲剧性。援交少女雅中用自己的身体换取充饥的大米和奶奶的米酒,精神的困苦与肉体的折磨早已让她失去生存的欲望,因为无心的一句话激怒了道俊,而被道俊杀害;流浪汉原本也只是一位无辜的目击者,他心地善良、充满正义,但最后却因为说真话死在护儿心切的母亲之手。《绑架门口狗》里元俊因为不愿贿赂上司而面临升职的困境,事业不顺带来的压力与家庭关系的矛盾造成元俊内心情感的畸变,形成郁结于心的“怨恨”情绪,而他解恨的方法正是将报复对象转移,试图通过对狗的虐杀来排解心中的“恨”;办公室职员千男因为梦想登上电视台的愿望迟迟未实现而产生一种遗憾、对自我怨恨的情绪。《雪国列车》里末等车厢的人们,他们因其精神上的软弱感而选择在压迫中隐忍。每天高负荷的劳作,被迫吃蟑螂制成的食物,他们甚至为了充饥而自相残杀,违背道德良知异化成吞食人肉的“动物”。但当他们无法忍受这种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时,怨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怨恨产生后会造成两种结果,一种是在压迫中继续隐忍,一种是在隐忍中爆发,很显然末等车厢的人们选择了后者。无论是高压社会生活中小人物的挣扎,还是与世隔绝的小镇下所暴露出的人性的脆弱与冷漠抑或反乌托邦列车里人性的回归,边缘化的小人物都在以一己之力在群体中寻求着个体的生命价值。他们承受着“恨感”情绪并将其内化为自我生存的动力,这或许是奉俊昊如此关怀底层人物命运的缘由。
个体永远是被历史绑架的人质。个体以一种不得不参与的宿命谱写着历史进程。在韩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总是夹杂着军事独裁、学生运动、金融风暴、政治斗争等多种社会变革。韩国一边在享受着民主化进程带来的社会发展,一边又在追忆着社会变革中所残留的残酷记忆。奉俊昊电影中对混乱年代的描述通过“不健全”的个体形式表现出来。《绑架门口狗》中的流浪汉表面上与常人无异,直到他被关进监狱,影片才揭示出他患有精神疾病的一面。千禧之年的韩国正经历着经济快速发展的阶段,经济的迅猛发展让国民的物质条件与精神世界存在着内在矛盾。奉俊昊将社会制度的不健全与阶级社会的矛盾通过患有精神疾病的流浪汉表现出来,直指病态社会对人性的压抑导致的畸变。《杀人回忆》是一场历史记忆的集体沉思。它将杀人案件与混乱的社会环境相结合,折射出个体在大环境下的悲剧命运。智障儿光昊是那个混乱社会的时代缩影,他看清了凶手“面目”,却无力“指认”,我们甚至无法得知光昊自杀的原因,导演通过这种戏剧性的表现手法,将历史与艺术融合,传达出混乱年代下人人都是“凶手”的真相。《母亲》中有两位患有精神疾病的人物形象,一个是备受母亲疼爱的道俊,另一个则是精神病院的孤儿。闭塞贫穷的小镇背后潜藏的是思想的封闭与行为的暴力。影片最后让更为“虚弱的人”——无父无母的孤儿“代替”道俊坐牢,母亲羞愧、悲痛又无奈。奉式电影中所呈现出的精神患者,是个体在时代浪潮中的印记,也是畸形社会的历史缩影。
三、“未解决”的结局策略
结局意味着解决方法,是作品主题思想阐发的关键所在。与好莱坞类型电影所崇尚的“问题—解决”的情况不同,奉式电影常处于一种“未解决”的状态。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韩国学者千二斗认为“恨”文化的特点是不关注矛盾的解决,仅满足于诉说“恨”的感情。从社会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讲,东亚社会的“未解决”状况在于“现代性”问题一直处于场域内部与外部、东方式的前现代文明与西方式的现代文明的矛盾冲突中而难以得到有效解决。文学艺术是文化、历史的表现形式与传播载体,“未解决”状况呈现在电影艺术中多为开放式的结局,形成对现实世界的隐喻,留给观众思考的空间。
作为韩国三大悬案之一的《杀人回忆》以“未结案”的开放性结局来与现实对接,产生出现实况味。奉俊昊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我不知道真正的凶手是谁,但这部影片有 540 万人次观看,我相信,凶手就是其中一个。奉俊昊在影片中通过戏剧性的手法为观众层层剖析,影片中曾多次为观众塑造即将抓到“凶手”的假象:智障儿光昊亲眼目睹杀人凶手的行凶过程;警察在案发现场发现“变态”行径的矿产工人;逮捕到几乎符合一切嫌疑特征的犯罪嫌疑人。然而剧情的设计又将即将浮出水面的真相沉入海底:光昊在压迫下自杀;矿产工人不过是一个被生活压迫的可怜父亲;最符合凶手原型的人物在最后却因为DNA信息不符而无法定罪。故事在首尔警察与犯罪嫌疑人的搏斗中达到高潮,“恨感”情绪也在此刻达到顶点,但结局仍然“未解决”,观众始终无法得知谁才是凶手,影片也在这种遗憾与悲愤中结束。导演通过这种“未解决”的结局让故事以悲剧基调收尾,将“凶手”是谁的现实发问,通过高超的叙事技巧装载于大众的思维模式中,以此引发社会反思。时代造就了杀人恶魔,而身处那个时代的人们都是历史的“凶手”,以此揭露社会的隐痛与不安。
《汉江怪物》看似封闭的故事结局,实是“未解决”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影片最后,女孩贤秀死于怪物之口,怪物被姑姑南珠射中致命的一箭(射箭是韩国传统运动强项,具有民族性),兄妹三人与乞丐合力将其杀死。怪物虽死,但问题尚未被解决。悲剧结局背后是韩国社会生态的暗黑,美国力量、韩国政府与社会各阶层对于“救援”的干涉,将“未解决”事件摆在台面,韩国如何走出困境没有答案,只要“未解决”,怪物就有可能再回来。在影片的镜像世界中,秀贤保护的小男孩幸免于难,康斗与小男孩这对“父子”一起吃饭的温馨画面,再次体现出前现代“田园式”生活的美好,“家文化”的传承。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与美好情感是面对世事无常的唯一枢纽,这也是韩民族对自身历史命运走向的希望所在。电视里播放着政府对此次事件的回应与解释,为了不影响专心吃饭,康斗用脚将电视关掉,对上层建筑的不屑跃然银幕。这一结束画面不仅意味着阶层的隔阂与矛盾难以调和,也在无声中完成了弱势群体“恨”情绪的表达。
四、结 语
奉俊昊电影善于将真实的历史语境与现实问题嵌入类型叙事的文本肌体,阐释文本的社会政治意义,追求文本的多义性。他以极具社会问题意识的深刻发问立足于电影界,试图通过底层人物的怨恨叙事,重新审视与回应韩国历史与现实的种种问题。从宏观到微观,再从个体延伸至整体,将对底层的书写拓展为对整个韩国社会历史甚至人类共同命运的观照,成为引领韩国电影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