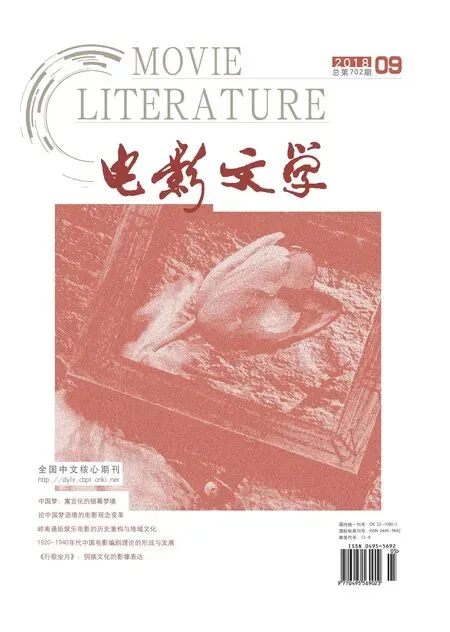《芳华》的多重视界
张思桥
(江苏师范大学 文学院,江苏 徐州 221116)
从1976年到2016年,整整40年的时间跨度,伴随着一代人的芳华凋零。但也可以这么认为,所谓的“芳华”其实根本就不存在,青春只不过是一朵貌似艳丽的“恶之花”,它吞噬了每个人的命运,然后又让它盛开在一代人的回忆之中。我们不禁叩问,是什么让刘峰这样一个善良的人走向了命运的坎坷?是什么让何小萍这样一个渴望爱的姑娘始终被人孤立?不可否认,这部作品中对于人性的窥视以及对于社会历史的认知至今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而恰恰正是这种民族情感的通约性,使绝大多数观影者在观影后产生了极大的心灵震撼,进而引发了整个社会的热议与反思。
一、金项链·照片·独舞:“真·善·美”的象征符号
和《集结号》里的“集结号”、《活着》里的“老牛”一样,在《芳华》中同样也存在着一系列担任隐喻功能的“象征符号”,它就像诗中的“诗眼”、文章中的“关键词”,让整部影片在不知不觉中得到了总体性升华。
所谓“象征符号”,是能指(标记者)与所指(被标记者)有某种内在或外在的类似性,用皮尔士的话来说,就是“某种借助自身和对象酷似的一些特征作为符号发生作用的东西”。在《芳华》中,这种“象征符号”是不容忽视的。
首先说萧穗子的金项链。金项链是“真”的象征。它的出现,是一位少女内心中“真”的呈示,是整个文工团走向沉沦时的一眼光辉。和郝淑雯、林丁丁不同,萧穗子没有她们优越的家庭条件,郝、林二者身上的骄傲与功利更是萧穗子所“不配拥有”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她和何小萍一样,都渴望爱,渴望真情,只是由于何小萍的存在,她有幸没有被孤立、被边缘。所以,当陈灿的牙被车撞掉之后,萧穗子义无反顾地冲开“秩序”的枷锁去探望陈灿并取出金项链去为陈灿做牙托。在影片中,“金项链”的出场还伴随着林丁丁“戒指”的对比出现,然而这条“金项链”却远远不同于林丁丁的“戒指”,如果说林丁丁的戒指象征着林丁丁身份的认同,那么萧穗子的金项链则是这个少女真实情感的象征,是其纯真心灵的外化。
其次是何小萍的照片。早在影片伊始,就为“照片风波”就埋下了伏笔。阴差阳错,这件事后来被众人发现,也由此开始了她的“受排挤”生活——先是照片被搜出,然后是胸罩事件、舞伴事件……而这时刘峰的出现,就像是“一塌糊涂的泥潭里的光彩和锋芒”。一如影片中的旁白所说:“一个始终不被人善待的人,最能识得善良,也最能珍视善良。”何小萍把照片撕碎后埋在了木板下面,但她没有想到,若干年后当刘峰再次返回文工团的时候,破碎的照片再次被发现、被黏合、被珍存,这种象征符号的前后呼应,在一定意义上既传递着“善”的合理性,同时也预示着“善”的最终完型。
最后说何小萍疯癫之后在草地上的“独舞”。不得不承认,这段“独舞”是整部影片的高潮所在,也是一种近于崇高的“美”的呈现。按小说中所述,她的“精神分裂”大致来源有二:一方面是在救护伤员时受到了刘峰和大夫的刺激,另一方面是前后巨大的命运反差所带来的心理冲击。所以当昔日的同伴再一次翩翩起舞的时候,何小萍潜意识中的记忆之火再一次被点燃,于是她不知不觉地走出了演厅,走向了一片开阔的草坪,开始了人生中最精彩的一段表演。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演厅中的《沂蒙颂》,也许这段“独舞”只是滑稽的;然而有了演厅中《沂蒙颂》的烘托,这段“独舞”便瞬间成为美的定格。杜夫海纳曾说过:“美是善的象征”,何小萍这段“独舞”之所以成为“美”的符号,其原因也正是在于主人灵魂中的“善”的依托。
二、红楼:一个浓缩的叙事空间
与传统的时间叙事不同,空间叙事的出现虽然很晚,但它却在各个方面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让·鲁塞曾说过:“时间和空间是文学作品按照一整套多变的音域和时值构筑和阅读的两个键盘。”相比于影片中纵跨40年的时间叙述,《芳华》中的空间叙述同样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刘峰、何小萍等人所在的红楼不是影片中唯一的叙事空间,但所有的人物、故事都是从这里缘起,它可以说是不同人物心理空间、存在空间乃至社会空间的聚集地。一方面,红楼作为一个“场”,文化、权力、身体、性别、身份、记忆等元素聚于此中,无论是刘峰的“活雷锋”事迹、触摸事件,还是何小萍的照片风波、胸罩事件,都是发生在这个“场”,而这个“场”又决定了每个人的命运走向。人与空间各自独立而又相互联系,空间与空间相互链接而最终又指向文工团的红楼,在种种关系的组合中,人既是作为存在于空间中的此在,又不断照面于新的空间。所以,未曾出场的伐木连,出场了的野战医院、越南战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红楼的延伸场域。在列斐伏尔看来,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因此,与时间的被动性不同,艺术作品中的空间建构具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它往往是被作品中的人物、故事所推动诞生,而不是像时间一样在推动着故事的发展。
红楼作为《芳华》中男男女女存在的场域,所有人性元素都出于此处。但影视艺术作为一种不同于文字文本的视觉艺术和镜像世界,追求的是一种心理上的直观效应,因此在叙事空间上的建构又略为不同于小说作品。正如有些人所说,“电影应该善于把时间性叙事转换成富有视听冲击力的空间性叙事,即善于在线性叙事的链条中寻找营造空间意象的一切机会,通过强有力的叙事空间的表现,来把故事讲得富于情绪感染力”。电影中没有选择何小萍太多的细节,而是集中描写了冲突最为激烈的那些部分。与之相反,电影中没有通过镜头去描写刘峰领奖、抗洪受伤的光荣时刻,而是选择了凸显他“活雷锋”形象的那些生活细节,其立足点都是旨在追求一种直观的审美冲击效应,从而营造出一种不同于文字文本的特殊叙事空间。因此,在这部电影作品中,叙事空间不是铺陈性的架构,而是浓缩性的聚焦。
三、本我对自我的反叛——从“活雷锋”到“英雄梦”
根据人的深层心理结构,弗洛伊德曾将其分为“本我”(id)、“自我”(ego)、“超我”(superego)三重人格。所谓“本我”,略可总结为人的各种原始本能、欲望等在无意识领域的总和,包括生的本能(生存本能和性本能)和死的本能(攻击本能)。而“自我”则“犹如一个看门人,专门控制和压抑各种不符合现实标准的本能冲动”。
再来反观刘峰,刘峰是作者严歌苓在少女时代遇到过的那种模范英雄式的人物,那个时候平凡即伟大。因此在电影一开始,刘峰就被定位成了“活雷锋”。在一个“平凡即伟大”的年代,人性中自发的“善良”往往不被允许拥有追求自由的权利。刘峰的每一分善良,都使他与领导、群众的关系更加亲密;而他的每一分善良,又让他与周围人的心理距离越来越大,直到成为人们潜意识中的“异类”。
表面上,刘峰被人尊敬、被人拥护,但实际上,众人不仅没有给予刘峰追求人性的权利,反而在“触摸事件”之后对他进行了无保留的攻击与落井下石。他们一方面禁止刘峰“本我”的释放,另一方面又借助刘峰的厄运使其自身“本我”的释放合情合理。从一定意义上讲,刘峰在那个时代就像是一个“禁忌”,大伙敬仰他,而又惧怕他。就像弗洛伊德所认为的,“严格地讲,禁忌仅仅包括:(1)属于人或物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或邪恶的)性质。(2)由这种性质所产生的禁忌作用……”
可以说,无论在什么集体中,这样一种“异类”都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总体的平衡,成为维系他者团结的工具。一方面是因为“异类”走向悲剧的必然性使然,另一方面则暴露了他者惧怕自身成为“异类”的可能与其宽容精神的缺失。
何小萍不想成为“异类”,刘峰同样不想。所以当何小萍去看望“活雷锋”刘峰的时候,刘峰将那些曾经象征着身份认同的“荣誉”通通扔掉;当他在战场上奄奄一息的时候,他宁愿用死亡来换取一段不太平凡的“英雄事迹”,从而能够让他获得林丁丁哪怕一丝的间接认同。
作者严歌苓曾在采访中说道:“我一直在想,人群里对一个弱者的迫害欲是从哪里来的?这是我们人性中的一个弱点,也正是由于这样的一个现象,导致了4个女兵不同的命运。”而事实上,人群中往往不仅是对弱者有着一定的迫害欲,对于“善良”与“正直”等品质本身也有着相似的迫害欲。正像影片中所说到的那样,“为何总是对好人苛刻,对坏人宽容? ”究其原因,也许是刘峰的善良挑战了大多数人“自我”中的人性平庸,也许是大多数人“本我”中的私欲接受不了“异类”对于普通心灵秩序的挑战。所以,不仅何小萍是悲剧的,刘峰亦然。
四、两种艺术的比照——谈《芳华》小说和电影的差异
从某种程度上讲,《芳华》既是作者严歌苓的“自传”,也是导演冯小刚的“自传”,甚至可以视之为整整一代人的“自传”。但是,《芳华》在小说和电影中所传递的思想及感情又各有侧重。
首先,电影中对于小说情节的减省,不仅仅是流于“故事”上的差异,更包含了思想倾向上的差异。其中,前者传达的是“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情怀,而后者体现的则是“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的惘然。电影虽是在立足于小说的基础之上而改编,却与小说表现出了截然不同的情感态度。例如,小说中最后的结局是刘峰得了肠癌死去,而刘峰的女儿刘倩、侄子侄媳等对亲人的离去表现出了出奇的“漠然”,这不仅让萧穗子感到诧异,同时也正是萧穗子等人心理上决然难以接受的地方——在那个逝去的“芳华”时代,无论善也好,恶也好,至少每个人身上都还是有点人情味儿的。但属于那一代人的“芳华”毕竟已远去,于今只剩下了他们难以理解的异化世界。而在电影作品中,结果则大为不同。电影最后是将镜头定格在了刘峰与何小萍相拥相依的那一刻,让他们的重逢成为青春和人生的缝合,其后的故事则一语带过,通通省略不计。
其次,在小说中,对人物采取了平行叙事的方式,是用不同人物的不同命运来架构一个总的主题;而在电影中,由于篇幅受限,则不得不借助于集中塑造典型人物的典型情境来凸显主题的有效性。即便如此,还是饱受“情节突兀”“支线混乱”等诟病。如在小说中,对4个女兵是同时展开叙述的,而在电影中,林丁丁、郝淑雯、萧穗子显然都退居主要场域,成为配角。而与此同时,何小萍与刘峰的形象,则得到了突出表现。不可否认,影视需要直观的视觉冲击,并由此进一步引发心灵的共鸣,从而实现其“格式塔”式的完型结构。
与严歌苓执着于描写“人性”略为不同,冯小刚更希望通过这一文本拍出那个时代的青春与美好,拍出他自己对于那个时代的虔诚。所以无论是谢幕时的《沂蒙颂》,还是散伙之夜所有人集体合唱的《驼铃》,无不弥漫了深深的怀旧情绪。这一点上的分歧,同样也成为电影与小说出现差异的一大诱因。
五、结 语
和同年播出的《冈仁波齐》《七十七天》等致力于探索理想与信仰之高的影片不同,《芳华》这部影片着眼于平凡的塑造,定位于生活与历史的碎片化表达。作为一个时代的产物,文工团在那时可看作是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承担过重要的政治与历史使命,见证过一代人的青春芳华。诚然,电影艺术是真实性与假定性的统一,我们不必苛求《芳华》完全符合历史真实,但起码,它给我们提供的人性认知、历史图像及时代价值所带来的冲突均值得我们进一步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