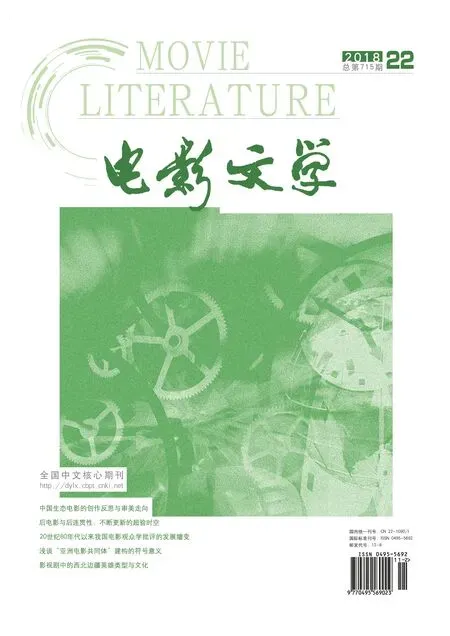电影《红颜》的女性困境读解
黄婧秋
(四川大学锦城学院 艺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1731)
李玉导演执导的电影《红颜》,上映于13年前的2005年,故事拍摄于四川省邛崃县,讲述20世纪80年代,一位女性小云人生中十年的生活段落,16岁意外生子,被男友抛弃,被学校开除,被母亲毒打,儿子也被送走。26岁,成县城戏班当家花旦,守护零落的艺术又不得不顺应时代潮流演绎流行文化,想要获得爱情却只堪被有妇之夫染指,遇见真心相待的10岁男孩,产生若有似无的两厢关照,却原来是自己的亲生儿子。26岁的小云最终与多年隔阂的母亲和解,带着随水而逝的骨肉之谜,永远地踏上了远行的火车。
影像中永远处在矛盾和抗争中的母女;那个一次又一次蹚过河流、在关键时刻拯救女主人公的男孩;生活在楼梯下方、不透光空间里的那对母子。这样的人物关系所创造出来的叙事结构有着经过时间的陈酿而散发的迷人气息。
一、符号意象的创作
(一)“鱼”
电影中多次出现鱼的镜头。
第一次,小男孩小勇为了获得云姐的欢心,叉了两条鱼放在云姐戏班子的房间门口,偷情结束的小云,推门看见水泥地上徒劳挣扎的鱼,笑了一笑。第二次,小勇和云姐如朋友般相处,他俩在剐鳝鱼。鳝鱼的头被铁钉穿过,顺着刀片,血淋淋的骨刺被小勇刮下来。而一旁小云试图捡起散落一地的鳝鱼,小勇就问道:“你怕什么,它又会不咬你。”第三次,小云得知十年前的初恋去世,在厨房剖鱼、刮鱼鳞,鱼在案板上挣扎,小云用菜刀试图打晕鱼。第四次,当小云的母亲得知小勇就是她送走的男婴,她路过湿漉漉的街道,一辆运鱼的货车在路边倾倒,满车的鱼露出明晃晃的肚皮,在肮脏的地面挣扎。
鱼在这部电影中是非常重要的符号意象。鱼离不开水,而电影中的鱼,没有一条是在水中的,也就是说没有一条鱼能够获得生存的权利。鱼的命运暗示剧中女性的命运,尤其和小云的命运形成映照。
(二)“水”
如果鱼不在水里,谁在水中?不是鱼,而是小云以及她所生活的小镇。电影开场的第一个镜头,小云坐在水中,头往后仰,她美丽、哀伤的脸庞在水里浮动。于是,女性和水的关系,在电影一开始的时候就奠定下来了。鱼在水中是生存,而女人在水中只会窒息。错误的安放,让生命之水成为死亡之水。水,既是女性柔美的象征,也是女性困境的象征。
电影本身没有做太多叙事结构的变化,而是像水一样顺序流动,随着人物的命运发展。电影中处处皆有水,宽阔的河流,湿润的台阶,戏班子的车穿行在大街小巷时总在下雨,而小云总是忍不住要掀开雨棚去接雨水,她始终是一个触碰禁忌的女性。“溺水的鱼”和“水中的女性”之间的互文关系正是电影想要讲述的主题。
(三)“苹果”
李玉电影中一个常用的意象,就是苹果,她甚至为自己后期拍摄的一部电影命名为《苹果》。
苹果在电影中仅出现一次,但出现的时机意味深长。小云在公开的演出中,被情夫刘云金的妻子带领众人厮打凌辱,受伤倒地。在汹涌围观的人潮中,她最终自人群中走出一条路来,消失在画面中。这一幕对于整部影片是一次情绪的转折,也是女主角被侮辱、被损害的人生历程中惨痛的片段,李玉导演在这一场景后安排了一场戏,小云自己的房间,她在蚊帐罩起的床上,啃一只苹果,面无表情,场景里只有苹果被咬下时清脆的声音。
《圣经》的《创世纪》中,夏娃收到伊甸园中撒旦所化的蛇的诱惑,偷吃了苹果,从此获得了智慧,有了羞耻心,但也因此犯下原罪,被赶出伊甸园。苹果的隐喻在李玉导演的影像表达中,不写悲情,反写知耻,是小云受辱后开智,为“出走伊甸园”式的离开埋下伏笔。
二、人物创作
(一)三个母亲
本片人物创作的最主要部分是导演创作了三个母亲形象,其中每一个女性都有自我意识的成长。
第一个母亲,小云。年少轻狂,因为一次犯错而永远无法弥补的母亲身份,这个身份直到影片结束她也没有真正尽到母亲的职责,她是“出走的母亲”。影片中儿子小勇对她的感情更接近于倾慕,在暗夜的桥洞下,小勇对小云说:“云姐,我养你嘛。”小云希望小勇亲吻自己,这一举动,转换二人关系,带有无意识的乱伦,小云在小勇的倾慕中重新找到了女性的自觉。她遗失已久的尊严感通过无意识的母亲角色得以回归和成长。
第二个母亲,小勇的养母,是处于“困局中的母亲”。为了表达这种困境,导演为她安排的生活场景是通过楼梯下行才能到达的地下室。她因为照顾小勇失去婚姻,甚至因为小勇不接受其他男人介入他们的生活,所以她与理发店老板的暧昧关系决不会在小勇面前表露半分。当小勇亲生父亲,也就是她的弟弟去世的时候,她这辈子唯一的依赖只剩下小勇。可以说,她为小勇牺牲了一切,困在阴暗、见不到光的空间不得解脱。
第三个母亲,苏老师,将自己“困于灵魂深处的母亲”。苏老师所遵循的道德原则不允许自己原谅小云,所以她选择送走男婴,告诉自己女儿这个孩子一出生就死掉了,用自己的方式拆散了一对母子。早年丧父,独自抚养小云的苏老师,是自苦而孤独的,她在影片前期的专横与强势,正是为之后不断暴露的孤寂与酸楚做铺垫。
电影中段,苏老师在厨房劳作,久不回家的小云放下钱出门,从母亲的厨房经过,这个定格长镜头并没有停下,女儿出画后,母亲的背影依旧长久地在后景里沉默忙碌,无须更多解读,也能体味母亲多年的孤独萧索。剧情到高潮处,母女矛盾爆发,她希望接回小勇,冲着自己的女儿爆发:“你不知道我这些年有多孤独!”再到小云决定离开小镇重新找到自己时,苏老师失声痛哭,表演艺术家李克纯老师在这场痛哭的长镜头中表现了极强的戏剧张力,昏暗的房间,湿绿色的墙壁,头顶一盏孤灯在母亲面部留下硬调的阴影,母亲从隐忍到痛哭,女儿从出画到入画,在这一刻,母亲得以释放自己,并最终和女儿达成和解。
(二)三个男人
围绕着小云这个人物电影里出现了三个男人。
第一个男人,张云峰,小云的初恋,小勇的生父,属于“缺位的男性”。小云未婚怀孕的事情暴露后,他将所有包袱丢给自己的姐姐,远走他乡,十年之后回到小镇的只有一捧骨灰。
第二个男人,刘万金,小云的情人。刘万金本身是有家庭的,但他甜言蜜语地哄骗小云说只爱她一个。当小云告诉刘万金不想没有身份地过下去时,他说出了让所有人内心都会为之一寒的话:“过去的教训你还没吸取吗?”他以高位审视小云,以过去禁锢小云。
第三个男人,钱老板,外界所有男性符号化的表达。他代表了小镇男性群体形象,认为小云不洁,谁都有权利欺辱。
(三)一个儿子
小勇,早慧又善良的儿子,他是整部影片中的救赎,是希望之所在。在电影里,围绕儿子的角色,表达了三层人物关系,他实际上是三个母亲的儿子。
小勇出场时,从房子的背面翻下石板,一个精灵不愿循规蹈矩的男孩形象就立住了。小勇去往外面世界的方法是穿过一条宽阔的河流,他从河流中的石板上走过,去往故事里的世界,又沿着石板回到自己的世界。拍摄中,李玉导演特意设计了一条悬空的轨道,以俯拍的方式完成对整个河流的全景拍摄,小勇在镜头的跟移里行完全程,这河流本身就是女性世界的暗喻,小勇横过河流,他是这部女性电影中维系的纽带,也是沟通的桥梁。
三、电影的精神内核
(一)女性意识的自我表达
波伏娃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被塑造成的。”
主人公小云在电影中完成了女性自我意识的成长。无疑,小云是美丽不羁的。和男同学相恋、怀孕生子,然后被学校开除学籍,全镇通报批评,小云还是选择留在小镇,承受数十年如一日的异样眼光。而经过十年生活的打磨,小云不仅没有进一步,反而和有妇之夫在一起。小云如同泥里的鱼,从未从泥水中走出来。
小云的母亲,苏老师对自己女儿的认知是川剧演员。而小云对自己个体的认知,就是一个唱流行歌曲讨生活的人。而这种身份认知的撕裂正是通过小镇这个社会群体完成的。李玉的镜头往往女性都是特写,男性用全景。当小云穿着戏剧服装表演时,台下的观众起哄要求小云唱通俗歌曲,镜头就从小云的脸部拉开,音乐一转,舞台变成嘈杂的歌厅。在这里,小云又一次面临着自我灵魂的放逐,生活所迫,她唱着自己不愿唱的歌。
小云并没有无边无际地随处坠落,在她逐渐麻木甚至适应自己就是一个卖唱歌手时,是小勇唤起了她作为艺术工作者的自觉,当小云得知小勇是自己的亲生子,有意识地和小勇拉开距离时,她重新穿回川剧的服装,在镜头面前扮相,完成了自己职业女性身份的确认,潜在完成自我认识的重新确立。
(二)“看”与“被观看”
在劳拉·穆尔维《视觉快感和叙事电影》中提到了三种男性窥视模式:第一种是认同式的窥视模式。第二种是窥淫癖模式,实质是男人对女人的窥视。第三种是恋物的观看癖。而好莱坞有一个逐渐演变的观点,女性形象逐渐从圣女变为娼妇,但不管是什么形象,女性始终处于被男性关注、关照的位置。
电影中的女性也处于三层“被观看”当中:第一层观看是,“我”对着镜头说话,“我”被镜头背后的摄影师所观看;第二层观看是,“我”在镜头,例如小云,不管被男人膜拜还是唾弃,与男性演员的沟通也是一种观看;第三层观看是,当小云的形象投射在银幕中,观众完成了对角色的观看。
小云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矛盾的角色。她有着隐秘、充满窥探感的往事,却选择了在舞台上永远处于被观看的川剧演员的身份,这样的社会身份和她个体身份形成了无解的结。而如何去消解“看与被观看”的矛盾也成了电影着力表达的部分。小云的扮演者是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刘谊,自身的戏剧功底和刚柔相济的气质,在角色演绎上颇具神韵。
电影中出现的最远镜头也成为“看与被观看”最经典的一个镜头。小云在外商演,周围都是看热闹的群众。这时候,小云情人的妻子在亲戚的帮衬下找小云麻烦,口里骂着狐狸精,手也不停地推攘,甚至撕破了小云的外衣。小云孤零零地躺在地面上,而小勇站在镜头最为偏僻的角落里注视着小云起身走远,他们之间形成了最远的构图距离。其中值得玩味的是,镜头里的群众全都是真实路人,他们不知道在拍摄电影,在镜头里完成了对小云这个人物真实、赤裸裸的观看。
(三)俄狄浦斯情结
李玉女性电影中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父亲形象的缺席。导演个体经验是从小生活在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与继父的关系也很糟糕,所以在她完成电影人物描摹的时候,就决定父亲形象是缺失的。
俄狄浦斯情结讲述的正是俄狄浦斯王在无知的状态下完成了恋母弑父的命运。在电影中的呈现是天真的小勇拿着父亲的骨灰碎片玩,嘴里还发出呜呜呜的声音,场景于观众是刺目的。小勇在无知的状态里完成了两件事:和自己的亲生母亲喝交杯酒,玩弄亲生父亲的骨灰,而他的一生也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
四、结语:开放性的无解答案
女性形象的悲剧不是源自生理,而是社会的、文化的意识形态带来的。
对于女性命运和女性精神归宿的话题是每一位女性导演想要去探讨解码的,但似乎没有一个导演能够给予女性一个可靠的答案,在女性精神出走后如何找到自己灵魂的归宿。女性色彩浓厚的电影似乎都没有欢喜结局,电影《红颜》最后小云和小勇依然是无解的关系,小云登上火车离开镜头后,小勇才从车站出现,再慢慢淡出镜头。电影给出开放性的结局,并没有强行加入注脚,解释小云今后的命运如何,是否如水中浮萍?远去的火车带走一地鸡毛,带走十年的小镇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