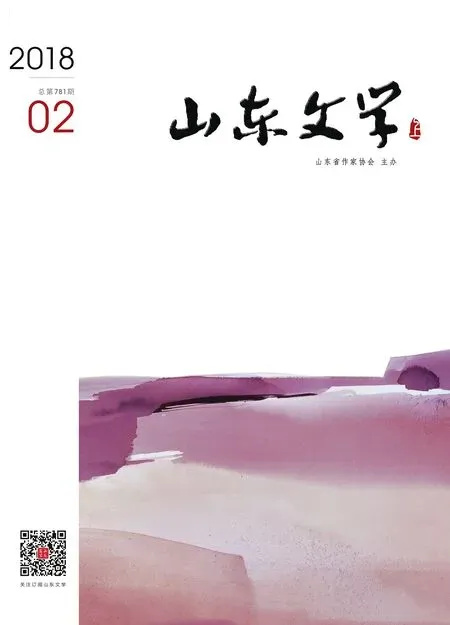散文二题
邱 勋
王希坚佚诗佚事录
佚诗
王希坚先生是建国前后的重要诗人,他的《民歌百首》《黑板报上写诗歌》在1950年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受到与会作家、评论家的广泛赞誉,周扬在大会报告中曾给予充分肯定。臧克家主编的《中国新诗选》(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山东解放区诗歌入选者,仅有他的《诗二首》。后沦为右派,20余年后复出,再无诗作发表。但1957年他有几首诗,曾见于省文联内部资料《整风反右文件汇编》,从未正式发表。现据遥远、模糊的印象,将佚诗抄录如下:
其一
朝辞白帝彩云间 千里江陵不见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 轻舟已在水中翻
戏改李白名作,将“一日还”改为“不见还”,“万重山”改为“水中翻”,自嘲、调侃、无奈、打油、戏谑之状可掬。批判者斥责他用玩世不恭的恶劣态度对抗整风运动,应是批判会后所作,写在日记上,被抄家搜出。当天日记中还有:晚读《约翰·克利斯朵夫》n页至n页,中午与小刘玩“顶牛”一小时。“顶牛”是一种乡间放牛孩子玩的土棋,地上画棋盘,小石子当棋子,蹲而弈之。小刘则不知谁人。
其二
闲爱孤云静爱僧 劝君着意爱浮萍
随波逐流团团转 永不生根入土中
亦批判会后所作,描绘的是违背毛主席“实事求是”原则、见风使舵的跟风派,批判者斥责他这是对于运动中积极分子的奚落和污蔑。
其三
千佛山下雾漫漫 漱玉泉边铁索拦
流水无情空怅惘 古今都道作诗难
也是日记中搜出,应是前二首被批判后有感而发。省文联旧址在趵突泉公园旁,距漱玉泉数步之遥,诗中漱玉泉即指省文联。省文联以至山东省,根据中央文件指示,反右错划率为100%,全部改正。反右中全省作者因诗文获罪罹难者,经省委召开大会并形成正式文件,全部平反。王希坚文革时因日记中以上诗作被上纲批判,自然也在平反昭雪之列。如果读者耐心再读到“其四”,欣赏一下批判者如何指鹿为马,就会更加豁然开朗、彻底明白个中真相了。
其四
忆昔从军20年 浪潮激荡接云天
(第三句忘记了) 永执干戈列马前
作者注明,纪念入党20年而作。批判者指斥作者混进党内,永执干戈站在右派头目马前,向党疯狂进攻。王希坚,山东诸城人,其父王翔千,中共山东党组织创始人,与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邓恩铭一起,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创办宣传马列的刊物《山东劳动周刊》《晨钟报》,任主编。与王尽美、邓恩铭一起,系山东最早的三位共产党员。党组织遭破坏后,回乡从事农民运动,以教书为业,流转各地宣传革命思想。解放后为山东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表,省政协委员,省土改委员会委员,1956年去世。胞姊王辩,山东第一位女共产党员,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邓小平、左权同班。王希坚受家庭影响,自小接受马列主义,1937年参军入党,系红军老战士,整风中并无任何反党言论。划为右派的原因,是因作为文联整风主要领导,不同意按百分比划定右派。批判者颠倒黑白,将一位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入党20年不忘初心的庄严誓词,雌黄其口、歪曲颠倒,实在是对于革命者和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亵渎。
《汇编》中还有4至5首,记不起来了。上述几首,记忆如有差错,识者正之。
佚事
我1956年来济南后,开会时见过王希坚,但他是省文联副主席、党组成员,我是出版社小编辑,并无交往。文革后期,我调往复刊的《山东文艺》,王希坚解除劳教回到省文艺创作办公室(文革中省文联撤销后成立的新单位),接触渐多,并几次一起出发,听到有关他的一些逸闻佚事,谨录如下:
其一
出发途中,谈到其长篇小说《地覆天翻记》,他说,小说写得很匆忙,偶尔得之。抗战初期,临沂地区有支杂牌部队,百十号人、枪。我家与其头头有点瓜蔓子亲戚,组织上派我去做工作,让他弃暗投明,投奔共产党。我住进一个小旅店,等待与他见面。一时联系不上,闲在旅店没事干,就写了《地覆天翻记》,写完寄给了华东新华书店编辑部。过了半年,行军途中遇到书店总经理,他问,你的书出版了,见到了吗?我说未见。他又问,给稿费没有?回答没有。经理下了马,靠在马背上给县新华书店经理写张便条,让他给我稿费若干。我去书店领了钱,买一支派克自来水金笔,剩下的请战友们吃顿饭,打了牙祭。
其二
这支派克笔派上了大用场,希坚说。1948年中央发布“土地法大纲”,作为指导全国土改的纲领性文件,我用一台破收音机收听,用这支派克笔,记录了大纲全文,后来形成文件,指导了山东全省和华东各解放区的土改运动。
希坚当时是华东局土改指挥部秘书,他的字写得又快又好。
其三
我去看一位老领导,遇到省人大W老,他听说我与王希坚同单位,就问其近况。他说,战争年代,行军时不断蹚水过河,过了河,两脚灌满沙子,需要脱了鞋袜涮出沙子,再穿上鞋袜,耽误了时间,往往掉队。王希坚干净麻利快,从不掉队。后来大家发现了秘密,他把几层粗布密密衲成的厚袜子底,从中间剪一道缝,过了河,穿着袜子在水里涮涮,沙子从缝中涮出,蹬上鞋立即跟上队伍。后来大家纷纷学了这一招。
其四
文革后期,王希坚被诬为“右派翻案集团”成员,遭关押批斗。谷牧同志来鲁视察,他曾是王希坚战争年代的直接领导,到济南后即让人通知希坚到南郊宾馆见他。希坚不去,也不回电话。第二次通知亦然,谷牧临走前,第三次通知。办公室告知王希坚,他轻声回答:他还没走?仍然不去。
此事是老作家翟永瑚先生转告的,我问翟,希坚为何这么执拗?翟回说,他可能觉得自己混成这般模样,无颜见老领导。按照一般人的思路,当时谷牧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见了最了解自己的老领导,请他给省里打个招呼,会改善自己艰难的生存状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真是求之不得的美事。但希坚生性刚直耿介,从来不屑于搞这一套,不然,那就不是王希坚了。
其五
有次出发见到诸城籍画家高天祥,他说,在他老家,有许多关于王希坚的传说,说他小时上学,课本读一页撕一页,最后课本撕没了。老师责问他,他回答,全都记下了,课本没用了。老师命令他背给全班同学听听,他从第一课背到最后一课,竟然一字不差。
希坚为人,光明磊落,坦荡其心,堂正其身,虽历尽劫波,但赤心不改。希坚为文,扎根热土,胸怀天下,笔下珠玑。他的作品,除诗集《民歌百首》等5部、小说《迎春曲》《雨过天晴》等6部外,尚有鼓词、曲艺等多部通俗文艺。其文学功力、艺术修养、知识积累,山东同辈作家中无出其右。他离开我们多年,渐行渐远,身影已经模糊。笔者草此小文,目的是希望引起年轻文学评论家对他的关注。相信在希坚作品逐渐变黄的纸页上,年轻的读者和文学评论家,将会感受、寻觅到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精魂、脊梁与底蕴。果能如此,则善莫大焉。
权将闲篇充药石
手持拐杖,步履蹒跚,凑热闹来到千里之外的浙江绍兴,参加第3届金近儿童文学奖颁奖大会,真有点不合时宜,徒令识者讪笑。参会的主要原因是:金近先生是中国儿童文学前辈开拓者、奠基者之一,《儿童文学》杂志首任主编,我的启蒙恩师,有机会前来拜谒先生的出生圣地,表达我缅怀、感念之情,尽管行动不便也是一定要来的。再是我已过耄耋之年,“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在家孤独寂寞,也想出来呼吸点新鲜空气。听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也想出来观一观风景,看一眼,赚一眼。
承蒙主持者不薄老朽,惠我一个与弄潮新锐同台晤面的机会,令我感念满满。会议通知要我谈点创作体会,又担心老迈如我者的陈谷子烂芝麻污人清听,思虑半天,向新老朋友交代几句。
一是写点小玩艺主要目的是为了养生。我一辈子爬格子,近年学着敲键盘,其他聊天、侃大山、唱歌、下棋、麻将、扑克,通通不会,也不感兴趣。人老了,脑子空空荡荡,身体只剩个空壳。唯有读点喜欢的书,偶尔写几行小玩艺,还会感到心里稍微充实一点。请不要见笑,还会有点小小成就感,觉得这一天没有白活,没有白白浪费农民种的粮食,心情就会愉快些,精神也会振作些,身体也会好一点。不仅我自己,据我所知一些老朋友也有类似情况。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孙幼军先生,年轻时是滑冰高手。他近70岁时亲口告诉我,他系鞋带从来不蹲下,也不弯腰,都是一条腿金鸡独立,另一条高高提起,悬空而系之。他写了许多童话,是那一代童话作家中成绩最突出的一位,比如他的《小布头奇遇记》,出版半个多世纪了,至今畅销不衰。他比我还小一岁,前几年身体突然变差,眼睛、脑子都出了问题,不久离世。我悲痛而又吃惊,致电给他夫人,回答是:他患病后,最大的打击是再也不能写东西了,自己觉得活着无用了,没有任何意思了。“哀莫大于心死”,对于生命来说,这是最可怕的了。因而我体会到,对于我这种没有其他真本事的庸人,晚年不放下笔,不断鼓捣一点小玩艺,是调剂生活、驱赶孤独、提高生命质量、争取多活几天的一种切实可行的养生手段。
还可以举孙犁先生的例子。孙犁是我所崇拜的中国当代作家,他著作等身,一生经历过多种挫折甚至磨难,但他所有的作品,全都经得起历史、时代和人民的检验,全都不会背离创作规律和违背作家的艺术良知。贾平凹先生说过,孙犁的作品,不论写于哪个时间段,全都可以收入全集或文集,不需作任何剔除删改。我同意贾的论断,并且认为除孙犁等极少数先生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作品能达到如此境界者,实属凤毛麟角,碍难寻觅。这正是一个作家人品、文品最值得同辈及晚辈尊敬之处,也将为漫长的文学史留下文学的尊贵和尊严与不朽。先生复出以后,抄家抄走的书返还了一部分,他没有工作,为打发时间,就天天给返还的旧书重包书皮,包好以后,顺手在空白处写几行字。这些文字,全似无心之作,信手而记。后来出版了《书衣文录》,读来平实细碎,不动声色,但内涵丰富,哲思蕴藉,字字珠玑,堪称一部奇书。复出十几年,他写了许多散文、杂文,都是炉火纯青、可资传世之作。每年集一本,一共集为10部。最后一部取名《曲终集》,可能取自前人“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诗句。先生一生的吟唱终于“曲终”,此后彻底封笔,再也不写了。
这套书由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总编辑汪稼明先生和作家自牧先生亲自到天津送样书,并看望他们多年心仪、十分崇敬的作家。自牧曾连续数年多次去天津看望孙犁,每次都送他一些包书纸,孙犁曾赠书、赠诗,赠亲手题写的书法作品。每次拜谒都相见恨晚,相谈甚欢。想不到时间过去不过年余,先生身体竟大不如前,已经卧床不起,神智不清。先生是书痴,平生爱书成癖,视书如命。如今见到印制精美的自己的新著,却一反常态缺乏起码的热情,反而向墙而卧,头也不回,嘴里问:稿费送来没有?
两人只好郁郁退出。又过不久,中国一代文学大师孙犁先生悄然离世,“曲终”以后终于“人不见”了。
有朋友告诉我,我们这类经常用脑子的人,突然封笔,脑子闲下来,很容易发病,更容易老年痴呆。我自然不会将以上例子以偏概全,当作普遍规律,但姑妄言之,或可姑妄听之,姑妄信之。如果因不断鼓捣点这类小玩艺,导致不患或晚一点患老年痴呆,权将闲篇充药石,也就算今生今世与笔墨得结善缘,实为暮年一桩快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