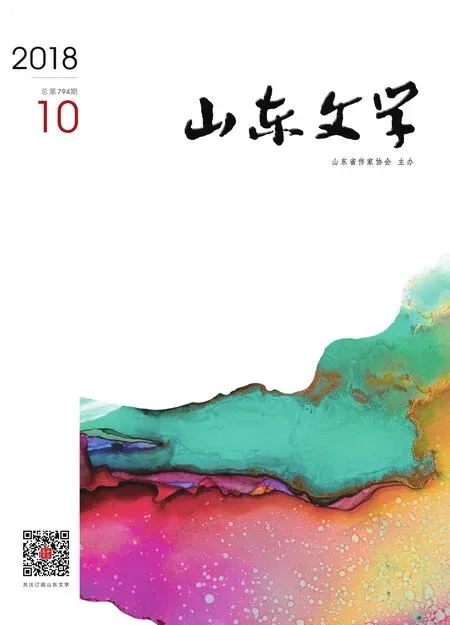故乡的冬天
冯连伟
故乡的冬天,总是在寒风呼啸中一路杀来,带着蚀骨的凄凉,带着苍茫的忧伤,寒冷的夜里,让我对着呼呼的北风发出声声叹息。
时光倒退四五十年,故乡的冬天真的好冷。孤寂的夜里,寒风从草屋的墙缝里嗖嗖往屋子里钻,脱了棉袄棉裤光溜溜的身子,在那床单薄的破棉被里缩了又缩,带着哨音的北风吹净了我身上的一点点热气。
小时候故乡的冬天雪特别多特别大。只要看到天空发昏发暗,用不多长时间,先是盐粒般的小雪粒开始往下砸,慢慢地就是鹅毛般的雪片漫天飞舞,此后屋上、树上、地上都变成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过上一夜,第二天早上起床后,推门时往往一下推不开,大雪把门封了。
一
故乡的冬天,最难熬的是寒冷。
人民公社年代,广大的农村,几乎家家过着没有完全解决温饱的日子。每个家庭少则三四个孩子,多则八九个,到了冬天,当娘的好不容易让每个孩子都穿上了棉袄棉裤,里面贴身的内衣是没有的,有的男人连个裤衩也没有。
只要走出屋门,顿时感到刺骨的冷风从裤腿角、袖口处嗖嗖的往上蹿,虽然穿着棉袄棉裤,还是冻得牙齿咬得嘎嘎响,瑟瑟发抖,深深地感受到:“百泉皆冻咽,我吟寒更切。”
整个冬天是没有条件洗个热水澡的,身上的灰尘有多厚不知道,身上的气味有多难闻也不好意思说,感受到的是浑身的刺痒。棉袄棉裤的针线缝里、胳肢窝里都长满了虱子;妇女的发髻、姑娘的辫子里用篦子刮一刮,就会刮下不少的“几子”(虱子的幼仔),用手一捻,心里瘆瘆的。
脚上穿的棉鞋也不暖和。过去穿的棉鞋鞋底都是碎布糊成的用麻绳纳成的布鞋底,冬天在雪水里一泡,整个脚像踏在冰冻上,晚上回到家里,两只脚冻得通红。家里条件好的,堂屋里烧着无烟煤的火炉子的,把湿透了的棉鞋脱下来,放到炉子边上烤干,第二天穿上舒舒服服的;家里穷的,没有点火炉子的,湿透了的棉鞋最多一夜往外控控水,第二天早上也只能继续把脚伸进这冰窟窿里。
故乡的冬天每年都会下许多场大雪。往往是头一场大雪还没融化,第二场大雪又接上了。早上出门走路的时候,往往看着有人走过的脚印,沿着别人的脚印走,但有时一脚踏下去,一下子掉到冰窟窿里,大雪没到膝盖,等把脚从雪堆里拔出来,棉裤里被雪也塞满了,顶着寒风,从裤腿角里伸进手去把雪一点点地抠出来,抠不干净的雪融化了,又淌进了鞋子里,好长时间暖不干。
大雪过后,家家户户住的草屋小院门旁,都有堆起的一大堆雪。现在的孩子冬天里盼雪天,如同过去农村的孩子盼过年一样,一旦下雪,往往拽着父母堆雪人拍雪景。上推四五十年,过去的农村孩子对雪太熟悉了,我们也去折了几根松枝子插到雪堆上,用两个玉米棒槌头插到雪堆上当雪人的眼睛;我们也打雪仗,抓起一把雪就是一个雪球,扔到身上灌到脖子里冰凉冰凉的。一堆雪晒太阳时间长了,撑不住劲了,不知道什么时候,高高的雪堆在太阳底下轰地一下倒塌了,当爹当娘的就会喊上孩子,拿铁锨的拿铁锨,拿扫帚的拿扫帚,直到把雪再堆好为止。
冬天下雪的日子里,家家户户的草屋檐底下都挂着一排排的冰棱子。
太阳照射下,冰棱子开始融化,于是就听到满院子传来此起彼伏的“滴嗒”声。到黄昏时,院子已经被融化的雪水浸湿了一大半,天黑了,太阳躲到山后去,气温再次降下来,屋檐下的冰棱子不再滴水。第二天早上起来,走在院子的泥地上,一脚踩下去,“咔嚓”“咔嚓”的,原来头天化到院子里的雪水又结成冰了。走路不注意,摔倒也是常有的事。
那时的农村是没有污染的。屋檐下的冰棱子长短不一、形态各异,太阳一照反射出五彩的光芒,不仅是寒冬里的一道风景,还是儿童不花钱的美食。找根杆子,对着屋檐下的冰棱子打下去,一根很长的冰棱子掉到地下摔成了好几截。拿杆子的两只手冻得通红,爹娘扫一眼看着心疼,往往会喊一声:“老天冻死人了你还不赶快上屋里去,找挨揍啊!”于是扔下杆子,从地上捡一块比较大的冰棱子,上屋里填到嘴里咂摸去了。有的当爹的疼儿子,伸手到屋檐下掰下一根完整的,儿子则像收到大礼一样,伸着双手接过来,一溜烟地跑到院子外找小伙伴显摆去了。
冬天里下大雪的时候,最怕的是年老的人经不起折腾抗不过寒冷就没命了。这个丧事在这大雪天里办理,丧主的儿女遭罪,帮着办理丧事的人也跟着受罪。
故乡里过去办个丧事复杂繁琐。我记忆中的故乡,如果谁家的老人去世了,无论平时的日子过得多么艰难,就是借债也要让死去的爹娘走得风风光光。棺材是一定要买的,死去的人火化后,还是要把骨头摆成人架子安放到棺材里。从去世到安葬一般是三天时间,从开始的指路、泼汤、报丧、守灵、搁棺、居丧、吊唁,直到最后的出殡、落葬,上百年来形成了非常复杂繁琐的程序。失去亲人的子女见人就要磕头,脚上要穿草鞋,只要和逝去的老人沾上边的亲戚,以及亲戚的本家族人都要前来吊孝,嫁出去的闺女,没出“五服”的侄女等,她们的配偶列入“重客”,也要一起参加到送葬的仪式中,大户人家送葬的有近百人。一道程序一道程序地走下来,直到把逝去的爹娘安葬完毕。因此在大雪天里,儿女给爹娘出完殡,真的是实实在在地扒了一层皮。爹娘去世后儿子还要“守七”,故乡的风俗是守到“五七”,也就是这30多天的时间里,儿子都要到爹娘去世的草屋里,睡在铺着麦秸的地上。在一个又一个寒冷的漫漫长夜里,“孝子”就这样慢慢地回报爹娘的养育之恩。
我的亲大伯就是在腊月二十四去世的,送殡的那天大雪纷飞。我们全家的亲人都在那寒冷的冬日里,感受着失去亲人的悲伤和严寒的天气带来的肉体上的痛苦。
二
故乡的冬天,总有父老乡亲在忙碌。
冬天天寒地冻,但农活还是要干的。出工就有工分,窝在家里不出工这一天的工分就没了,对社员们来说,工分就是粮食,工分就是全家生存的命根,天再冷也要强忍着出门。
从故乡流传的谚语中可以清楚地了解,冬天里的农活并不少。社员们需要浇灌小麦,需要积肥,需要喂好牛驴骡马,需要把萝卜白菜收藏窖中。
故乡的冬天尽管天气寒冷,生产队长上工的铃声还是会按时响起,社员们每天的农活一点也不耽误。积肥的时候,需要到东河里推土。天好的时候,推车的中青年壮劳力都是自己推独轮车的;下雪的时候,冰天雪地天冷地滑,半大小子姑娘们就都从家里拿着一根绳子,和推独轮车的自愿结对子,在独轮车的车前脸上套上绳子,帮着“拉车”。
每辆独轮车的后面有一个青壮年劳动力推车,前面则是个半大小子或姑娘拉车。拉车的遇到的推车的叔伯大爷大哥是体谅人的,或是恰恰一对小伙和姑娘,则皆大欢喜有说有笑的,前头拉车的不用出多少力,也不影响这辆独轮车的行走,甚至走在别的车辆的前头;如果拉车的遇到个推车的是互相不顺眼的,或者两个家庭本来就有矛盾积着一肚子火的,这就麻烦了,拉车的有的是出工不出力,也可能拉车的使出了洪荒之力,可推车的故意刁难,小推车有如千斤之重,始终慢腾腾的,总之一句话:“拉车的使死也赚不出好,”还会招来一顿埋汰,于是矛盾就爆发了,先是口舌之争,其后就可能拉车的把绳子一扔,推车的把小推车一放,双方就动起手来了。
实行农村承包责任制以后,父亲不再是生产队的牛倌,也没有再干他曾经的“杂货商”,而是推起小推车去洪瑞车站旁摆起了水果摊。
冬天的早上娘都是给爹盛上一碗热糊豆,爹喝上这碗糊豆吃上一个煎饼,就推起装满四五筐苹果、梨、柿饼、大枣、软枣的独轮车上路了。
爹的手和脚都冻裂了,他舍不得给自己买一双棉鞋。他摆摊的车站旁边就有一个饭店,在摆水果摊的十几年里,从没有舍得去饭店里单独吃顿饭。
无论冬天的气温多低,当父亲推起盛满果筐的独轮车往外走时,他的脸上都刻满了自信的印痕,心里总是充满了火热的斗志。肩负着全家人吃穿的重担,天气再冷,父亲的心里总是揣着一团火。
天是冷的,心是热的。一个又一个冬天,父亲一次又一次推起了他的独轮车,推出了全家人的幸福生活,推起了儿女的成长和家庭的幸福。
三
故乡的冬天,最繁忙的是女人。
冬天里要迎来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春节,女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忙啦,娘就是这繁忙的女人的代表。
母亲在腊月,白天黑夜地要忙上一个月,直到大年初一吃了饺子才可以舒心地喘口气。
母亲冬天的夜晚,是在豆粒大的煤油灯的微光,以及后来的15瓦灯泡昏暗的灯光下,缝衣服纳鞋底剥玉米扒花生中度过的。冬天里,母亲边过日子边掐算最多的,是长长的“春脖子”怎么让儿女们填饱肚子。
冬天里让儿女吃饱穿暖是母亲心中的大事。
人民公社年代,我们生产队里每年决算下来,每个工日少则一角多钱,多则两角多钱,我们家挣工分的劳力少,每年算下来不往生产队里倒找钱就很庆幸了,日子过得总是紧巴巴的。
母亲要操持一家老小的吃和穿。家里的收成主要是地瓜干和地窖里的地瓜,另有少量的小麦、水稻、花生、大豆和玉米。每天的主食都是喝地瓜糊豆吃地瓜干煎饼,家里经济的来源除了用鸡蛋去兑换油盐酱醋外,主要靠母亲和姐姐们用芦苇编席子、斗笠去换钱作为家庭的开支之源。
四十年前的冬天真的是天寒地冻,现在的冬天常常无雪,而过去的冬天雪下得特别多、特别大,而且非常配合节气,“小雪不过三五天,大雪不过一两天”必然铺天盖地落下来,每年冬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是一种常态,常常是早上一推门,大雪封山,到处是银装素裹,一片洁白的世界。
晚上睡觉的时候,一床破棉被盖了头捂不住脚。刺骨的寒风透过土墙上手指宽的裂缝吹进室内,盛水的盆盆罐罐都结了一层厚厚的冰凌,睡在秫秸垫子上的我冻得瑟瑟发抖,把被子往头上拽拽,脚露出来了;缩缩腿捂捂脚,上半个身子又裸出来了。每天早上要起床上学的时候,总是赖在被窝里能多拖一会就多拖一会,直到母亲抱来一抱黄豆秸点上火,把我的棉袄棉裤都在火上烤热了,把我从被窝里拽起来,让我趁着热乎气还没散时,赶快穿上衣服去上学。
我姊妹5个,我是老小,我的棉袄棉裤都是哥哥姐姐的棉衣改造的。那时,生产队里每年都要种一些棉花,但在以粮为纲的年代,棉花种的很少,每年能分到各家各户的棉花也就能做一两件棉衣,如果碰上家里娶妻嫁女,连亲戚邻居家分的那点棉花也买过来。每年天冷的时候,母亲就把我们姊妹的棉袄棉裤都找出来,先让我们穿穿试试,重新测量一下各人穿衣的大小长短,该加长的加长,该改短的改短。大姐找了婆家了,需要给做件新衣,别让未来的女婿看不起;大哥都是一名中学生了,也不能穿得太寒酸,即使用的棉花少一点做得薄一点,也要穿得板板正正;父亲是家里的大树,尽管在吃穿上从没有对母亲提过任何要求,但一定要让“当家的”在人前挺住腰杆有面子。母亲就这样老的小的都装在心里,冬天到来的时候,父亲和我们姊妹都穿上了可身的冬衣,而母亲那件斜大襟的棉袄和蓝粗布棉裤一直穿了好多年。
冬天昼短夜长,母亲晚上的时光充实而快乐。那时没有电视,谁家如果有个收音机就是有家用电器了。上小学的时候,写完作业急三火四地喝碗糊豆、吃上个煎饼就跑出去和小伙伴们玩耍。那时的娱乐活动主要是借着月光玩老鹰捉小鸡、丢手绢、捉迷藏,往往玩得满头大汗才回家。
母亲的夜晚总是排得满满的。为了让我们姊妹春节时都能穿上一双新鞋,母亲早早地就开始忙活了。母亲的笸箩筐里,有各种青线、白线、麻绳、顶针等,一双双鞋底都是母亲一针一线地纳出来的,戴顶针的手指头都勒变了形。秋天收获的玉米被母亲打成捆挂在屋檐下或树枝上,冬天的晚上,母亲就招呼我们一起,把这些玉米棒子全部剥成玉米粒收藏起来。记得我们姊妹围着一个盛玉米粒的大箢子,母亲用剪子在玉米棒子上先捅出几路空隙,我们就用手沿着这几路空隙往下剥玉米。母亲给我们的奖赏就是允许我们用小铁锅每晚炒上两勺子玉米粒吃,随着炒的次数多了,铁锅里也能爆出玉米花来。如果是扒花生,那这个冬天的夜晚则更幸福。家里那时每年从生产队里分到的花生,也就是一二十斤,加上母亲到河东岸莒南等花生产地去用笤子倒的花生,全家每年也就几十斤花生,母亲对这些花生平时看护非常严格,直到临近春节要把花生去壳变成花生米换油时,才招呼我们利用一段时间集中扒花生,扒花生的时候对又瘪又甜的小花生可以不经请示就填到嘴里,对一个花生三四个粒的可经母亲批准,放到自己的书包里在同学面前炫耀一番。
如今,娘已经走了。
其实,娘活着,已经不需要她再忙了,她只需要在温暖如春的房子里,看着我们忙就可以了,可这已是再也不可能实现的愿望了。
娘已经和爹又走到一起了,不知爹还去摆水果摊吗?娘还会在寒冷的冬天里给爹盛上一碗热糊豆吗?
没有了爹娘,故乡的冬天在我的心里我的眼里都天翻地覆了。
四
小时候最盼望的节日就是过年。
在那比较贫穷的年代,只有过年的时候可以添件新衣服,可以吃上平时吃不到的猪肉,可以吃上水饺,吃上白面馍馍,所以每过完一个年,就接着开始数算着什么时候过下一个年。
赶年集是腊月里最快乐的事。
离故乡最近的集就是洪瑞集,洪瑞逢集的日子是三和八,因此,腊月二十三和腊月二十八这两个集是最重要的年集。
腊月二十三的年集娘是不让我们姊妹去的,这个年集一般都是娘自己去,主要采购一些娘认为过年必需的年货,如干海带、糖瓜、柿饼子等等;到腊月二十八那天早上,娘会给我们姊妹每人发上两角钱,让二哥二姐领着我去赶洪瑞集。
从我家到洪瑞年集只有二三里路,周围二三十个村庄的人们都来赶年集。这是春节之前的最后一个集,所以,买东西备年货的来赶集,即使不买东西图个热闹看个“光景”的也来赶集。赶集的路上熙熙攘攘,集市上更是人挨人,人挤人,热闹非凡。
集市上卖农副产品的、卖猪肉的、卖鸡的、卖鱼的、卖纸花的、卖糖葫芦的、卖糖瓜的、卖鞭炮的、卖摇钱树的,应有尽有。
卖猪肉的摊子前,有的是家里有喜事需要办几桌菜的;有的是在城里工作回家割几斤肉孝敬爹娘的;也有的是生产队结算分红后分到了钱的,今年收成好,多割几斤肉,过个肥年,让孩子们多吃几顿肉馅的水饺。二哥二姐领着我经过猪肉摊前,总是不多看一眼,拽着我的胳膊快速地经过,因为我们手里的两角钱没有去割肉的计划。
卖鞭炮的摊子二哥二姐是不让我过去的。这个地方场地很大,几十家卖鞭炮的轮流燃放,除了放上百响的鞭炮,还放我们统称“地雷子”“二踢脚”“钻天雷”的,赶集的路上就听到不停的鞭炮的声音,离卖鞭炮摊子很远望去,上空也是一片烟雾,空气中弥漫着浓浓的硝烟味。
卖糖瓜的摊子是必去的。过去年集上卖的糖瓜,都是大米花用熬的红糖或白糖,极个别的是地瓜油粘的饼,一般花5分钱可以买两三块薄薄的糖瓜,拿在手上吃到口中香香的、甜甜的。
二哥二姐带着我赶集的时候,受娘的委托还要带着我到饭店里买碗菜吃,一般花一角钱可以买一小黑瓷碗不带肉但是肉汤熬的粉条,如果买两角钱一碗的,里面就能带上几块五花肉了。我吃这碗菜的时候,二哥二姐都是看客,他们舍不得给自己买一碗,每每想起这碗菜,口中还是余香犹在。只是感叹穷的时候嘴馋,现在有钱了,肉可以随便吃了,想吃多少有多少,却不能吃了,血脂高、血糖高、血压高,不敢吃肉的,想想都感到生活真会开玩笑。
从饭店里出来,二哥二姐会带着我到卖泥人的地方看看。泥公鸡,鸡尾巴上插着两根红鸡毛,一点也不像,可是使人看去,就比活的更好看,家里有小孩子的,不能不买。买了泥公鸡,又看见了小泥人,小泥人的背上也有一个洞,这个洞里面插着一根芦苇,一吹就响,孩子们很喜欢。
二哥二姐一般不会给我买泥公鸡泥人的,他们往往会给我买个小哨子或竹笛子。从递到我手里的那刻起,不论是哨子还是笛子,我都会随时随心所欲地吹一吹,兴奋一下。
从集上准备往回返的时候,一定要去买一棵摇钱树的。所谓的“摇钱树”就是竹子,那时老百姓家里的院子里都有石磨,买回的竹子插到磨眼里,上面挂上一串串的花生、红枣、纸花等等,到年初一的那天早上,晃动这棵竹子,掉下的花生、红枣,寓意往院子里撒钱,图个大吉大利。
赶完年集就盼着真正的过年啦。
真正的猪肉馅的饺子,只有等到大年初一的早上才能吃上,吃完水饺就结伴去大队部,看大队里组织的自编自演的文艺演出。
小时候我们大队只有一条主街,东起河堰门,从河堰门再往东可以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跨过沭河;主街的西侧往西延伸走西汪的南涯窄窄的小路,一直通到村外,再往北一折,可以通到北侧二三里外的岚兖公路。所以乡亲们习惯地说:“村东头”和“村西头”。
说“村东头”一是说村子的方位,如你要找的人家住在村子的东头,二是指老冯家,因为村东头居住的基本上都是冯氏的子孙;我们说:“村西头”的时候,同样的一是指村子的方位,二是指诸葛家,再就是当时的大队部、村小学、卫生室、供销店都是在村西头,全大队的文化经济中心都在这里。
大年初一吃完饺子离开饭桌,就会自然而然地说上一句:“上村西头去看看吧,看看这次他们又弄出什么花样来。”
时隔几十年,现在真的记不住他们演的什么节目了,但我记得的所有参演节目的男女老少,脸上一定是涂得红红绿绿的,这是化妆最明显的标记;当然如果是演小丑的,脸上化的底色则是白色的,眼鼻口则会化成红色或黑色。
最让我难忘的是台下看节目的人群,比台上演节目的还热闹。平时尽管是生活在一个村里,村东头的和村西头的见面交往也不多,现在大年下见了面,村西头的多数给村东头的都是称呼:“三叔、二大爷、老奶奶。”见了面都是“老奶奶长老奶奶短”地热情拜年;其实被称为“老奶奶”的年龄并不大,谁让老冯家过去多少辈都穷娶妻生子耽误了,不如村西头诸葛家人丁繁衍速度快,于是年纪轻轻的赚了个高辈分。
春节期间看这些自编自演的节目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当娘的趁此机会,给自己到了成家年龄的闺女儿子,找婆家寻媳妇牵线搭桥。
“老奶奶,明年过年的时候该娶儿媳妇了吧?”诸葛氏一句话就问到了关键处,平时她就是给人牵线搭桥的月下老人。
“孙媳妇,你真会说话,我心里可真是盼着明年过年娶儿媳妇的,三间屋已经盖好了,虽然不是全砖全瓦的,但也是中上等了。你大叔还没有合适的人,就等着你给我找个又俊俏又懂事的儿媳妇,到时一定少不了你八样谢礼。”边说边拽着孙媳妇离开戏台子回家拉呱去了。
至于戏台上还会演什么节目已不是她们关心的了,她们拉呱的最大成效可能没出正月十五就相亲;到了中秋节前就计划“传启”(农村确立恋爱关系后男方给女方家买10身左右的衣裳,送衣裳称为传启);秋收结束家里有了粮食,就可能男方去给女方家送“年命帖子”(男方送给女方的结婚年月日和时辰),再到过年的时候,“老奶奶”真的把儿媳妇娶回家啦。
五
故乡里的冬天,最难熬的寒冷已成为一种记忆,当如今在冬天过着室内温暖如春的日子,有多少人还会去想那寒风刺骨瑟瑟发抖的岁月呢?
故乡,是爹娘生我养我的地方;如今,故乡里有我爹娘合葬的一个坟墓,那里面睡着我的爹娘。
寒冷的冬天里,父亲推着独轮车摆水果摊已成为我的回忆,娘在寒冬腊月挑灯夜战,给我纳鞋底做一双布鞋已成为我的念想。
故乡历经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发生了大变化,但故乡的冬天里,发生的那些让我铭心刻骨的事,却永远地保存在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