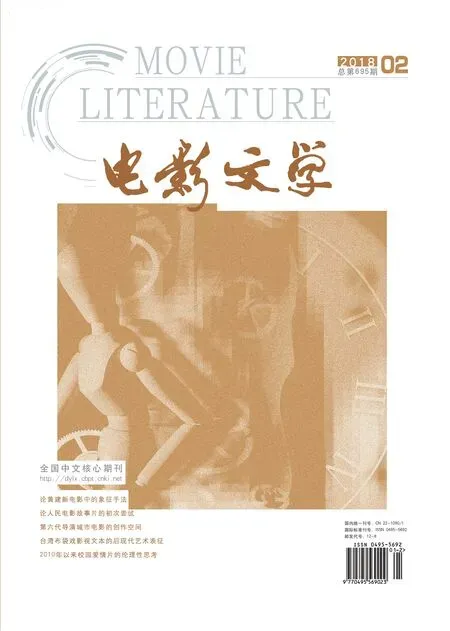2010年以来校园爱情片的伦理性思考
杨 璟
(重庆人文科技学院,重庆 401572)
2010年以来,校园题材的青春爱情片在银幕上十分突出,出现了《匆匆那年》《既然青春留不住》《同桌的你》《万物生长》《我的播音系女友》《我的青春期》《小时代》《左耳》等电影,到《夏洛特烦恼》达到高潮。这些电影“以其讲人话、接地气的良好表率,建立起观众对于国产电影的信任度,显示出文化亲近感之于市场的说服力,也在不断反衬出甚嚣一时的古装大制作的日趋式微,提示着中等成本商业类型片的切实可行”。然而,部分校园题材青春爱情片中的伦理价值取向与中国传统校园题材电影有较大的差异,值得我们深思。
一、中国传统校园题材电影的伦理道德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以来,近代中国智识阶层主张“‘悉夷’(了解西方)‘师夷’(学习西方)、和‘制夷’(抵御西方)”。因此,近代以来教育问题是极其严肃、崇高的。在中国电影史上,电影家们也同样重视电影教育的作用,周剑云提出电影“是引导社会向前进,予人以是非善恶而暗示的,……‘收潜移默化之效’。这不是通俗教育的明证吗?”因此,早期内地校园题材电影很自然地建构起严肃的导向意识,成为展示历代教育工作者筚路蓝缕的视窗,也成为文化精英与大众交换教育理念的平台,在其中家庭、社会和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之间无论是冲突还是融合,最终以引发观众对教育事业的反思为其终极诉求。
“中华民国”时期,真正的校园题材电影还比较少,但已经出现了一些关于教育问题的影片。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引起轰动的电影《孤儿救祖记》(1923)就展现了新办“义学”,“主张用义务教育来改良社会”;《桃李劫》(1934)中更是引发人们对精英伦理教育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冲突的思考。新中国成立后,广受争议的《武训传》(1950),勾勒了武训乞讨办学的悲剧而崇高的人生,“歌颂他坚持到底的精神”。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校园题材电影,如《为孩子们祝福》(1953)、《祖国的花朵》(1955)、《花儿朵朵》(1962) 、《园丁之歌》(1974)、《金色的教鞭》(1979)、《苗苗》(1980)、《四个小伙伴》(1981)等。可以说,在这些校园题材电影中,不但“出现了一批以校园为背景的歌颂新社会少年儿童幸福生活的影片”,奠定了电影关注基础教育的传统,还较好地执行了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教育功能,形成了积极向上的校园伦理文化。
二、新时期中国内地校园题材电影伦理价值的转向
改革开放以来,在多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洗礼之后,中国内地校园题材电影开始关注个性自由,并逐渐将“真”这一品德摆放在重要的位置。
1984年,根据著名作家铁凝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衬衫》改编的电影《红衣少女》成功地塑造了少年安然的形象,而“这部以表现心灵纯净为主旨的作品,容纳了相当深刻、丰厚的社会思想底蕴”。安然为了能够评上三好学生,不断地遭到家人对其个人自由的剥夺,最终她终于评上了三好学生,但这却是靠姐姐为韦老师发表文章换来的,她开始怀疑生活,无法理解社会中的人为什么做自己会这么困难。接着彭小莲导演的《我和我的同学们》(1986)、史蜀君导演的《失踪的女中学生》(1986)等校园题材电影纷纷把视点放在个人自由之上,教师和家长也会因为失去了“真”而受到学生的怀疑。在《我和我的同学们》和《失踪的女中学生》中,开始触及了违反校园伦理规范的“早恋”现象,而作者并没有去抨击早恋,而将它作为青春少年正常的心理需求,安放到个人自由的伦理追求之中。
1987年,陈凯歌改编了阿城的同名小说《孩子王》,故事主线是“文革”时期知青老杆在贫困的村里的初中教书的故事。这部电影表面上很像“支教”话题的电影,然而,陈凯歌将其对文化霸权的思考融入影片的情节和细节设计之中。正如法国学者路易·阿尔都塞所言:“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以意识形态方式’发挥其功能作用。”
无论是《红衣少女》《失踪的女中学生》还是《孩子王》以及后来的《一个都不能少》(1999)、《无声的河》(2000),虽然打破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建立的校园伦理文化,卸下了崇高的教育诉求,在伦理道德问题上更多地关注个人意志和个人品德,然而总体上还是严肃的、震撼人心的。
三、2010年以来中国内地校园青春爱情片的伦理性思考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港台地区拍摄的校园青春爱情片开始影响中国,而这些影片中不少是宣扬“纯爱”“真爱”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关系是不以自由恋爱为基础的,例如,“严禁良贱通婚是周秦以来历代在婚姻条件上奉行的一条准则”。因此,为反对旧文化、旧道德,在新文化运动之后,自由和纯洁逐渐成为文艺作品中爱情伦理的最高原则。2010年以来的校园题材青春爱情片不但将爱情作为影片的主线,而且其中所反映出来的爱情观比较好地继承了新文化运动以来健康积极的爱情文化,但确实也存在一些值得思考的伦理问题。
(一)是否应该歌颂早恋
早恋一般指未进入大学阶段的青少年之间发生的爱情。早恋是中学阶段甚至小学阶段存在的客观现实,在2010年以来的中国青春爱情片中,早恋现象开始堂而皇之地登上银幕,并且成为被歌颂的对象。《80后》(2010)、《青春派》(2013)、《初恋未满》(2013)、《匆匆那年》(2014)、《左耳》(2015)中都涉及高中生早恋;《同桌的你》(2015)中的林一和周小栀甚至从初中就开始早恋了。在这些影片中均将早恋作为没有沾染“社会恶习”前的纯爱来歌颂。
《匆匆那年》和《同桌的你》采用倒叙手法增加了影片的悲情感,当故事的男主人公经历了“世间繁华”之后,才真正地感觉到初恋的真诚与可贵。《初恋未满》更是以诗意的手法,展现了董啾啾和夏静寒在高三时的初恋。有评论家声称:“《匆匆那年》在网剧基础上,为大银幕题材开拓又迈进了一小步,让早恋也有了青春正能量。”也有评论家在观看了《同桌的你》之后这样评价道:“我们这代还没有老,但已经喜欢回忆,现实在不断地打击着我们,学校时代是我们最单纯最幸福的阶段。”
诚然,爱情的纯洁性、排除其他社会因素的干扰是理想爱情的终极追求。所以,在物质欲望较弱的少年时代的爱情很容易被等同于纯爱,而弘扬纯爱精神在当今中国社会的伦理性价值极大。但是,中国电影目前还没有实现分级制度,这些青春爱情片是可以面向所有年龄阶段的观众的,那么这样的爱情故事对未成年人也可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引导作用。现代教育学和心理学研究早已取得明确的研究成果,早恋对少年的身心都有一定的伤害,那么为了表现纯爱而歌颂早恋的策略的正确性本身就值得商榷。
(二)在世俗生活中坚持人性本善的原则
这一轮校园青春爱情片的风潮中,在人物塑造策略上更加突出其 “真”的品格。为了追求这个“真”的震撼力,一些校园青春爱情片在主要人物的设计上突破了“好人”和“坏人”传统二元对立的限制。不少剧作家认为“十全十美的人物是不会令人喜爱的。所以当你的人物是一个好人时,你应当注意不要让他太过完美”。在这轮校园青春爱情片中,许多主要人物的道德缺陷明显,在行动线中犯下一些道德错误。然而作者大都抓住了人物的“道德谴责感”,着力突出人性本善原则,并成功地实现了以情感人的效果。
《第一次》(2012)中,本来只是为了钱而骗宋诗乔感情的吕夏逐渐被宋诗乔的纯真所感动,对宋诗乔产生了真挚的感情。《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2013)中,陈孝正为了自己的前途出卖了郑微真挚的爱情,这成为他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因为青春,就是梦想遭遇现实的一次撞击”。而《匆匆那年》和《同桌的你》中的陈寻和林一同样是背叛真爱的男人,影片着力突出两人对各自愚蠢选择的深切悔意。《夏洛特烦恼》(2015)中夏洛的道德谴责感表现在“当他站上所谓的人生巅峰,内心深处最无法忘怀的,却是那曾经被自己吃到腻烦的汤面”。
在《左耳》(2014)中,主要人物张漾“可谓是这部电影中最为复杂的一个人物,他外表冷酷,性格乖张,脾气倔强,有一股说不出来的狠劲。……可是骨子里他又好强上进,目标清晰,希望在社会上出人头地。”黎吧啦对张漾真挚的爱情,让他的心里充满了道德负罪感,直到黎吧啦的死真正唤起了他善良的本性。
如果说黎吧啦是反抗秩序的符号,那么《万物生长》(2015)中的柳青就是典型的社会“坏女青年”的代表。而秋水可以说在爱情上毫无道德底线,但“观众看到的是他们拥抱时的美好,却看不到秋水此时是在为背叛爱情而自责还是在为偶然的激情而窃喜”。
中国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过程中,确实出现了一些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社会现象,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的爱情的纯洁性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围绕着经济利益,爱情、权利和财富的界限被打破,老百姓对腐败、拜金思想深恶痛绝。那么在文艺范畴内对纯洁、真诚的追求极大地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让人们得到了心灵的净化,所以象征着纯洁的校园爱情也成为电影人自觉的选择。虽然在这一文化图景中还存在一些过于娱乐化、个人化及不合适的导向问题,但总体上对人生的探讨是有意味的,是充满正能量的。因为文艺作品中爱情是永恒的主题,那么这一轮校园青春爱情片的伦理价值取向完全可以被以后的其他类别的电影创作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