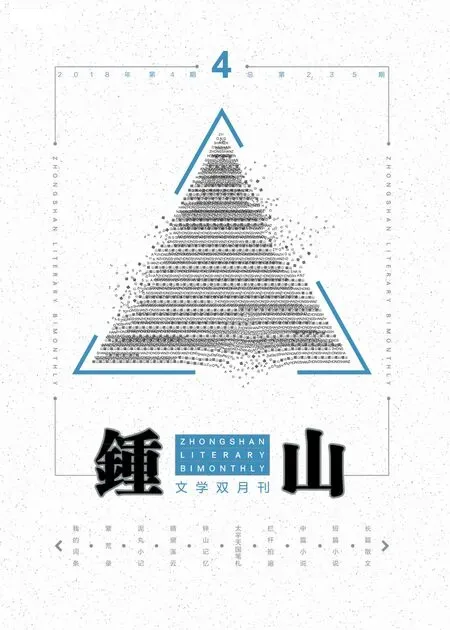白鹭在冰面上站着
雷平阳
LEIPINGYANG
一冬日黄昏的土路,冰凌早就融化了。但那一层薄薄的冰凌化不出多少水来,它们只是把路基表面的尘土浸湿了,人走在上面有点打滑。小男孩从旧庙改成的小学校出来,低着头,匆匆忙忙地就往家里赶。脚上的布鞋是父亲穿烂了的,母亲缝上几个补丁让他接着穿,尺码显然大了很多,他在鞋尖里塞了布团子,仍然不合脚,走在土路上,一拐一滑,看上去十分费力。
土路两边都是收割干净的稻田,蓄了水,从上面吹来的北风既刺骨又阴冷。小男孩上身只套着穿了两件补丁成堆的单衣,下身就是一条有了几个破洞的劳动布单裤,所以,尽管走路很费劲,他还是一个哆嗦接着一个哆嗦,脸上吊着长长的鼻涕。他幼小的灵魂似乎已被冻僵在了离去的风里,所幸他尚能把它收回来。
“放学后,马上回家,去荒地里挖点荠菜。”上学前,母亲叮嘱过他。
“挖荠菜,是不是,妈妈?”小男孩以为自己听错了,反问了一句。蔬菜是有等级的,青菜、白菜和莲花白排在末尾,一般都是清水煮,配上一个辣辣蘸水,便可应付一顿饭。往上,就是菠菜、豆尖苗和荠菜,这三种菜清水煮出来味道寡淡,不仅填不饱肚子,还让胃里水汪汪的,很不舒服。但只要把它们放到油汤里去煮,再加些肉片或豆腐进去,滋味就变得无比的鲜美。再往上,就是青蒜、青椒、生姜和小葱之类的佐料了,小男孩的家里,几乎没有它们的踪迹,只要爸爸妈妈说,去地里采几个青椒、拔几根蒜苗、挖一块生姜,嘿嘿,那就是说,接下来的这顿饭有炒肉吃了。小男孩上一次吃肉是中秋节的时候,算起来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情了。之后,家里来过一个借粮的亲戚,晚饭时母亲用猪油汤煮过一次菠菜。想起猪肉和油汤,小男孩就忍不住嘴巴里冒口水。所以,听到妈妈说要他挖荠菜,他就知道今天的晚饭有油荤了,心里说不出来的高兴。以至于整个下午的两节课,小男孩根本不清楚老师都讲了些什么,一会儿想着自己在荒地里挖荠菜,一会儿又想着饭桌上那油汪汪的一碗,想着想着就又是咽口水又是傻笑,脑袋上挨了老师的几颗粉笔头。
一切不出小男孩所料,到了傍晚,妈妈洗了头,换了一身干净衣服,很上心地把他挖回来的一竹篮荠菜择洗干净了,果然用油汤煮了一大碗油荠菜,关键是,里面还放了很多雪白的豆腐。妈妈把荠菜煮豆腐做好了,又用油炸了一碗土豆条,拌了碗酸菜。小男孩欢天喜地地拿着碗筷,大声喊着门外正在劈柴的爸爸:“吃饭啦,吃饭啦!”
“我们再等等,一个亲戚快到了。”妈妈一边对小男孩说,一边又冲着小男孩的爸爸问:“他到底什么时候才到啊?天都黑了。”
“应该进村子了吧!”爸爸的声音压得很低。
这时候,家门口有人路过,吸了吸鼻子,就与父亲打招呼:“哈哈,你们家有油荤啊。”爸爸知道,这种情况下,千万不能装大方,邀请别人来吃饭,一旦随口说上一句客套话,对方肯定会欣然接受。所以,爸爸依旧挥斧劈柴,嘿哧,嘿哧,没搭对方的话茬。对方伸长了脖子,眼光伸进屋内扫了一圈,见主人家默不作声,有些不舍地走了。又有人过路,接连几个,情况也一样。
“妈妈,我饿死了……”小男孩说。
“再等等。”妈妈应答说,目光转向了门外。
这一等,雪就下来了,而且越下越大。小男孩的爸爸把劈好的木柴搬进家里,在灶台的角落,耐心地将其堆成塔状的两堆,心里想着这应该够过冬用了吧。他站起身来,喊了一声儿子的名字,把一根长长的松节递给儿子。两双手碰了一下,都是黑黝黝的,手背上均开裂了,有的裂口还沾着血丝。
“把它点燃了,可以上厕所时照明,也可以读书。”爸爸说话的时候,素来紧绷着的脸上奇迹般的出现了一丝笑容,语气里夹杂着一丝得意,就好像送给了儿子一件什么宝贝似的。小男孩九岁了,心里想得到的可不是松节,这种松节他有很多根了,有的用了,没有用过的全放在床边的一个纸盒子里。村里有几个小伙伴都有手电筒,他其实最想有一支,但一直没敢开口。所以,从爸爸手上接过这根松节,他并不太珍视,转过身去,凑在豆粒似的煤油灯上,就把它点燃了。屋子一下子比刚才亮堂了许多。
屋子是典型的滇东北乡下的土坯房,上下两层,门后一副木楼梯通向楼上,楼枕和铺在楼面的竹条子,看上去都被烟火薰得黑漆漆的,挂满了尘灰吊子和各种杂屑。靠门洞的那堵墙有几处炸裂了,裂缝里钉了粗大的几个木楔子,挂满犁铧、板锄和镰刀等农具。从门里进来的右手边,是灶台和石水缸,左边是火塘和吃饭的地方。正堂那堵墙,左右各有一个门洞,一个通向爸爸妈妈的卧室,一个则通向猪圈。两个门洞间的墙体下面,摆着一张比小男孩还高的松木供桌。供桌上方悬挂着领袖的画像,桌面上的东西很多、很杂,有装着各种不同液体的乌黑的玻璃瓶,有铁凿子、墨斗、推刨、钉锤、斧头,还有几本小男孩破破烂烂的旧书。供桌有几个抽屉,同时也充作橱柜。从供桌到大门,地面上坑坑凹凹的,纸片、草茎、布团和菜叶到处都是。看得出村庄所在的地方垃圾严重过剩,人们的卫生习惯没有养成,而且小男孩的妈妈也无心于此。
小男孩拿着点亮的松节,走到饭桌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快要冷掉的饭菜。火塘边上坐着纳鞋底的妈妈抬头望了望他,又把头转向爸爸。
“要不让孩子先吃饭吧。”妈妈的语气平静而消极。
爸爸已经走到大门边,换上了牛皮鞋,准备出门。掉转紧绷着的脸,对小男孩说:“你就先吃吧,我出去看看,这人怎么还不来。”他打开木门,一阵北风就把雪花吹进屋子来了,也把小男孩手上的松节吹灭了。
小男孩很懂事,盛了一碗饭,分别夹了些豆腐和荠菜,坐到火塘边狼吞虎咽地就吃了起来。
“多夹一点豆腐嘛。”妈妈说。
“算了,留给亲戚吃吧。”小男孩说话时,满嘴都是荠菜的清香。妈妈放下鞋底,伸手把荠菜豆腐端过来,让儿子多夹一些。小男孩眼睛里闪着欣喜的光,但还是摇了摇头。
“我今天上课时,就想得淌口水了。妈妈,如果天天能吃上一点儿,那就太安逸了。”小男孩的头快伸到碗里去了,他的话仿佛是从碗底传出来的。
妈妈叹了口气,把荠菜豆腐重新放回桌子上,又开始低头纳鞋底。麻线穿过鞋底的声音,压住了小男孩吃饭的咀嚼声。
两碗饭下肚,小男孩告诉妈妈,他想出去玩一会儿,如果找得到小伙伴,就打打雪仗。妈妈心里想着什么,就只是嗯了一声,小男孩迅速就出了门,走进灰白色的雪夜里。
二又是雪。小男孩刚出门,妈妈放下了手里的鞋底,站起身来,开了门,也走到屋子外边,站在了雪地上。雪花没有记仇,很快就落白了她的头发和衣衫。九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雪夜。一部公安局的吉普车东倒西歪地开进村庄,还没停稳,上面跳下来的三位年轻战士,六只充满了劲儿的大脚,踢得一地的雪尘纷飞,急冲冲地就扑向了妈妈的家。他们没有拍门,直接破门而入,其中一个,抬起手上拿着的手铐,指着正在火塘边烤火的妈妈的相好,你是某某吗?妈妈的相好当时正在与妈妈作别,一脸的泪水,点了点头,主动就把双手抬平了,让那人咔嚓一声把手铐铐上。那时候的妈妈还没人叫她妈妈,她还是一个清洁的少女,小男孩刚刚在少女的肚子里萌芽。
相好被押上吉普车之前,头一直扭回来,望着妈妈,没有说话。妈妈也没有说话,站在门口的雪地上,浑身抖得厉害,吉普车开走了,才蹲到雪地上,继而坐到了雪地上,双手抓一把雪捏在手心里,“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事情发生在前天夜里,天快亮的时候。村庄里的队长老爷驾着牛车,准备早早的去昭通城拉化肥。队长老爷穿着一件绿色的军大衣,戴着棉帽,嘴巴上叼着一支金沙江牌香烟,刚把牛车赶上村边的河堤路,熹光与雪光之中,远远的就看见路上蹲着五个幽灵似的人。那时候的河堤两边全是又粗又高的白杨树,枝条上的积雪一坨一坨的往下掉着。五个幽灵也看见了队长老爷,缓缓地站了起来,双手抱在胸前,待队长老爷和他的牛车行至面前,他们从怀里分别抽出钉锤和木棒,几分钟时间,就把队长老爷打死了。最后,他们把队长老爷的尸体扔在牛车上,拍了几下牛屁股,牛车继续朝着昭通城的方向慢慢驶去。
这五个幽灵一样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妈妈的相好。另外四个,有两个是妈妈的堂哥,有两个是相好的朋友。他们之所以制造了这起后来震动昭通县的凶杀案,原因非常简单:队长老爷借分工的权力,把美得像野山茶花但又不谙世事的妈妈分了去生产队的保管室做保管员,并找空子,在粮种堆上多次占有了妈妈。只有十七岁的妈妈,怀上了身孕。
天大亮之后,那辆牛车行至邻近的一个村庄,人们看见牛车上的人,一动不动,身上堆了厚厚一层雪,担心这人睡着了会被冻死,拉住牛鼻子,让车停下。一喊,没有动静,伸手去摸,发现这人已经死了,脑袋被打开了花,贴着身体的那一层雪全是红彤彤的。
五个行凶者,其他四个都跑了,后来当然也被缉拿归案。妈妈的相好没跑,他对妈妈说,“跑也是跑不脱的,还不如陪一下你。”
相好被抓走后,很快就判了刑。宣判大会那天,五个杀人犯脖子上吊着写了大红色罪名的木牌,站在卡车车厢里被押着游街,妈妈挤在人山人海的观众中,哭得一塌糊涂。相好几次想抬头看一看人群中能不能找到她,都被身后的战士伸手把他的头按下去了。
妈妈在相好入狱后一个月,就嫁给了爸爸。爸爸与相好曾经在一个水库工地上卖过命,是旁边村庄里的人,与妈妈结婚,其中仿佛带了某种特殊的使命前来倒插门。结婚几个月后,小男孩出生了。村庄里有人把小男孩视为一个恶灵,特别是队长老爷家族里的那些孩子,经常把小男孩揍得鼻青脸肿。
三小男孩回家时,看见妈妈站在门前的雪地上,身上积了雪,特别是头上,像顶着一团棉花。
“妈妈,你像个雪人。”小男孩脸上红扑扑的,“你是在等我吗?”
“是啊。”妈妈一愣,但还是很快地回过神来,问小男孩:“儿子,他们没打你吧?”
“没有,没有,今晚一起打雪仗的,都是我的同学,嘿嘿。”小男孩对着妈妈扮了个鬼脸,伸出了舌头,吐着了一团白雾。
进了屋,看见桌子上的饭菜还没动,爸爸也不在,小男孩的笑脸随即不在了:“妈妈,那个亲戚还没到啊?爸爸不是说去接他了吗?”
妈妈用毛巾擦干净身上的雪,又把小男孩拉过来贴着胸口,把他头上的雪和额上的汗水也擦了。小男孩顺势抱住了妈妈,脸巴贴在妈妈的乳房之间:“妈妈,其实,今晚又有人在雪团里包了石头打我,幸好只是打在了屁股上。”妈妈一脸惊愕,弯下腰就要脱小男孩的裤子:“让妈妈看看……”
“没打痛,没打痛。”小男孩说着,拉开妈妈的手,闪身到了灶台边。又说:“他们这么久还不来,饭菜都凉了,我给你热一下,你先吃吧!”说着就往灶膛里投柴。
“妈妈不饿。还是再等一下他们。这样吧,明早还要上学,儿子,你先上楼睡觉去吧。”妈妈说着,坐到火塘边,又纳起了鞋底来。
土坯房的墙壁,最大的问题就是总有很多裂缝,春夏秋三季还好,到了冬天,冷风就会从裂缝中吹进屋来。小男孩没有床,楼板上铺厚厚一层稻草,稻草上再铺一张草编的席子,席子上一床布毯和一床被褥,就是他睡觉的地方。他衣服没脱就钻了进去,墙裂里吹进来的风,把楼上的杂物吹得噼啪乱响。这时候,他才伸手去摸胸口和背上被人用石头打中的地方,发现有一处已经肿起来了。疼自然是很疼,但他已经习惯了疼。平时,只要没有太大的伤口,他被人打得再厉害,也从不让爸爸妈妈知道,即便爸爸妈妈知道了,他也会装出没事的样子。懂事以来,爸爸和妈妈从来没有跟他流露过半句关于他身世的话,可听人咒骂多了,他大概已经知道自己总是被人打骂的原因。有一次,放学路上,他被队长老爷家的两个儿子拦住,把他拖到秋天的玉米地里,逼着他跪下,吃他们拉出来的屎。小男孩死死咬紧牙关,抿住双唇,怎么也不配合,结果他们抓住他的头发,打旋子,让他转晕了,最后才把他的脸按在了屎堆上,弄得一脸都是屎。还嫌不够,他们又把些屎抹在了他的衣服和裤子上。两个恶童走后,他才找了个池塘,洗了身体,又洗了衣服。一身湿漉漉地回家,他也只是对妈妈说,他不小心掉在了水沟里。他觉得自己遭受的是天灾。当然,也有过几回,他想问一下妈妈,为什么那两个恶童总是说,是他和妈妈害死了他们的爸爸,但每一次憋红了脸,看着妈妈阴沉的脸,到了舌头上的话,都跑回了肚子里。爸爸妈妈对他很好,甚至比其他人家的爸爸妈妈对自己的孩子还好。别人家的爸爸妈妈因为什么事,有理无理,常常把孩子往死里打,村庄里到处都是伤痕累累的孩子,可他的爸爸妈妈从来没打过他,也很少骂他。但他发现,爸爸妈妈似乎一直都不开心,家里总是死气沉沉的。有的人家,不仅打孩子下狠手,夫妻间因为钱啊吃饭啊也会大打出手,但碰上什么过年过节之类,人家又会一家人高兴得敲锣打鼓放鞭炮,想尽一切办法捕鱼买酒大吃大喝,自己家里则不一样,没有喜事儿,也没有呼天抢地的伤心事,笑脸很少,哭脸也不多,爸爸和妈妈对吃和穿都没什么兴趣,家里凌乱得插不进脚,也不会太在意。就像今晚这样,说是有亲戚要来,一个荠菜煮豆腐就是一年中难遇的好菜了,就足以让小男孩嘴巴淌水水了。而且没有酒。
被褥冰凉,得由小男孩的体温慢慢捂热。墙缝里吹来的风,不时又扫过小男孩的脸,小男孩干脆连头也缩进了被褥里。就是这时,小男孩听见,家门打开了,爸爸进了屋,啪啪啪地跺脚,似乎想把牛皮鞋上的雪抖干净。心里好奇,想知道家里来的是什么亲戚,小男孩把头又伸到了被褥外面。
“他回来了,但不来我们家,一个人在他家火塘边喝闷酒。问还来不来我们家,他说过几天再说。”爸爸的声音谈不上失落,闷声闷气的。
足足有两分钟没有人说话,家里静谧得像冰封住了似的。屋外的风雪声倒是很大。
“月初他的来信上,他不是说,出来了就直接来我们家吗?”很久后,才有了母亲低沉的声音。这声音仿佛不是向外发出,而是一说就开始内收。
爸爸没有回应妈妈。他们热了饭菜,一声不吭地吃了起来。小男孩觉得那个说要来又不来了的亲戚,要在几天后才有可能来,这意味着还可以吃荠菜煮豆腐,他心里升起一丝喜悦,双手捂着胸口上肿起来的地方,恍恍惚惚地睡着了。
四接连几天,雪一直时断时续地下着。村庄旁的河流,河堤两边蓄了水的稻田,都结了冰。小男孩照例每天都去上学,有时,看见其他孩子三五一群走在河堤或土路上,只要有队长老爷那两个比他大了几岁的儿子夹杂在里面,他就下到河里或稻田里,咔嚓咔嚓,踩着冰面一个人去学校或者回家。冰面比积雪的路面更容易打滑,他的鞋子又不合脚,一再地摔跤。每摔一次,都会引来其他孩子的嘲笑。嘲笑的次数多了,有时摔倒了,他就不立即爬起来,而是卧在河面上,边抹眼泪边望着冰面上寂然站着的一只只白鹭出神。冰层封住了水面和泥土,这些白鹭用什么东西填饱肚子呢?它们为什么不飞走?为什么总是伸着细长的脖子静静地望着某个方向?
每天清晨,出门前,小男孩都会望一眼正在生火或者煮猪食的妈妈,希望妈妈喊住他,告诉他放学后早一点回家。大雪把荒地遮住了,不能挖荠菜了,他觉得妈妈会叫他去家里的自留地里挖菠菜。每一次,妈妈都没有喊他。以前,每天出门,妈妈还会交待一下,注意安全啊,听老师的话啊,别与人打架啊,这几天全省略了,感觉妈妈的心思一点儿也没在他身上。至于爸爸,每天出门或者回到家里,他更是见不到人影子了。几乎接连的几个晚上,都是他钻进被窝后,甚至已经睡着了,爸爸才会一脚踢开大门,带着一身积雪倒进家里来,大声嚷嚷着什么,说出来的话一句也听不清楚,明显是喝醉酒了。妈妈去扶他,倒水给他喝,他扬手就把装水的土碗打掉到地上。那土碗粉碎的声音,在死寂的夜里,既突然,又刺耳,让小男孩本来就毫无安全感的心里,感觉到有什么东西也在跟着破碎,并为之愈发的恐惧,无助。
说好要来的亲戚终于没有来。
相反,有一天放学回到家,小男孩的书包还没有放下,妈妈头发凌乱,面色苍白如蜡,一把就将他揽到了怀里,双手的十个指头鹰爪一样箍在他的背上,指甲快陷进他的肉里去了。同时妈妈的眼泪,不间断地流到了他的头发里。
妈妈的声音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她告诉小男孩,爸爸走了。国家在大山里修一条从云南通往四川的公路,爸爸修公路去了,要很多年后才会回来。“很多年”是什么概念,意味着什么,小男孩不是太清楚,只是预感到,爸爸有可能再也不会回来了。他的双手同样抱紧了妈妈,瑟缩在妈妈怀里,像妈妈那样没节制地哭了起来。